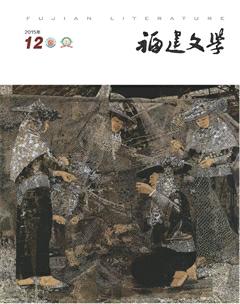穿越塞上古城
葉小秋
從蒼茫的塞上古城銀川返回青翠蔥蘢的北京,已是落日時分。垂柳、碧湖、樓群,還有大街上穿梭的巴士、人流,都被天邊的霞光染成酡紅一片。暮色漸臨,霓虹燈次第亮起,古老的皇城被裝扮得多姿多彩。可我的心兒,卻還留戀著邊城塞上那片雄渾與粗獷所創造的頑強生命與厚重文明……
水洞溝文明
三月的塞上寧夏,正午陽光熾熱而晃眼。天邊的云朵在前面召喚著我們,車子在青銀高速上已經追趕了兩個小時。放眼車窗外,四周灰蒙蒙的一望無際。除了荒堿地還是荒堿地,一兩排新植的小樹搖擺著稀疏的葉子,這怎能掩蓋得了這里的空曠與荒涼?
忽地,車子輕輕停下。眼前,一座筆直的古堡大門撲進眼簾。藍天和黃土之間,仿若從高空拋下的一個巨大“目”字,突兀地橫躺在黃土荒野之上,沒有任何修飾,哪怕是一點點的綠色過渡都沒有。這是四尊牽手相連的人類高大塑像,線條干凈,表情莊重,特別是緊緊抿著的寬厚嘴唇好像要說點什么卻又一聲不響。一派的灰黃與簡約書寫著一派的雄渾與古樸。正是遠古人類壁畫中的形象呀。這兒是寧夏銀川的水洞溝遺址博物館,也可以說是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祥地。
走進博物館,迎面的是一群遠古人類的塑像群。我們靜靜地聆聽,希望能聽見那伴著來自遠古時代的腳步聲和狩獵的吶喊聲。而這一切都那么靜寂,只有導游女孩清脆的講解。
位于寧夏靈武市的水洞溝地區,三萬年前曾是人類繁衍生息的圣地,中間又經歷了幾多波折變遷,誰也不知曉。直到1923年,大清王朝剛剛結束不久的民國年間,兩個名叫德日進和桑志華的法國生物學家來到了水洞溝,他們本意淘金,未曾想卻誤打誤撞發現了一批遠古時代的文物。在當地一家名叫張三小店的幫助下,憑著專業素養,他們沿著河溝側面垂直向下挖開,一層一層出土了大量不同時代的石器和古生物化石。歡呼聲傳過來,水洞溝成了我國最早發現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文化遺址、史前考古發祥地。此后又經過多次考古發掘,這里共計出土石器達五萬多件、動物化石上百件。看著館中陳列的野驢、鬣狗、羚羊、牛、馬等動物遺骸化石,我們仿佛看見了水洞溝人在水豐草茂的林間狩獵嬉戲的場景。石杵、刮削器、砍砸器、尖狀器、石葉片、雕刻器等,剝皮、切肉、砸骨、烹煮,仿佛還沾著水洞溝人昨日的生活氣息。而那些被精心制作、穿孔成串的骨制飾品,不知又曾掛在哪位美少女的脖頸上,隨著跳躍的腳步甩動不息。如此精湛的制作工藝,如此精美的石制工具和裝飾品,在同時代堪稱世界最高水平。
博物館運用展陳、燈光、影像等手段,全面展示了史前水洞溝人的生產活動和生活場景。如果不是那一場突如其來的自然災難,也許水洞溝人還將在這里留下更加輝煌的文明。可是,那場災難又將水洞溝人驅向何方?用心去體會水洞溝文化,那產生于荒蠻而影響于后世的史前文明,留給今天的現代人又是幾多思考。
土夯長城
實景體驗了三萬年前的遠古時代,我們前去探秘五百年前的明代地下兵城。這一路的穿越旅程著實令人振奮!藏兵洞未至,我們先遇到了明代的土夯長城。
水洞溝地區是寧夏和內蒙古交界的地帶,在大自然長期的風化水刮雕蝕之下,一處處奇崛的“雅丹地貌”令人望而生奇,大有地老天荒、曠古玄遠之嘆。眼前的明代土夯長城,蜿蜒于崗巒層疊和山澗溝壑之中,似巨龍起伏,蔚為壯觀。風化的緣故,傾圮十分嚴重,但其昔日雄風仍然可見。據說,明代為了防止韃靼和瓦剌貴族的南侵,在兩百多年間一直在修筑長城。為使長城易守難攻,修筑長城時,不僅依山傍水、就地取材,“挖深溝、筑高壘”,還有意將“草茂之地筑于其內,使虜絕牧(不能到長城以外放牧),沙磧(沙漠)之地筑于其外,使虜不廬(不能設帳篷或蓋房居住)”。長城一定程度上貌似融絕了殺戮與野蠻,但也隔絕了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流。所幸的是寧夏長城段的內側又修筑了一條“寧鹽大道”,即今天的銀川市到鹽池縣的運輸大道。自從清水營“馬市”設立以后,“商販滿關隘,茶船遍江河”,倒是延伸了最初滿足戍軍后勤供應之需。“寧鹽大道”在客觀上成為了有武裝保護的茶鹽客商來往的“黃金商道”,促進了明朝周邊各民族的交流交往。這恐怕就是走西口的前身吧。據史料記載,當年康熙皇帝御駕親征新疆噶爾丹的分裂叛亂,正是沿著這條“寧鹽大道”,搖旗揮進,西渡黃河,到達寧夏府城今銀川的。
歷史的穿越真的很奇妙。明明曾是大漠孤煙、長河落日的邊塞軍事要地,如今倒成了旅游勝地。長城墻體下的塹壕成了荒漠中難得的水渠,滋養了一方百姓,也成了今人蕩舟游玩的所在。當年運送戰地物資的駱駝也成了游人體驗的代步工具。一切的山川河流,一切的人為鑿痕,在時光的無涯里悄無聲息地演變,直至積淀成為我們看到今天的遺址樣子。我們驚嘆于自然的造化,更慨嘆世事的無常。
好吧,我們也試著騎騎乖巧溫順的駱駝。邊關的風很大,陽光十分強烈,人們的皮膚都被涂上了古銅色。只有那兩道招徠客人的目光,既淳樸熱情又多了幾分商人的熟練。吆喝聲中,高大的駝群從第一只開始,依次下跪,待客人上背后再穩穩起立。沿著古老的長城,駝群在坑洼不平的土道上緩緩地行走,風中的荒漠駝鈴響成了一道歷史的風景。我們在駝背上前后搖擺,深陷歷史……
才下駝隊,又上游船。蘆花谷,葦筍嫩綠清新。湖面上,蘆葦叢中百鳥翔集。紅山湖內綠波蕩漾,游船往來,水岸長城,難得一見,在游船上觀賞對岸巍然屹立的古長城,真是別有一番情趣。
藏兵洞
藏兵洞的出現,使寧夏靈武市水洞溝這一軍事防御體系立體起來。這里不僅有雄渾的長城、高大的峽谷,還有獨特的藏兵洞、守軍的城堡。固若金湯,穩如泰山,堅不可摧,牢不可破,這是封建帝王希望締造的神話。但是人事總有偃旗息鼓的一天,只有歷史才能給出最客觀的評價。
也許只有通過地圖,可以更清晰地弄清這個完整、科學、協調的防御體系。藏兵洞位于寧夏東面,連著它與水洞溝的是一段4公里長的大峽谷。大峽谷與長城相伴,它的盡頭就是明代城堡紅山堡,“藏兵洞”就建在紅山堡城邊大峽谷兩側。城堡、洞穴、長城,環環相扣,這是防御工事的基本要素。但是,倘若沒有沙場戰士的奮勇與犧牲,再堅固的工事也無法誕生堅不可摧的奇跡。
紅柳一叢一叢,在這片貧瘠的荒地上倔強地生長了千百年,伴著我們前往藏兵洞的路途。“不錯,不錯,真不錯!姑娘一定會嫁給我!……”駕駝車的腳夫大伯先是唱了一首鄉音濃郁的靈武民謠為我們助興,詼諧的調子滲著喜慶味兒。腳夫大伯唱興正濃,又唱了個陜北民歌《三十里鋪》。“提起個家來家有名,家住在綏德三十里鋪村,四妹子交了一個三哥哥,他是我的知心人。三哥哥今年一十九,四妹子今年一十六,人人說咱二人天配就……四妹子有心和哥哥你拉上兩句話,又怕人笑話。”聽著聽著,覺得就跟著駝車走進了那段風沙漫漫的邊關歲月。老伯的陜北土調竟蒼涼得如同那冷照邊塞長城的月光,明晃晃、激靈靈地滲入心扉。我不禁淚流滿臉,只好掩飾地揉揉眼睛。
我們登上四五十級的臺階,跨進“藏兵洞”,一股陰涼之氣悄然迫近。藏兵洞筑于懸壁之內,上下相通,左右連屬,蜿蜒曲折,不見其終。不足兩米寬的通道僅供單人直立行走。通道左拐又彎,幾乎沒有光線。是開發的后人點了節能燈,才使我們看清這些供人休息的居室。或坐或臥,一人高,一米寬,真是陋室如斗呀。洞壁上掏挖了不少小龕,有的小龕上還有破碎的陶片和煙熏的痕跡,看樣子是放置燈具所用。洞內有一圓形大廳,空間寬闊,那是議事大廳吧。而令人大開眼界的是洞內有小糧倉、兵器庫、彈藥庫等。墻龕上擺著糧庫出土的白菜、蘿卜、稻谷等糧食,兵器庫陳列著刀槍劍戟、箭頭、箭袋、頭盔、盾牌、鐵蒺藜等兵器。此外,洞中還有水井、灶廚、陷阱、暗器孔道等等,我們不禁贊嘆起這樣一處極好的戰時防御工事。
當我們磕磕絆絆地穿過這些暗無天日的洞溝,洞外的紅柳顯得格外明媚。一簇簇熱烈綻放的柳花,在空曠的荒野上顯得十分耀眼,那是歷經風雪之后在天地間傲然怒放的生命之花吧!
責任編輯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