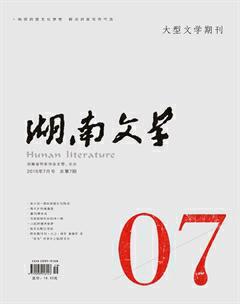閑侃汪曾祺
金實秋
汪曾祺為什么被西南聯大開除別解
在陸建華先生所著的《汪曾祺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中,陸建華首次向外界公開披露了汪曾祺被西南聯大開除的事,這本書是全國第一本關于汪曾祺傳記的書,且出版時正值汪曾祺去世不久,所以影響較大。汪曾祺于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本來應于一九四三年畢業,但由于英語、體育不及格,只能延長一年學業,待英語、體育補考及格再補發畢業證書。然而,一九四四年因抗戰之需,西南大學根據當局要求,所有應屆畢業生中的男生(體檢不合格除外)必須為美軍陳納德的飛虎隊作翻譯和入遠征軍赴緬甸作戰,不應征者一律開除。
汪曾祺時在應征之例,但他卻沒有去。《汪曾祺傳》是這樣敘述的:
“報到那天,汪曾祺翻遍行李,卻找不出一條沒有破洞的褲子,總不能穿著破褲子去報到吧?汪曾祺怕丟臉就沒有去,錯過了報到時間,可不能像英語、體育不及格那樣再補考,汪曾祺因此被學校按規定開除。”
關于沒有應征事,汪曾祺也對他的子女講過,其中也提到了破褲子。他(汪曾祺)說,“他沒去當美軍翻譯其實另有原因:一來覺得外語水平太差,恐怕應付不了這個差事;二來當時生活十分窘迫,連一身像樣的衣服也沒有,身上的一條短褲后邊破了兩個大洞,露出不宜見人的臀部。于是到了體檢那天他索性就沒有去。”(見汪朗等《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然而,有人對汪曾祺此說提出疑義。曾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張源潛先生說:“因為沒有一條完好的褲子而不去報到的。這話很難教人相信。戰爭時代,窮學生沒有完好的褲子比比皆是,就是教授的褲子也少不了打補丁,何況一進譯員訓練班,馬上發給全套美軍制服。”張源潛先生還認為:“甘愿被開除學籍而不去服役,總該有深一層的原因,聯系他的英文不及格,經重讀而延長一年,是不是怕不能勝任口譯任務呢?軍隊生活有嚴格紀律,他散漫慣了,不能適應。再者,翻譯官也要上前線,生命或有危險(確有幾位殉難的烈士)。總之,這些理由中任何一條,總比一條完好的褲子更接近實際一些吧。”筆者認為,此說是有道理的。不過深一層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以為,汪曾祺不去報到,不去服役,當然不是因為“沒有一條完好的褲子”。明眼人一看就會明白,所謂破褲子說,乃托辭耳。至于說是英語不好怕干不了翻譯也有點道理,但也非根本原因。究竟出于何故,從他的一些文章中卻可以揣測與探尋出一些緣由來。
汪曾祺在《七載云煙》中坦言,到西南聯大“我就是沖著吊兒郎當來的。我尋找什么?尋找瀟灑。”在汪曾祺關于西南聯大的文章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西南聯大“自由”的看重或推崇。西南聯大“中文系似乎比別的系更自由”(汪曾祺《西南聯大中文系》載《汪曾祺全集》第四卷)正是這種自由,無形中也培養和成就了他的自由———瀟灑!
從軍作戰,這當然是不瀟灑的,對于不瀟灑的事,汪曾祺當然不干了。我想,這就是汪曾祺不應征的深層次原因。而這樣的瀟灑固然與汪曾祺的性格有關,也離不開當時的西南聯大的相對自由的背景。
平心而論,當時的西南聯大的民主、自由度的空間在國統區甚至是絕無僅有的。且舉一兩例為證吧。
曾經就讀于西南聯大的何兆武先生之《上學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說:“我在二年級的時間才十九歲,教政治學概論的是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教師周世逑,他的第一節課給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問:‘什么叫政治學?政治學就是研究政治的學問,這是當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孫中山有個經典定義‘政者,眾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這是官方的經典定義。可這位老師一上來就說:‘這個定義是完全錯誤的……。”據張鳴《西南聯大的‘黨義課》一文中講,西南聯大甚至對每周一次的“總理紀念周”的政治儀式也是抵制的,每逢紀念周,就于中午十一點半學生午餐時間由“訓導長出來,站在操場上,自己背誦一通總理遺囑,就算了事。”甚至當教育部長陳立夫為此“親自出馬,到聯大演講,試圖說服學生。……沒想到訓到半截,學生們像約好一樣,拼命呼喊抗戰口號,把個陳部長喊得七葷八素,腦袋大了幾圈,實在講不下去,只好識趣收兵。”(載《各界》2014年第3期)
即以征調此事為例,西南聯大的應屆畢業生從總體上說是服從應征,積極投入到愛國抗戰中去的;但是,也有不同的聲音和舉動。當時“在西南聯大影響很大的中共地下黨掌握的民主青年同盟也不贊成學生加入青年遠征軍,甚至不惜與他們尊敬的師長展開激烈辯論。”其時,學生中“有人把辣子粉涂在肛門上,引起痔瘡復發,希望不能通過體檢。”法律系的李模也表示不能應征(見聞黎明《關于西南聯合大學戰時從軍運動的考察》,載《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3期),還有的學生散發和張貼反對征調的傳單。(見[美]杜易強《抗日戰爭中的西南聯合大學》載《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1期)“這一決定在聯大引起了爭議。張奚若教授發表談話,力勸同學們不要盲從。他認為政治如不民主化,軍隊如不國家化,則所謂建軍,實徒私人利用,軍隊之素質與待遇決不能因此提高。”(見侯德礎《略論抗戰后期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載《民國檔案》2006年第2期)。這樣的背景,不能說對汪曾祺沒有影響,也許還是觸發汪曾祺不去報到的根本原因之一。
對于汪曾祺的拒絕征調,當時聯大師生如何看待,時至今日,基本上已無從了解,但至少可以斷言的是:此事似乎在聯大并未有什么不良反映,亦沒有帶來什么負面影響,甚至一點也未損壞師友們和他的關系。現在看到的一些當事人的回憶可以證之。如:
汪曾祺的同學,摯友楊毓珉應征入伍了,但他從越南前線回到昆明休養,還不忘去看望汪曾祺,目睹汪曾祺其時窮困潦倒之狀,立即找人幫汪曾祺找到了教員的工作。(楊毓珉《往事如煙》載《中國京劇》1997年第4期)
中文系的馬識途,比汪曾祺低一班,當時是中共西南聯大的黨支部書記。他回憶說:“那時我們認識,我卻不想和他來往,就因為他是一個瀟灑的才子。我尊重他是我們中文系的一個才子,從藝術上我也欣賞他的散文,但是我不賞識他的散文那種脫離抗戰實際的傾向。……我則認為他們愛國上進之心是有的,認真鉆研專業是可取的,政治上處于中間狀態,是我們爭取團結的對象。事實上他們后來都卷入到學生運動中來了。汪曾祺也是這樣的知識分子。”(馬識途《想念汪曾祺》,載《你好,汪曾祺》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版)。
事實正是這樣,雖然汪曾祺拒絕征調,但他還是愛國的,還是有正義感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四位愛國學生遭國民黨特務暗殺,四烈士出殯那天,汪曾祺也參加了西南聯大送行的隊伍,而且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他還曾去聽聞一多的愛國演講,對聞一多的被害,心情尤為沉痛。(何孔敬《瑣憶汪曾祺》載《長相思———朱德熙其人》中華書局2007年版)
巫寧坤是從西南聯大外語系志愿報名為美軍翻譯的,與汪曾祺是早在一九三六年就“臭氣相投”的朋友。周大奎,與汪曾祺一起創辦“山海云劇社”的社長,還有沈從文先生等,他們也都沒有因此事而輕視疏遠或斷交。
尤其是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那時可是西南聯大外文系的“林黛玉”,她婉拒了一個個同學中的追求者,正式和汪曾祺談起了戀愛。至于后來朱德熙對汪老子女說:“當時我們對你爸爸特別佩服,能夠硬頂著不去美軍翻譯很不容易。你爸爸很有骨氣。”(見《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我想,這也許是有點贊過頭了。然而,他們從在西南聯大就開始的友誼一直很鐵,持續了幾十年,以至他們的子女也彼此成了好朋友。
還應當指出的是,汪曾祺不去報到,不去服役,是公開的抵制,公開的拒絕;既沒有動腦筋在體檢上耍花樣,也沒有想離開聯大,他并不認為自己的選擇是錯的,也從來沒有認為自己的選擇是錯的。盡管,此舉對他不利。然而,這畢竟不是他的亮點或光環,而是極容易被別人詬病的劣跡與臟斑。因此,汪先生自然盡量要對此事避而不談或含糊其詞,這應當是可以理解的,其道理也是眾所周知的。韓石山先生曾指責汪先生“對不利于自己的事,總是多方掩飾,”我的感覺是有點言過其實,“急”過頭了。
對于拒絕應征,汪曾祺是付出了代價的。這個代價,不僅僅是他被西南聯大開除,一時生活極為艱難;更大的代價,是他以后面對此事只好或含糊其辭,或避而不談,或不得不找出上述理由來掩飾、去搪塞,給他大半生帶來的內心糾結和沉重負擔不言而喻,時至今日,幾乎還從來沒有人公開給予同情和理解。這很不幸。
眾所周知,汪先生寫了不少關于西南聯大的散文,也有以西南聯大為背景的小說,其中寫了不少老師、同學和自己的事,但是,唯獨于應征一事絕口不提。不知為什么,他卻在小說《釣魚巷》里似乎捎帶了一下:
“反右運動中,追查他的歷史,因為他曾在孫立人的遠征軍中當過翻譯,在印度干了一年。本來問題不大,甚至不是問題,但是斗起來沒完。七斗八斗,他受不了冤屈,自殺死了。中國有許多知識分子本來都可以活下來,對國家有所貢獻,然而不行,非斗不可!八億人口,不斗行嗎?”
文中的“他”,乃小說的主人公程進,是廣西大學礦冶系的,汪先生的許多小說,緣于真人實事,所謂廣西大學,我以為其實說的是西南聯大,是我牽強附會呢,還是汪先生“別有用心”呢,且附記于此吧。
最后,我必須說明一下,此文撰寫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為汪先生辯解,也不是對汪先生拒絕應征表示贊同,我只是覺得,對當事人已經過去了的事情,我們應力求在比較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礎上予以相對客觀公正地論述;而不要一味地套用某些原則去上綱上線,判斷是非。這樣的努力,較之于簡單武斷或偏激片面的做法,應當是更有利于學術研究和接近真理的。
(附注:張源潛先生是西南聯大的校友,又是《西大聯大校史》的作者之一。他對汪曾祺沒有應征的說法提出疑義,并講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其認真嚴肅的學風、文風是值得欽佩、學習的。陸建華作為《汪曾祺傳》的作者,自然要尊重傳主所言,他在讀了張源潛先生的文章后,覺得有道理,便于后來的傳記文學《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作了修改,書中這樣寫道:“面對當局這種強制性的規定,生性散淡、且總是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汪曾祺,作出了寧可被開除學籍也不去當譯員的選擇。他到底是擔心自己英文太差不能當好稱職的譯員,還是出于對戰爭的恐懼?這些都讓后人難以猜測……”這樣一改,顯然比原說好多了。不過,也有的人仍沿舊說,如于2008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集》之楊早的導言。)
閑侃汪曾祺之粗疏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汪曾祺寫了一篇《吳三桂》的短文,發表于同年第七期《北京文學》。不知是什么原因,文章中應為“敝鄉于二百六十年間出過兩位皇上”這句話,成了“敝鄉于六十年間出過兩位皇上”,一下子整整少了二百年。邯鄲市鍋爐輔機廠的梁辰,是一位細心的讀者,他發現了這個錯誤,遂致函刊載此文入書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社將此信轉給了汪曾祺。汪曾祺為此深為感動,特地在《對讀者的感謝》中鄭重地寫道:“我完全同意梁辰同志的意見。我從小算術不好,但作文粗疏如此,實在很不應該。梁辰同志看書這樣認真,令人感佩。”汪曾祺的文章發表于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文匯報》,時隔出版社轉給他的信僅兩個多月。后來,于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中的《吳三桂》中,那二百年已補上了。可見汪先生對自己作品中出現“粗疏”,是十分注意的,一是虛心接受,二是及時改正,盡管這“二百”兩個字,也許是他本人沒有寫,也許是排版時丟掉了或校對時疏漏了,但汪先生還是將錯攬在自己的身上。
在汪曾祺的作品中,類似于這樣的“粗疏”還有二例,陳德忠先生曾撰文指出,題為《由汪曾祺文想到的》,載于中央文史研究館和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的文史類雜志《世紀》上,此文說:
近讀已故著名作家汪曾祺《四川雜憶》一文中關于樂山的一節,他寫到樂山大佛因風化脫落,雖多次修補,仍造成遺憾時,表示無奈,接著又寫道:“走盡石級,將登山路,迎面有摩崖一方,是司馬光的字。……他的大字我還沒見過,字大約七八丈,健勁近似顏體。文曰:登山亦有道,徐行則不躓司馬光。”這段文其實有誤……事實上這段題詞并沒有刻鑿在大佛身旁的石級邊,而是刻在與大佛一水之隔的烏尤山“止息亭”。題詞的作者不是宋人司馬光,而是清末四川名士趙熙。現今仍嵌于亭壁的碑刻原文如下:“登山有道,徐行則不躓,與君且住為佳。”
短短五十余字中,汪先生錯了好幾處:
一、字的作者搞錯了。將清末的趙熙誤為宋之司馬光了。
二、字的內容有誤。“登山亦有道”,應為“登山有道”,汪先生多了一個“亦”字,“徐行則不躓”后有“與君且住為佳”六字。正如陳德忠所言:“漏了最后一句,意思便是顯得不完整”。
三、字的地點不對。此處不重復了。
陳先生的文章,我是在上海辭書出版社于二○○六年出版的《文苑剪影》一書中讀到的。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中之《四川雜憶》還是老樣子,是不宜訂正,還是不知訂正呢,我不知道。我想,今后在又發表《四川雜憶》時,最好能于文末附注一下,這樣免得以訛傳訛,遺誤后學。我想,汪先生的在天之靈是不會反對的。
還有一個“粗疏”之處,是汪曾祺將自己在西南聯大的老師唐蘭教授說成了無錫人。(見《唐立廠先生》,載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九日《南方周末》)說唐教授上詞選課時“打起無錫腔”。(見《修髯飄飄》,載1991年4月7日、14日《中國教育報》)其實,唐教授是浙江嘉興人也,也許是唐教授曾求學于無錫國學專修館,并曾在無錫做過中學教師,加之嘉興話與無錫話亦相近,故汪曾祺將唐教授誤以為是無錫人了。
這雖然是小“粗疏”,但把自己的老師籍貫說錯了,總是不該的。倘若汪曾祺知道了,必定也會要改正過來的。
順便扯一點閑話,唐蘭教授的書法是第一流的,有人曾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問過沈從文,當代書法誰最好,沈從文答曰:唐蘭。(見李勇、閆妮《流淌的人文情懷》———近現代名人墨記[續],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出版2013年)識者謂唐之行楷“用筆凝練靈活,氣力均勻,鋒法表現特別,結體自然,筆勢瀟灑,書風大方優雅,端莊有法,瘦硬清勁,峻挺而有媚趣,有‘館閣體的中規,又多自然灑脫之氣,大有唐人寫經之風度,堪稱文人書法之精品。”汪曾祺喜書法、懂書法又善書法,可惜在寫唐教授時未于書法著一筆,真是遺憾———當然,此非“粗疏”也!
被汪先生斥為“胡來”的一副對聯
在汪曾祺的懷舊散文中,有一個人寫的一副對聯,曾引起了他的不滿,至少有兩篇文字提到此聯。一是發表在一九八九年第八期《今古傳奇》的《和尚》一文中。文章談了三個和尚,第一個和尚是鐵橋,文章一開始就寫道:
我父親續娶,新房里掛了一幅畫,一個條山,泥金地,畫的是桃花雙燕,題字是“淡如仁兄新婚志喜,弟鐵橋遙賀”;兩邊掛了一副虎皮宣的對聯,寫的是:
蝶欲試花猶護粉,
鶯初學囀尚羞簧。
落款是楊遵義。我每天看這幅畫和對子,看得很熟了。稍稍長大,便覺出這副對子其實很“黃”的,楊遵義是我們縣的書家,是我的生母的過房兄弟。一個舅爺為姐夫(或妹夫)續弦寫了這樣一副對子,實在不成體統。
二年后,汪先生在《我的父親》中又寫到了這副對聯,文字大同小異,但是略去了舅舅的名字“楊遵義”,并說此事“胡來”,“覺的實在很不像話”!
兩篇文字中說的是同一事,用了“實在不成體統”“實在很不像話”這兩個“實在”,實實在在地表達了汪先生的不滿,這在他的文章中是不多的。
其實,這副對聯并不“很黃”,只是“黃”一點而已。
在舊時文人圈子里,逢喜慶之事送諧謔之聯乃雅事,趣事也。晚清聯家何又雄即以雙關語賀人新婚,聯為:
雪點梅花,今夜不知五六出;
灰飛玉管,小陽初入二三分。
傳馮友蘭先生賀吳文藻、謝冰心結婚之聯云:
文藻傳春水,
冰心歸玉壺。
一九三五年,六十六歲的政界名流熊希齡與三十三歲的文壇才女毛彥文結婚,沈尹默賀聯打趣云:
且舍魚取熊,大小姐精通孟子;
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
還有一佚名聯云:
熊希齡雄心不死,
毛彥文茅塞頓開。
有資料披露,這幾副聯當時都曾見于報端,可見,其時并沒有人以不堪入目視之。
在民國時,曾有幾則諧謔的婚聯頗為流行,如:
不破壞,安有進步?
大沖突,方生感情!
伸偽足,原形質滲透;
生孩子,留種族作用。
從詞句上說,“黃”的成分似乎可歸屬于“重口味”一類,且欠文雅,但由于用了當時的一些新名詞入聯“賣萌”,故曾傳誦一時也。
我以為,汪先生對此聯大為不滿,自是出于對父親的尊重也;然而,汪老先生對此聯卻不反感,且長期置放于房間,以至于“看得很熟了”。于此,我們也窺見汪老先生對親友的尊重,也可佐證其人之放達也。
最后,順便說一下:此聯并非楊遵義所撰,乃出自唐朝皮日休之《聞魯望游顏家林園病中有寄》,原句為“蝶欲試飛猶護粉,鶯初學囀尚羞簧”。清時,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將此詩句中第四字改“飛”為“花”,此一字之改,遂容易使人產生聯想了,況且又是掛在新房中哩。據云,今江蘇蘇州留園尚存鄭板橋所書此聯,至留園者猶可欣賞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