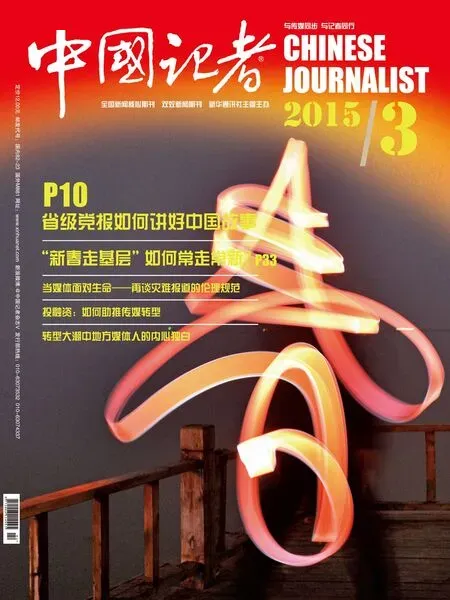以“用戶圈”為核心打造新媒體矩陣
——關于黨報新媒體建設之路的思考
□ 文/楊自強
黨報轉型發展是新媒體建設的基礎
觀點:黨報的發展,應由信息型媒體向樞紐型媒體、驅動型媒體轉型。
黨報的新媒體建設,其前提是有著黨報特色和黨報優勢的新媒體,而以單向傳播、線性傳播、大眾傳播為主要特征的紙媒,其媒體性質是與“互聯網思維”大相徑庭的,很難想象在這樣的土壤上能開出新媒體之花,目前大多報紙建設新媒體陷入停滯不前的窘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因此,黨報要建設新媒體,發展媒體融合,首先要做的,是黨報自身的轉型發展,這是前提和基礎。
轉型的目標,就是由信息型媒體向樞紐型媒體、驅動型媒體轉型。我們一直以來把黨報定位為“大眾傳媒”,而在多媒體的時代,一統天下、老少通吃的“大眾媒體”其實已不太可能,因而,黨報應該適時由“大眾”向“分眾”(即以機關干部、企業主、企事業單位管理層等為主的精英人群)轉型,即所謂“影響有影響力的人”。“傳媒”應該由重點為“傳”,向“‘傳’‘媒’并重、以媒為體”的定位轉型。樞紐型媒體的建設重點有三個:
1.有競爭力的內容。全球領先的信息提供商麥格勞 希爾集團董事長兼CEO哈羅德·麥格勞有句名言:“既然我們現在生活在這樣一個一切以內容為中心的世界里,我們的競爭力就來自于‘聰明的內容’”。對黨報而言,所謂“聰明的內容”,就是受眾在網絡或其他媒體上很難獲取的權威信息。從目前來看,許多新聞種類仍須“持照經營”,傳統媒體尤其是黨報在時政、突發、調查、輿論監督等領域有著網絡媒體所稀缺的新聞采訪權,且這一優勢因意識形態的特殊性,不可能向市場開放。黨報應該充分利用在這部分信息上的“壟斷地位”,精耕細作,做大做強。也就是說,強化“喉舌”的色彩,以本地黨委、政府的代言人形象出現在受眾面前,不一定說得早、不一定說得多,但說的一定是最權威、最具公信力,起到“定音錘”“壓倉石”的作用。
2.占領解釋權的制高點。除了提供權威信息,更提供在此基礎上的分析、判斷、見識,即通過對時政、經濟等新聞的分析與解讀,傳遞出某種有啟發的見解和觀點,占領輿論場上解釋權的制高點。澎湃新聞的一個經典做法,就是通過對海量信息的專業篩選、深度解讀、權威發布,樹立“但凡我所關注,讀者無需他顧”的領導地位。而對黨報而言,更必須也相對更容易做到這一點。
3.強化樞紐和驅動的功能。傳媒,不僅是“傳”,更是“媒”,所謂“媒”包括三方面的內涵:一是聯結各方的樞紐;二是各方發生聯結的應用工具;三是各方展示、推銷的平臺。也就是說,報紙所生產的,不僅是報紙這種產品,更提供給用戶一種與其他層面的聯結關系,一種展示和發展空間,一種以提供信息為核心的服務平臺。而這樣的樞紐功能、驅動功能,黨報相對于網絡媒體而言,有著太多的優勢。
毫無疑問,未來的媒體內容可分為兩種,一種是隨處可見的“免費”信息,一種是需要支付成本的“高附加值”信息,黨報的優勢就在于做好這種“高附加值”信息,因為“人們會為那些能幫助他們賺錢的信息付錢”( 硅谷創業之父保羅·格雷漢姆)。更重要的是,這種“高附加值”信息以及黨報“樞紐型媒體”的功能,是黨報開展新媒體建設的最優質也是最獨特的資源。
以“用戶圈”為核心建設黨報新媒體
觀點:新媒體的本質不僅是傳媒,更是平臺。新媒體建設的核心不僅是信息,更是用戶。
1.新媒體建設應以內容傳播為主嗎?
縱觀這幾年來傳統紙媒所辦的新媒體,不管是網站、微信、App,鮮有成功者,就建設方向而言,其根本的誤區是把新媒體當成了單純的媒體,當作傳播信息的介質,希望走“傳播信息——吸引受眾——出賣注意力”的贏利模式。事實上,這種傳統模式在當前的報紙經營中都已經面臨考驗,用在新媒體中更無異緣木求魚。在這樣一個信息爆炸時代,就一家網絡媒體而言,既無壟斷的信息渠道,又缺乏專業的權威人士,那又有什么信息是受眾非看不可的?又有多少信息是受眾真正感興趣的?要用多少人、多少錢才能采集到、傳播出真正有價值的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少以傳播信息為主要內容的網站、App、微信公號,不是新媒體,而是傳統媒體。
當然,以傳播信息為主要方式而較成功的自媒體并非完全沒有,比如微信訂閱號粉絲較多的大致有這幾類:專業類,面向某一專業的從業人士;愛好類,面向某一類愛好者,如教人打球,教人書畫,教人做菜;實用類,吃喝玩樂、養生保健、投資理財、穿著打扮;公知類、明星類等等。這些微信訂閱號,有幾個特征:一是內容無法推廣模仿,比如教人打羽毛球,可以同時有幾個十幾個微信,但不可能全國有幾千個;二是開設者必須是本行業最有知名度的專家,而這樣的專家全國也就幾個十幾個;三是粉絲分散來自全國各地,開展線下活動較難;四是贏利模式并不明顯,只叫好不叫座。從這點來看,類似這樣的新媒體,非但不是紙媒之所長,而且也無法模仿。
似乎可以這樣認為,以傳播信息為主要內容的新媒體,是很難成功的。現在報紙紛紛在做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習慣于把記者采寫的稿件改頭換面移到網絡上,真正成功的幾乎沒有,其深層的原因就在這里。即使偶爾有幾個做出了影響和效益,但細細考察,如果用公司制的標準來核算,其實并不贏利。更要命的是,所謂的贏利,在很大程度是依賴了報紙品牌,通過報紙的傳播來“轉化”為微信的贏利,無非是自欺欺人而已。
2.從讀者、受眾到參眾、用戶。
自新媒體興起以來,傳統媒體對新媒體,從開始時的漠視、排斥,到后來的接受乃至主動融合,其過程的背后,實質上是傳統媒體在新格局下對于受眾群體需求認識的轉變過程。而其最為關鍵的“角色轉變”,就是傳播對象從被動的“受眾”變成互動的“參眾”,正如美國學者丹·吉摩爾所說的:“此前被稱為受眾的人們現在成為‘參眾’,那是一種不同的關系了,核心就在‘我’的參與。由‘我’的訴求、進入‘我’的圈子交流、獲得‘我’的愉悅性體驗,這是信息社會新老媒體的根本區別。”也就是說,對“我”——參眾的重視與開發,是新媒體建設的出發點和根本點,一旦做到了這一點,“參眾”也就自然成為“用戶”——可以營銷的對象。
參眾或者說用戶,對于新媒體建設的價值,可以從一個簡單的事實來說明。眾所周知,為提升新媒體的影響力,不少報社號召采編人員向自己辦的新媒體發帖,有的還出臺了獎勵措施,但往往收效甚微。而與此同時,同樣一個人,在他的微信朋友圈、微信群里,在他參與的網絡論壇里,盡管沒有一分錢的報酬,卻發帖發得不亦樂乎。這里原因,不外乎三個:一是傳播欲,有了一個好的想法,有了一句妙語,必欲說之而后快;二是成就感,當自己說的話引來一片點贊、眾多評論,其成就感不是幾十塊錢的稿酬所能取代的;三是提升力,在這個圈子里,可以學到自己想學的東西,同時還可以提升自己的形象。而這三點能夠成立,前提是“我”必須在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斷刷新自己的存在感,也就是說,“我”是一名活生生的“參眾”,是這里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不是一名幾萬分之一的簡單的“受眾”。
所以,新媒體(微信朋友圈、QQ群、微博群、網絡論壇)其實就是個“江湖”。每個人行走江湖,總希望自己能交到郭靖、令狐沖這樣的朋友(社交功能),希望向黃藥師、周伯通學點功夫(提升自己能力的工具),希望在闖出個好名聲,人家尊一聲“大俠”(成就感),希望有朝一日從張君寶成為張三豐(提升自我形象的平臺)。一旦能給他建起這么一個江湖,其對江湖的“黏性”是可以想見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黨報的新媒體建設之路,就是以“廟堂”之尊,充分發揮樞紐型、驅動型媒體的功能,打造一個個“用戶圈”——草根者的夢想江湖,而報紙的新媒體建設戰略也就呼之欲出了。
3.以“用戶圈”為核心建設新媒體。
“用戶圈”,是借用商業營銷中的一個概念,在新媒體建設中,是指黨報利用自己的聯結各方尤其是政府部門和群眾團體的樞紐作用,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和權威性,利用各種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融合的優勢,組成一個個有著高度同質化、高度影響力的新媒體“用戶圈”,在此基礎上,擴大傳播的影響力和有效性,并開展各種營銷活動。其本質是把新媒體作為社交的平臺,把用戶作為新媒體建設的核心。
“用戶圈”具體如何打造?黨報發揮自身優勢,聯合有關政府部門和社會團體,充分利用已有的組織網絡,在微信、微博、QQ、網站論壇、App上建立起一個個社交圈。比如說,地市黨報可以和文化局、文聯、攝影家協會(一般說來,由于報社在攝影上的專業化水準和專業化人才,在當地的攝影家協會中有著強大的影響力),以報社的攝影部門為核心,以某個攝影記者(一般在當地攝影圈里有著較強的號召力)為主要運營官,在微信上建立一個“某報·攝影家”的微信群,在QQ上建立一個“某報·攝影家”的QQ群,在報社的網站上建立一個“某報·攝影家”的論壇,建立一個“某報·攝影家”的App,在報紙上定期開一個“某報·攝影家”的專欄,依托協會,依托報社,開展各種活動,努力使這個圈子活躍起來,在當地產生較大的影響力,而報社則理所當然地成為這幾個圈子的后臺。
與此相仿,報社的各個部門,根據部門和采編人員的優勢,細分各個條線,充分發揮報社的“樞紐功能”,做類似“某報·名師”“某報·名醫”“某報·名律師”“某報·社工”“某報·旅游”“某報·車友”“某報·青年企業家”“某報·書畫家”“某報·收藏家”之類的“用戶圈”(自然還可以分得更細),從而形成一個由數十個乃至上百個“用戶圈”矩陣。
類似的做法其實不少報社已在嘗試。像羊城晚報報業集團就通過細分人群、細分行業,以家庭、社會精英和90后為重點對象,建立了面向特定人群的網站群、有20萬粉絲的微博矩陣和已擁有16個賬號的微信矩陣。《錢江晚報》在2013年下半年,以《錢江晚報》官方公共賬號為龍頭,推出了“杭州吃貨”“杭州房產”“浙江名醫館”“悠游天下”“好攝之友”“錢報車友會”“升學寶”等26個子賬號,組成矩陣,累計吸附粉絲超過40萬。
“用戶圈”隱藏著商業開發的巨大潛力。從本質上看,這實際上是把黨報的政治優勢、宣傳優勢、社會資源轉化為新媒體環境下的優質資源,把黨報影響力轉移到“線上”,把“二次售銷”變成多維度銷售,把單一的廣告模式變為協同利潤模式,實現產品的多樣化,收入渠道的多元化。這樣的“用戶圈”,首先是高度同質化的,是某一類產品的目標人群,有利于精準營銷;其次是各個階層中的代表人物,通過他們可以影響一大批愛好者,營銷的效率相當高。第三是這些人在當地可算精英,在社會上影響力強,可以圍繞著這些人搞一些活動,提升報社的品牌影響力。總之,在這樣一個“用戶圈”中,報紙可以通過大數據找到用戶需求,用戶也可以借此滿足個性化消費。如果說,紙媒做廣告是“普降春雨”,雨下了很多,但具體到某一塊田、某一株苗是否澆到、澆到的是否需要,或多或少要打上一個折扣,而“用戶圈”則是充分體現互聯網時代的“滴灌式” 營銷,精準化、滲透式、點對點,效率十分高。
其實在商業領域,“用戶圈”營銷的成功案例并不鮮見,典型的如寧波范小米化妝品有限公司,范小米和她的團隊在營銷上最大特點,就是不以產品為導向,而是以人為導向,通過加強相互社交解決客戶體驗和信任的問題,用優質內容打造平臺和社區,從而把目標用戶圈進來,有了大量目標用戶之后,用戶會告訴你他們真正需要什么產品。這樣“滴灌式”的營銷成功率相當高,所以只用了8個月的時間,通過賣化妝品賺了三千多萬,而其社區平臺,粉絲量已達120萬。
“用戶圈”可以充分發揮黨報的優勢。建設“用戶圈”為核心的新媒體,可以把黨報樞紐型媒體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而這些恰恰是其他的團隊或個人所難以做到的。一是政府資源。可以把政府部門、群眾團體對某一個階層(如攝影家、企業家、書畫家)的影響力,通過部門的協調組織,為我所用。二是宣傳優勢。可以通過各種媒體的宣傳,幫助“用戶圈”的人在社會上提升知名度和影響力。三是人才優勢。媒體的記者編輯,對各個條線、各個領域的情況熟悉、人頭熟悉,對宣傳業務更是專業。當然,這里還有個角色的轉換,如胡舒立所說的,要從記者編輯向產品經理改變。四是有團體優勢。互聯網是“物以多為貴”,這樣的“客戶圈”,一個兩個可能成不了氣候,但如果同時做幾十個,形成了一個矩陣,聲勢和能級就不一樣了。能同時建起十幾個“客戶圈”的,大概也只有報社這樣的單位才做得到,任何個人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