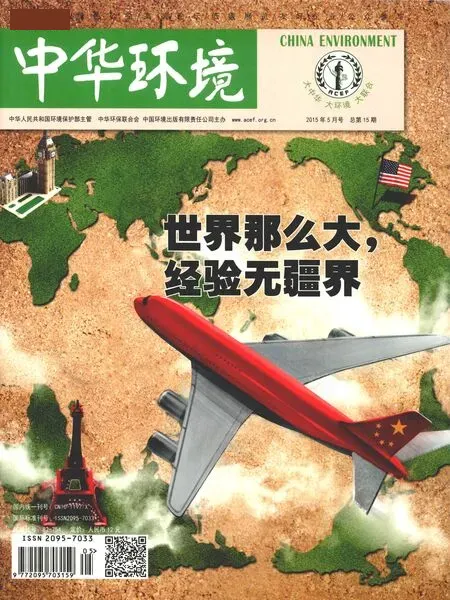《美國超級基金法》能否“洋為中用”?
劉曉星
《美國超級基金法》能否“洋為中用”?
劉曉星
35年前,美國為了治理企業搬遷后遺留下來的有毒“棕色地塊”,出臺了超級基金法。實踐證明,只有將污染場地防治制度上升到法律層面,才能把監督、修復落到實處。目前,我國這方面總體上還處于立法缺位的狀態。
“棕地”是國際上對高污染、高耗能企業設施搬遷后遺留下地塊的統稱。美國國會1980年通過了《環境應對、賠償和責任綜合法》,批準設立污染場地管理與修復基金,即“超級基金”,授權環保署對全國“棕地”進行管理。政府以這一基金為核心,制定了全面有效的“棕地”管理框架,從環境監測、風險評價到場地修復都建立了標準的管理體系,為污染地塊的管理和土地再利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但是,《美國超級基金法》自誕生之日起就充滿爭議,也引發美國工業界尤其是那些“百年老店”的不滿,甚至有家全球著名的公司還向聯邦法院數次提起了《美國超級基金法》違憲之訴。那到底該如何評價這部法律?其“不同以往”的特色是什么?在解決美國歷史遺留的污染方面成效幾何?是否能夠“洋為中用”?日前,由專家、學者以及部分媒體代表聚首北京,出席由環保部宣傳教育中心“我的綠色大學”主辦的研討會,就《美國超級基金法研究》一書進行解讀。
當“愛河”變“毒河”,推動立法意義幾何?
《超級基金法》治理污染場地分為四步,發現并調查污染場地;對污染程度進行定義;確定整治修復方案;進行為期五年的跟蹤監測。
1978年春,離尼亞加拉瀑布不遠的紐約州拉夫運河(Lovecanal),原意為“愛河”,一個令人傷痛且改變美國歷史的案件在這里發生。
這是典型的美國城市郊區,是藍領集中的社區。這里環境宜人,工薪一族在這里擁有自己的住房,他們生兒育女,生活美滿。
洛伊斯·吉布斯是一名家庭主婦,有兩個孩子,5歲大的兒子麥克患有肝病、癲癇、哮喘和免疫系統紊亂癥。5年間,她絕大多數時間是在醫院兒科病房度過的。她不明白為什么兒子小小年紀竟會患上這么多奇怪的病癥。有一天,她偶然從報紙上得知,拉夫運河小區曾經是一個堆滿化學廢料的大填埋場,于是她開始懷疑兒子的病是不是由這些化學廢料導致的。
當她把自己的懷疑說給鄰居們聽的時候,許多人也產生了同樣的懷疑。隨后吉布斯聯絡了一些姐妹開始進行調查,看是否還有類似遭遇的家庭。結果她們吃驚地發現了一個又一個家庭都曾出現流產、死胎和新生兒畸形、缺陷等經歷。此外,許多成年人體內長出了各種腫瘤。
隨即,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被曝光:1947年到1952年之間,當地一家名為胡克的化學工業公司把含二惡英和苯等82種致癌物質、共21800多噸重的工業垃圾傾倒在該運河中。運河被填埋后,這一帶便成了一片廣闊的土地。
1954年,胡克公司將垃圾埋藏
封存在那里之后,以一美元的價格將土地賣給了當地的教育委員會,并附有關于有毒物質的警告。然而,政府明知土地已被污染,仍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小學。不久之后,小學周邊的地區開始繁盛起來,逐漸形成了今天的拉夫運河小區。新來的居民哪里知道有毒物質正在滲入他們的社區?那些化學廢料逐漸滲出地面,威脅著人們的健康。
這一事實的揭露令小區居民震驚不已。人們走上大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進行更加詳細的調查,并做出合理的解釋和相應的措施。
1978年4月,當時的紐約衛生局局長羅伯特·萬雷親自前往視察,他親眼見到以前埋在地下的金屬容器已經露出了地面,流出黏乎乎的液體,像是重油一樣,又黑又稠。
4個月后,紐約衛生局宣布小區處于緊急狀態。拉夫運河小區的居民們意識到必須團結起來,他們扣留了美國環保署代表作為人質,要求白宮答應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疏散居民,并宣布這里是重災區。
一時間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各路媒體也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紛紛發表文章譴責政府,宣稱支持居民的行動,呼吁政府就這一丑聞盡快做出解釋,并妥善解決。
幾天后,居民們終于得到了回應。卡特總統頒布了緊急令,允許聯邦政府和紐約州政府為尼亞加拉瀑布區的拉夫運河小區近700戶人家實行暫時性的搬遷。
7個月后,也就是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環境應對、賠償和責任綜合法》,規定由聯邦政府設立專門的基金,并授權環保總署組織對污染場地進行治理, 同時向污染場地的責任人追回治理費用。超級基金法案主要針對的是廢棄或已經被再開發的場地,那些仍在使用中的場地上發生的污染由之前頒發的“資源保護和回收法案”來管理。因為該法提出設立“超級基金”來為污染去除或環境修復提供資金,故在實踐中又稱該法為《美國超級基金法》。
事實上,早在拉夫河事件發生前,美國就出現了一引起歷史遺留污染造成的公眾健康受損案例,只是因為規模較小未曾引起廣泛關注。雖然在《清潔水法》、《資源保護與恢復法》以及《有毒物質控制法》中有零散的規定,但是無法為清理歷史遺留污染場地和消除對公眾健康的隱患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尤其對那些法律生效前產生的污染問題的追責,更是束手無策。
環保部宣傳教育中心主任賈峰帶領青年研究團隊用3年時間完成《美國超級基金法研究》的編著。
賈峰表示,上世紀,美國“拉夫運河事件”的爆發政府處置不力以及隨后政府必須承擔數十億美元的沉重財政壓力,讓國會面臨失職的指責,迫使國會在1980年后半年加速了立法進程,最終在當年國會休會前,以《危險廢棄物污染法》為藍本,在吸收另外三個方案內容的基礎上,出臺了《綜合環境反應、賠償和責任法》,并獲得通過。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美國超級基金法》的出臺源于公眾的不滿和輿論的壓力,促使該法成為美國乃至全球環境法律中嚴刑峻法的典型。
根據《超級基金法》的治理方式,第一步,通過環境管理部門監測、公眾檢舉、土地使用者通報、土地用途改變過程中的污染檢測等方式發現污染場地,并對污染場地進行調查。第二步,根據污染危害評分系統的相關指標,對污染程度進行定義。符合標準的場地將被列入《國家優先治理污染現場順序名單》(NPL)。第三步,對納入NPL名單的污染場地進行整治調查與可行性研究,再由聯邦政府提出《整治修復方案》。該方案經社區民眾參與討論并提出建議后,由政府形成決策報告書。第四步,當修復達標后,還需進行5年的跟蹤監測,確定穩定達標時,可將其從NPL中刪除。
如何找出潛在責任方?
《超級基金法》打破了法律界、學術界、司法界多年不變的原則:法不溯及既往。按照《超級基金法》,此前的許多污染行為即使當時是合法的,也應依法承擔污染物清理或環境修復的法律責任;責任人之間是無限連帶的,可以只針對其中一個或幾個實力雄厚的潛在責任人提起追償訴訟。
我國2014年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全國土
壤的點位超標率為16.1%,重度污染占比1.1%;耕地的點位超標率為19.4%,重度污染占比1.1%。更糟糕的是,其中很多超標點位屬于歷史遺留的污染場地。

武漢漢陽,漢江邊原武漢農藥廠片區進行土壤修復治理。CFP/供圖
這一切,誰來埋單?“關于歷史遺留污染場地的治理,目前國內主要有兩種不同意見。”賈峰告訴記者,一種觀點認為,應在堅持法不溯及既往的前提下,由政府對其治理;另一種觀點認為,完全由政府治理財政壓力過大,放棄對污染者的追究也不盡公平合理。
其實,歷史遺留污染場地治理責任承擔問題并不是一個新課題,拉夫運河事件的爆發,讓現行法律的缺陷暴露——當時,民意認為若污染者不承擔消除污染或環境修復的責任而由政府兜底實則是公眾來埋單,那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環境法律責任主體是誰?《超級基金法》規定的責任主體不僅包括污染物排放者和排放時的業主,還包括該不動產當前的業主或使用人。1996年《超級基金法》修正法案規定:“污染設施的信托人對保管期間的污染應在其實際保管的財產價值范圍內承擔責任。”對于污染事故負有責任的高管人員也被列入責任主體范圍。
更重要的是,“《超級基金法》打破了法律界、學術界、司法界多年不變的原則:法不溯及既往。”賈峰表示。他說,按照《超級基金法》,此前的許多污染行為即使當時是合法的,也應依法承擔污染物清理或環境修復的法律責任;責任人之間是無限連帶的,可以只針對其中一個或幾個實力雄厚的潛在責任人提起追償訴訟。
《超級基金法》以追溯既往的方式對整治和修復義務規定了嚴格的無限連帶法律責任。任何一個責任方均可以被要求向政府或受害人賠償全部污染治理和損害賠償的費用。無論某一責任方主觀上是否有過錯,均應承擔責任。該責任并不會因為責任方屬于責任有限的組織形式而受到限制,任何對其控股或參股的組織或個人均可能成為責任主體。即使法律行為或法律事實發
生在《超級基金法》頒布之前,并在當時被認為是合法的,也不能免責。
應該說,《美國超級基金法》的責任機制突破了過去約定俗成的法律原則,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嚴格的責任機制對污染者產生了巨大的震懾作用,為源頭控制污染作出巨大貢獻。
為了促進反應行動快速有效地進行,相較于美國其他環境法律,《美國超級基金法》賦予行政機關更為強有力的反應權力,也建立了相應的權力制衡機制。該法授權總統對危險物質的釋放或釋放威脅進行處理,總統有權(或者說有義務)采取清除行動以及相關的修復行動來保護公眾健康和環境安全。總統又將該項權力授予國家環保局,并敦促其他內閣部門密切配合。強力授權和有效制衡對于法律的順利實施、反應行動的迅速開展以及污染場地的快速清理起到了積極作用。
費用如何確定及負擔?
《超級基金法》規定,政府和公民均可以對責任方提起“司法檢控”程序。
在污染場地被發現和緊急危險被處理后,美國環保局開始查找潛在責任方。這些查找技術包括查閱場地文件記錄,尋找場地內桶罐和材料上的名字,或是采訪場地的前雇員和鄰居。一旦確認了潛在責任方,美國環保局將用信件通知他們。信件介紹美國環保局用于確認潛在責任方的信息,并鼓勵他們與美國環保局合作來承認對場地清理修復負有責任。
潛在責任方可能需要負擔全部清理修復費用。因此,能在前期與美國環保局談判中獲得公平合理的清理修復計劃,將從長遠上節省清理修復的時間和成本。
如果潛在責任方不予合作,美國環保局既可通過訴諸法庭強制要求責任方清理修復,也可以利用超級基金的資金開展修復。
根據規定,場地所在州應分擔聯邦的清理修復成本,州政府必須承擔至少10%的清理修復費用,并且負責場地的運營和維護。
當污染責任方無法被識別或無力支付清理修復費用時,美國環保局使用信托基金即超級基金中的錢清理修復污染最嚴重的場地。
“超級基金”先行墊付費用,然后通過訴訟等方式向最終責任方追索。資金將被用于支付以下費用:“不屬于《國家應急計劃法》管轄范疇的遷移和補救費用;任何個人實施的不屬于《國家應急計劃法》管轄范疇的其他“必須”的責任費用;申請人因他人污染而造成的對“自然資源”的損害并且該種損害無法獲得司法救濟;對環保治污技術研發的資助以及對地方政府治污費用支出的補償。”
超級基金的主要來源先后包括原料稅、環境稅、財政撥款經費以及對責任的追償費用和罰款。根據美國政府績效辦公室的報告,截至2007年財政年度,超級基金總計融資423億美元,算上責任人主動修復污染場地花費的225億美元,總金額達到648億美元。此外,聯邦和州政府啟動了棕色地塊再開發計劃、州自愿治理計劃等項目,推動私人資本參與較輕污染場地的修復治理和再開發,上述各項經費來源為《美國超級基金法》的實施及相關修復治理計劃提供了充裕的資金保障,確保法律出臺有足夠的實施資金。
《超級基金法》如何“洋為中用”?
如今,《超級基金法》已實施30余年,雖然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一些爭議,但成效也顯而易見:據統計,自1983~2008年,超級基金項目共清理有害土壤、廢物和沉積物1億多立方米,清理垃圾滲濾液、地下水、地表水約12.9億立方米,為數萬人提供了潔凈的飲用水源。截至2014年6月,1158塊場地已完成修復工程,占累計列入國家優先治理名錄場地的68.1%。為推動地下水修復技術向前發展,EPA設立了“超級基金創新技術評價”標志和場地清理技術交流平臺,鼓勵企業與科研單位的技術創新。
正如賈峰所言:《美國超級基金法》的實施還產生了諸多不可量化的效益,例如提升被修復場地及其周邊社區的公眾的愉悅感、減少土地資源閑置和浪費、推動環境保護的公眾參與和信息公開、防止危險物質不受控制的釋放、提高政府與公眾的應急反應能力等。《美國超級基金法》的實施還催生并發展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等一系列新型環境治理工具,對美國的環境管理創新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此外,該法最為顯著的一個不可量化的效益在于其對企業的巨大威懾作用,促使企業迫于法律威嚴而重視環保,使諸多的污染問題在源頭得以預防。
然而,即使如此,美國的超級基金法案支持下的棕地治理仍然存
在不足和爭議。專家認為,該基金在“棕地”修復上效率過低,由于需要律師訴訟,很大一部分的資金和時間被用于漫長的司法程序,并且修復的時間極長,通常修復一個場地需要幾年到十幾年的時間,與此同時,其資金的來源缺口越來越大,每年資金數量都在銳減,這些都不利于嚴峻的“棕地”治理現實。
對比美國和我國搬遷企業遺留場地的開發,我們發現,對搬遷企業遺留場地再開發過程中各利益相關方責任的規定對場地的再開發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歷史上美國法律對于開發商責任的規定過于廣泛和嚴厲,嚴重阻礙了遺留場地的再開發;美國的法律法規越來越傾向于減免開發商的責任和風險,越來越鼓勵地方政府強制進行棕地的治理和開發;但開發過程仍然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性,開發商對開發棕地仍然不夠積極;國內現有的搬遷企業遺留場地開發模式非常粗放,沒有具體規定各利益相關方的責任,特別是污染者的治理責任沒有得到體現;各方對于開發涉及的責任和風險的意識非常淡薄。這種粗放的開發模式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導致各方之間的糾紛,妨礙搬遷場地的順利開發。

南京利用生物對黑臭河“打針吃藥動手術”CFP/供圖
中國污染場地修復立法缺位
除美國的《超級基金法》外,加拿大的《國家污染場地修復計劃》、日本的《土壤污染對策法》等,都是針對污染場地預防和治理的專門法規。只有將污染場地防治制度上升到法律層面,才能落實到實處。目前我國這方面總體上還處于立法缺位的狀態,業內專家建議,借鑒《超級基金法》的立法經驗,盡快建立我國的污染場地管理法律體系,是環境保護工作中的重要任務。
在立法中,應制定針對不同類型污染場地的監測和修復技術規范,根據土地的不同功能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污染程度認定與修復標準,以及修復效果的評價標準。明確污染場地調查、治理、評價及監督的法定程序。應在明確對責任方以追溯既往的方式承擔嚴格的無限連帶責任的同時,規定當責任方暫時不能確定、無力支付或情況緊急時,由“專項基金”先行墊付治理、賠償費用,并由“專項基金”向責任方追償。對于基金的來源可以采用多種渠道,包括稅收、高污染企業提交的保證金,以及社會資金等。對于基金的建立,要給予應有的政策拉動和保護。同時,對基金的運作程序,分配方式作出明確的規定。為實現基金的優化運用,應借鑒《超級基金法》,建立污染評分系統,制定“污染場地優先治理順序名單”,名單中應動態反映污染場地的區域、時空分布,污染的面積、類型和污染程度等數據。
由于土壤污染的隱蔽性和不可逆轉性,污染場地在我國應引起足夠的重視。美國《超級基金法》及其相關制度的實施為我國提供了寶貴經驗。國外的經驗表明,僅依靠環保執法人員,難以及時發現污染場地,必須依靠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我國應結合國情,合理借鑒,從立法層面上和行政層面上共同促進,從政府層面和社會層面上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