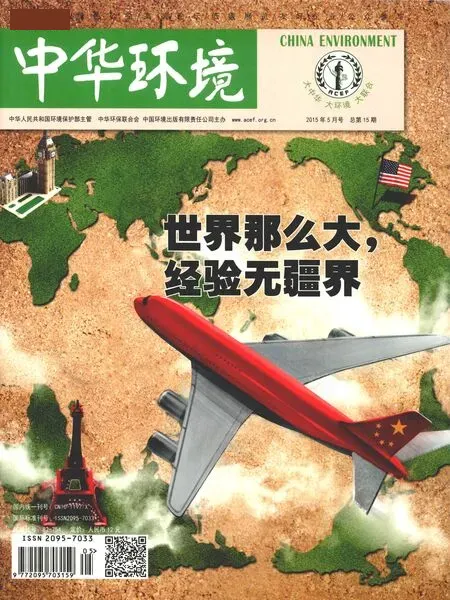日本:法治戰勝污染
李蒙
日本:法治戰勝污染
李蒙
法律把環境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要求在"循環"、"共生"、"參與"及"國際合作"四項原則下,使社會經濟活動最大程度地減少對環境造成的負荷。
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也曾是環境污染的大國,其污染的嚴重程度,跟當下的中國差不多。但如今的日本,無論走到哪里,都是天藍水碧,街道整潔如新,看不到絲毫污染的痕跡。在日本治理污染的成功經驗里,法治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很值得中國借鑒。
立法不斷完善
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初,日本經濟取得了年增長率達10%的高速發展,但工業化和不斷增加的能源消耗,也產生了嚴重的大氣污染和其他形式的環境污染。與之相生相伴的,各個城市相繼制定防治污染條例。1950年開始,戶畑市(現在的北九州市)受排煙危害的地方婦女會就展開了反污染示威。1955年,東京雖制定了《防止排煙條例》,但在高樓鱗次櫛比的市中心,一到冬季從采暖鍋爐排出的黑煙,使市民依然很難看見太陽。
自1955年起,四日市地區引發了“哮喘問題”,惡臭使得中小學校即使在炎熱的夏天也不能開窗戶上課。在千葉縣、岡山縣、名古屋市,污染也同樣嚴重,發生了由于排煙而使草木枯萎的事情。在川崎、尼崎、北九州等地,大氣污染引發了市民的慢性支氣管炎和支氣管哮喘病。1968年,政府正式認定,熊本的新日本氮肥株式會社(TISSO株式會社的前身)和新瀉的昭和電工株式會社的排水是產生水俁病的原因;三井金屬礦山株式會社的排水是“痛痛病”的原因,從而明確了這些健康損害是由于工業污染所致。
不斷加重的大氣污染和其他環境污染使日本國民和政府都認識到,必須制定法律來防治工業化引發的環境污染。日本的第一部空氣污染控制法是《煤煙排放控制有關法律》,于1962年12月正式生效。日本將環境污染稱為“公害”,1967年制定了《公害對策基本法》,并在1970年的“公害國會”上進行了大規模的法律修訂和新法制定。此屆國會修訂的《公害對策基本法》和《防止大氣污染法》,成為日本大氣污染對策的最重要的法律基礎。
1970年,日本公布(或修改后重新公布)了14項有關公害的法律,除《公害對策基本法》和《大氣污染防止法》外,還包括《道路交通法》、《噪音管制法》、《廢棄物處理法》、《下水道法》、《防止公害項目費企業負擔法》、《防止海洋污染法》、《有關人體健康的公害犯罪處罰相關法律》、《農藥管制法》、《防止水質污濁法》、《自然公園法》、《有毒物及劇毒物管理法》等。
1971年,日本成立了環境廳,各都道府縣、各市町村也都設置了政府環保機構。這些法律和機構,形成了直到今天仍高效運行的治理公害的框架。1993年,日本通過了《環境基本法》,對有關治理公害和保護環境的法律進行了進一步修改完善。
從《公害對策基本法》發展成為《環境基本法》,標志著日本的環境政策的基本思路發生了重大轉變。不僅是城市生活型的大氣污染
和水質污染問題,還有其他領域,如廢棄物、化學物質引起的對環境損害的風險問題、自然及生態系統的保護問題、生物多樣性和全球變暖等問題,都是《環境基本法》和基于該法的環境基本計劃的基本目標。這部法律把環境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要求在“循環”、“共生”、“參與”及“國際合作”四項原則下,使社會經濟活動最大程度地減少對環境造成的負荷。

日本東京,數百名反核人士集體躺倒,在日本環境省大樓外舉行擬死示威。示威者要求對核災難受害者提供補償,移除放射性物質并要求環境大臣Nobuteru Ishihara下臺,后者曾表示只要給錢,地方政府與民眾就會支持放射性物質存儲計劃。CFP/供圖
當時的污染對策體系的主要內容包括:一,依據《公害對策基本法》針對工業界制定污染物排放控制標準;二,為恢復環境、補償損害和控制污染的目的,對工業污染源收費,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污染者負擔原則;三,設置環境廳作為一元化的行政部門,依據上述法律和原則賦予其環境方面的規劃、立項、執行的責任和權力。
污染受害者司法訴訟
環境立法后,嚴格執行法律也非常重要。1970年后,日本的地方公共團體興盛起來,每年提出大量的公害意見,都能得到政府的及時回應和依法處理。1970年地方公共團體提出的公害意見合計59467件,其中大氣污染12911件,水污染8913件,土壤污染67件,噪音、震動污染22568件,地基沉降11件。之后逐年增高,到1972年達到21576件。此后,開始下降,到1979年,降到14591件。到1979年,日本的大氣污染在許多地方都得到了比較好的治理,空氣質量明顯改善。
日本的環境污染受害者能通過司法訴訟從污染企業那里得到損害賠償。本來,通過民事訴訟途徑請求損害賠償時,受害者必須舉證傷害的發生、加害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加害者的故意與過失,以及受害者的權利或利益受到非法侵害的證據等。可是由于在大氣污染等污染訴訟中,科學地證明環境污染行為與健康損害的因果關系相當困難,同時不可缺少的數據往往掌握在作為被告的企業手中,原告沒有數據。為解決上述問題對司法的制約,從當事人地位平等這一原則出發,出現了不少在審判過程中減輕受害者舉證責任的判例和觀點。
另外,許多大學科研機構對環境污染展開流行病學調查,他們的科學結論為受害者提供了證據。例如,在四日市污染訴訟案中,原告方
列舉出三重大學吉田克已教授等接受四日市地區大氣污染對策協議會委托所進行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證明了大氣污染與呼吸器官疾病的發病率之間的確鑿的相關性,在大氣污染民事審判方面做出了劃時代的努力。基于已經清楚了邏輯關系的流行病學調查,1972年7月法院作出了四日市污染判決,駁回了被告企業提出的已采取當時最新的技術措施防止污染的這一主張。并強調,企業如果排放可能危及人體和生命的污染物,必須不計經濟費用,采用最先進的技術和知識進行預防,否則就難免形成過錯。

日本川崎市環境綜合研究所。李蒙/攝
國家無過錯損害賠償制度
1972年,日本頒布了《大氣污染防止法和水質污濁防止法的局部修正法律》,其中規定:即使損害造成者不是故意或者無過錯,由于環境污染行為而發生受害者超出忍受極限的損害時,也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1973年6月,《公害健康損害補償法》出臺,它不僅有利于熱切盼望獲得賠償的受害者,而且對因污染頻發使生產活動受到影響的產業界建立某種保險制度。
在《公害健康損害補償法》中,認定受害者有制度性的規定,即先指定大氣污染顯著且在其影響下疾病多發的地區(指定地區),在該地區住所或工作場所暴露在大氣污染下超過一定時間(暴露條件)的人,如果患上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哮喘性支氣管炎及肺氣腫以及并發癥(指定疾病),則認為這些人的疾病與大氣污染之間有因果關系。
補償費的給付總額在一定時期超過了千億日元。
根據補償法,由地方行政長官認定的健康受害者,除負擔其醫療費以外,還要補償他們由于污染相關的疾病所造成的其他利益損失。此外,還決定,為了幫助被認定者恢復、保持和改善因特定疾病而造成的健康損失,實行一些與污染相關的健康和福利活動是非常重要的。
實施健康損害補償制度所需的費用,根據大氣污染物的排放率來確定,工廠、作業場等固定發生源和汽車等移動發生源之間的費用分擔比例,在大氣污染物中,考慮了全國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情況,確定為8∶2。固定發生源所負擔的8成補償費用,由全國一定規模以上的工廠、作業場分攤。各個工廠、作業場的分擔比例,以硫氧化物為指標,根據其排放量的大小來確定。
根據本制度確定的指定地區,到1978年由開始時的十二個增加到四十一個,1988年認定患者人數達到了10萬人,補償費的給付總額在一定時期超過了千億日元。
治理污染不斷取得成效,每年認定的患者人數在不斷減少,指定的污染地區也不斷減少。 1987年,修正了《公害健康損害補償法》,第二年3月取消了與大氣污染有關的全部指定地區。解除指定地區時認定的患者總數大約是11萬人,整個14年期間被認定的患者總數約達為18萬人。對原來制度下指定地區已認定的患者,只要所患的是指定病種,則繼續得到補償。到1995財政年底,認定患者人數約有74000人,該年度所支付的補償金額為869億日元。從實施公害健康損害賠償制度開始到1995年底為止,累積補償金額達到了16600億日元。
通過在法律框架下政府主導企業積極應對的不斷減排政策,通過司法訴訟和無過錯損害賠償制度,日本的環境污染得到了有效的防治,污染受害者也都得到了應有的賠償,這些經驗和作法都非常值得中國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