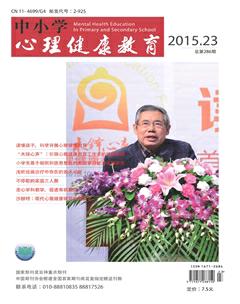遇見“例外”,讓星火得以燎原
饒一
2015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首屆“木鐸心聲”心理健康教育高峰論壇在北京如期舉行。我很榮幸作為“邊玉芳名師工作室”成員參加了此次培訓。培訓的內容除了聽取全國各地高校心理學專家的報告外,其中有兩天兩夜的工作坊時間,我們重慶過去的工作室成員被安排在了“看見例外”工作坊,給我們培訓的老師就是美國德克薩斯州大學琳達·梅特卡爾夫教授。
從北師大培訓歸來,感覺整個人心平氣和了許多。這一次的培訓,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原來,每一個我們認為的“問題孩子”,都有其“例外”的一面。而那一面,就好比黑暗中的一點星火,如果我們有幸發現了它,也許這點點的星火在我們的呵護下就能逐漸蔓延開來,照亮黑暗。
琳達教授用了兩天的時間,列舉了大量理論依據和案例來向我們論證:遇見“例外”,是一種救贖。每一個前來做心理咨詢的孩子身上,都有“例外”,而這個“例外”不容易被發現,在被大量問題覆蓋之下,那一點點值得驕傲的“例外”顯得微乎其微,所以,不管是心理醫生還是班主任,都要有一雙善于發現“例外”的眼睛,并不斷地挖掘再挖掘,因為,如果有幸發現了這一點點的“例外”,就意味著我們很有可能拯救這個問題孩子,讓他忘了過去種種的不好,重新接納自己。
在培訓期間,學校正在舉行運動會。由于擔心下雨,所以運動會提前了。說實話,學生們有點措手不及。我能想象沒有班主任在場,再加之副班主任又是學校的攝影老師,班級中會是怎樣一種狀況。原本我們班學生相對其他班級就有些調皮,難管理,而這一次,無疑是雪上加霜。出場的cosplay道具沒有準備,運動員口號沒有統一,“多人多足”項目的訓練沒有一次是人員齊備的,而最讓我引以為豪的“跳長繩”項目在這一次的運動會中規則發生改變,由過去的16人增至20人,而我一無所知,這就意味著又要在平時沒有參加過集訓的孩子中間臨時選拔4人,配合與默契可想而知。我每一天都通過各種渠道關注著我們班的情況。運動會的名次怎樣啊,班里的投稿情況如何啊,班級的紀律好不好……然而,結果似乎在意料之中,我們班倒數第一。得知這個消息,我有些驚訝,但又不得不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人在北京,心在學校,失落和無奈的感覺一次又一次襲來。
帶著一種失落回到了學校。第一節課,我不打算上新課。因為我覺得我有好多話想跟孩子們說。我沒有指責,也沒有批評,我的第一句話是:“說吧,孩子們,在這一次的運動會中,你覺得你表現得怎么樣?”教室里寂靜無聲。突然,有一個女孩子站了起來,接著,又有幾個孩子站了起來。我問他們為什么要站起來,肖佳琪說:“饒老師,我沒有給運動員加油,我在一旁玩耍。”何宗銳說:“我和哥哥在跑道邊追逐打鬧。”
聽孩子們在這里懺悔、自責,我心里突然有些感動。能夠主動承認自己的錯誤本來就需要很大的勇氣,在承認錯誤的同時,還能理性地分析錯在哪里,這對于三年級的孩子來說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孩子們陸陸續續地哭了。這一次的淚水,顯然是自責的淚水。
這時候,我想到了琳達老師說的話,過去已經無力改變,錯了就錯了,時光不能倒流,如果老師一直抓住孩子的錯誤不放,那么孩子可能會一直錯下去,一直被貼上“問題孩子”的標簽,最終的結果可能就是,在這個孩子的身上,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突破的“例外”了。
我原諒了主動認錯的孩子。接下來,就讓我們一同來發現這次給我們帶來慘痛教訓的運動會的“例外”吧。我對孩子們說,這一次的運動會名次已經成為了過去,老師也知道每一個運動員都盡力了,當然也有很多客觀的原因,比如賽事提前、規則改變,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們都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失敗就是失敗了,失敗了還可以爬起來,既然是倒數第一,至少我們的上升空間比前三名大得多呀!孩子們聽我這樣一說,都笑了。這讓他們有些意外,他們可能在想,這個平時動不動就發火的饒老師怎么突然變了?
在北京培訓的時候,有家長告訴我,好多孩子回到家都在說“饒老師要是知道我們倒數第一,肯定很難過,很生氣。”“遭了,這次肯定要被饒老師罵慘。”是的,過去的我,做什么事都風風火火,甚至有些急功近利,以至于孩子們怕極了我,于是他們一定想,運動會的失利肯定少不了要被饒老師痛罵一頓!
在孩子們的笑聲中,我接著又說:“想聽聽這一次的運動會中,有沒有哪個同學或者哪件事讓你感動?”孩子們你看我,我看你。
張鈺杭舉手了:“饒老師,宋國豪帶來了一盒薯片,他把薯片都分享給我們了,而他自己一點都沒吃。”緊接著,舉手的孩子越來越多。
“蘇小單沒有進決賽,他一個人躲在角落哭了。”
“趙小詩沒有參加項目,但是她全程跑來跑去給班上的運動員加油,我好感動!”
“我們班拔河的時候,十秒鐘就拔贏了對方,”
此時的我,忍不住熱淚盈眶。多好的“例外”呀!我對孩子們說,這就是我們這次運動會最大的成功!我們懂得珍惜集體榮譽,懂得分享快樂,懂得在挫折面前不放棄,如果一次慘敗的運動會能教會我們這些道理,我認為一切都值了!
在工作坊培訓期間,琳達老師給我們做了一個現場的心理訪談。來訪者是我們工作室的趙玉婷老師。趙老師說,近一個月以來,她嚴重失眠,就算睡著了也是噩夢連連,以至于整個人看著都很頹廢。說完自己的情況,琳達老師的第一個問題讓我有些意外。她并沒有詢問她失眠的各種癥狀和原因,而是問:“你有不失眠的時候嗎?當時的情景有什么不同?”趙老師愣了愣,仔細回憶,然后說道:“也有,比如,先生在身邊的時候;喝了一杯熱牛奶的時候;把燈開著的時候;看了一部電影的時候……”說完這些,琳達老師一直追問,還有嗎?還有嗎?直到趙老師再也說不上來。這時候,琳達老師說,有那么多的情景可以讓你好好睡一覺,那你為什么不給自己刻意制造這些情景,讓這些情景慢慢形成一種常規不就好了嗎?
焦點解決與病理性的心理輔導不同,它把視線放在學生擁有的資源和優勢上,認為最復雜的問題不一定要用最復雜的解決方法,永遠要關注“例外”情況。
琳達老師分享了一個她的成功案例。一個14歲的小女孩找到她。她被他的表哥性侵了。她原本不知道表哥對她所做的那些行為是性侵,是因為她在學校聽了一堂關于防范性騷擾的課之后,才意識到自己被表哥性侵了。由于不敢跟任何人訴苦,她一度想到自殺。琳達聽了她的傾訴之后,問了她一個問題:“你的祖母活了多少歲?”女孩想了想,回答:“86歲。”琳達又問她:“你想過一種怎樣的生活,我想,肯定不是現在這種狀態。”女孩點點頭:“我想過一種幸福、快樂的生活,我希望有一個美滿的家,有一個愛我的人,可我現在很痛苦,我沒有信心。”這時候,琳達在黑板上畫了一條線——生命軸。從女孩出生到14歲被性侵是一個線段,緊接著,沿著這個線段又繼續往后延伸。她解釋說:“你看,你的家族的年齡有86歲,除去14歲以前的時光,你還有72年的生命時光,在這72年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或者過你希望過的生活,這72年足夠你去完成自己的夢想,遇到你的白馬王子。”一周以后,女孩和媽媽再度來訪,女孩的媽媽說,女兒仿佛變了一個人,變得非常開心,非常愛笑,她說她有72年的時間可以去做她喜歡做的事。
故事到這里似乎有了圓滿的結尾。但我想說的是,琳達在做這個案例的時候,只字不提女孩的傷疤,而是引導女孩往前看,看到她目前困境之外的“例外”,而這些“例外”就像明燈一樣指引著女孩沖破眼前的黑暗,去迎接光明。
我知道,要改變一個“問題孩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家長、老師的共同努力,共同給予希望,當然也少不了孩子本身內心的期望和對自己積極的暗示。我相信,看見“例外”就是看見希望,就是抓住了一株絕境中的“救命稻草”。
(作者單位:重慶市南岸區珊瑚中鐵小學,重慶,400000)
編輯/張帆 終校/于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