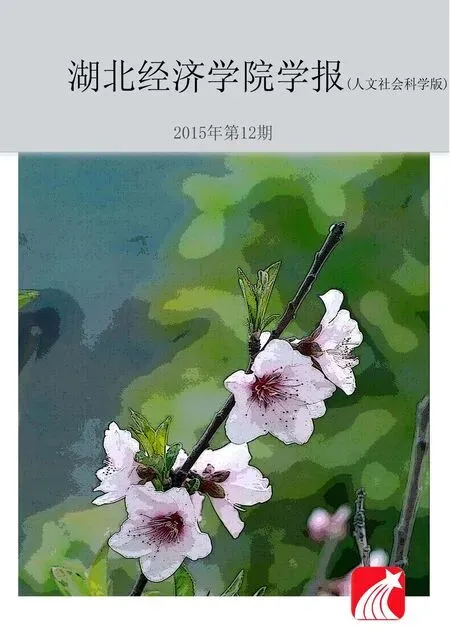逮捕必要性條件運行實證考察
——從社會危險性的視角
崔凱,茆仲義
(1.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武漢430205;2.平湖市人民檢察院,浙江平湖314200)
逮捕必要性條件運行實證考察
——從社會危險性的視角
崔凱1,茆仲義2
(1.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武漢430205;2.平湖市人民檢察院,浙江平湖314200)
2012年以來,我國對逮捕必要性條件的實踐中出現了一些偏離立法意愿的情形,整體來看,社會危險性條件已經成為批捕條件中的重要內容,但在執行中,還存在傳統思維尚未轉變,檢警存在分歧,制度不夠細化,公眾溝通不到位等問題,值得引起我們高度關注,以期為今后的改革打下基礎。
逮捕必要性;社會危險性;實證
我國在2012年修法時對逮捕制度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由于各種原因,對逮捕制度的調整雖有大改之心,但最終只形成了小改之實。①因為立法的諸多缺陷,致使我國的逮捕制度在運行中出現了各種偏差。筆者進行了專題調研,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資料。本文擬圍繞著逮捕的必要性條件中社會危險性的適用進行實證考察,以深入揭露逮捕制度中暴露中的各種問題,為今后的進一步改革提供支撐。
一、逮捕社會危險性條件簡述
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第一款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即依法逮捕。”這其中,“尚不足以發生社會危險性”條件規定較為原則。雖然最高人民檢察院對逮捕條件有著進一步具體的操作規定,但實踐中也有一些部門反映,對于社會危險性包括哪些情況、是否有程度限制,如何理解“有逮捕必要”等規定比較模糊,在具體案件中容易出現認識分歧。[1]為此,2012年修法時,立法對社會危險性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解釋,“(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三)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五)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這是從法典高度對1996年立法的一種細化。
二、逮捕社會危險性條件的實施考察
(一)逮捕率的統計分析
2012年,有媒體統計,“據近10年來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各地檢察機關的逮捕率基本在85%左右,而全國法院判輕刑率持續超過60%,職務犯罪輕刑率更是超過75%”。[2]這種對比說明了我國逮捕率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

近五年批捕與提起公訴人數對比圖②
本文所說的批捕率為檢察機關批準逮捕的人數與提起公訴的人數之比,結合上圖中的數據和以往的數據可見,我國近五年的逮捕率較之前有較大下降。即便是存在統計口徑可能不一致的因素,從上圖中均來源于最高人民檢察院歷年工作報告的四年數據可以仍然可以看出顯著變化,2010年的79.79%到2014年的64.22%可以清晰證明我國在降低未決羈押方面已經取得的巨大成績。根據相關省份人民檢察院2015年工作報告,2014年,湖北省共依法批準逮捕刑事犯罪嫌疑人31306人,提起公訴43595人,逮捕率為71.81%;浙江省全省共依法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67844人,提起公訴122050人,逮捕率為55.59%;廣東省全年共批準和決定逮捕犯罪嫌疑人133463人,提起公訴149143人,逮捕率為89.49%。由此可以推導,各省的數據和全國的數據能夠相互印證,
(二)逮捕條件中“社會危險性”的統計分析
“社會危險性”在批準逮捕中的細化是2012年修法的結果,因此相關統計并不多見。從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可以得知,2013年,全國對涉嫌犯罪但無逮捕必要的,決定不批捕82089人,比上年上升2.8%;2014年,對涉嫌犯罪但無社會危險性的,決定不批捕85206人,同比上升3.8%。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的“涉嫌犯罪但無逮捕必要”與“涉嫌犯罪但無社會危險性”為同一行為的不同表述。
在某些省份,“社會危險性”也得到了相當的重視,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敬大力檢察長透露,③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實施之后的一年半多時間,湖北省檢察機關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47137人,不批準8289人,其中因無社會危險性不捕4952人,有效減少了不必要羈押。[3]湖北省因為無社會危險性不捕的人數占總不捕數的59.74%,可見這一條件在該省批準逮捕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課題組在A省調研時也發現,該省2013年批捕人數中依據刑事訴訟法第79條第一款五種社會危險性作出決定占批捕總人數的67.3%,和湖北省的公開數據基本相仿。
為了進一步了解“社會危險性”條件的適用,我們將A省B市作為分析對象,具體調研其下轄各區縣在適用五種社會危險性情形批捕情況的數據數據。該市2013年的總體數據為,采取第一種“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作為批準逮捕理由的占整個批捕人數的約為35%,第二種“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比率為不到8%;第三種“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稍高于8%;第四種“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占不到4%;第五種“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約為12%。但具體到各縣區,五種條件的適用并沒有表現出過多的規律。如,該市檢察院批捕適用的100%均為第三種條件,而H區有73.5%的案件適用了第一種條件,T區有46.9%的案件適用了第二種條件,C縣有28%的案件適用了第四種理由,L區有32%左右的案件適用第五種理由。在一個地級市內部,這種差異已經超越了正常的犯罪類型、犯罪數量等造成的合理偏差,可見各地區對社會危險性情形的把握還有一定的適用分歧。A省檢察院在2013年進行專項檢查時發現,某區院認為其批準逮捕的5件7人都不具有五種社會危險性情形,但經復查發現有跡象或有一定證據表明有5人曾多次作案,可能歸入“可能實施新的犯罪”之中,可見各地在具體條件的歸類上可能會有一些把關不同的情況。
在具體的程序上,為了保障社會危險性條件的落實,2014年之后,我國不少省份的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聯合會簽了要求公安在申請批捕時提交社會危險性證明材料的文件,從媒體的公開報道看,昆明市官渡區、吉安市吉州區、內江市市中區等地都較好的開展了對社會危險性的審查工作,這已經成為各地檢察機關重視批捕工作的一項有力舉措。在操作上,一些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密切溝通,對于出現不提供社會危險性證明材料及提供的證明材料無證明力等問題,一般由案件承辦人要求偵查人員予以補充。
三、社會危險性條件適用的現狀評析
(一)取得成效,但“構罪即捕”思想仍待改變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法時對人權保障的重視已經得到了各地檢察機關的認可,各地在具體的執法實踐中,已經能夠普遍貫徹最高人民檢察院等上級檢察機關涉及人權保障的各種制度性規定。無論是從統計數據上看,還是從各地調研的材料看,均反映出各地檢察機關對逮捕社會危險性相關制度有一定程度的落實,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不能否認的是,“構罪即捕”思想在我國,特別是在某些基層檢察院仍然有廣泛的存在空間,這種現象的成因較多,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檢察機關辦案人員存在規避辦案風險的考量。在我國,對社會危險性審查是一項“良心工作”,需要檢察官審慎審查,增加了大量的工作量,這有利于維護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但是不會增加檢察官的直接個人利益,而萬一出現偏差,出現辦案人員沒有批準逮捕但被追訴人阻礙訴訟正常進行的情況時,則辦案人員將會承擔很大的壓力,甚至面臨著嚴苛的追責。與此相對應,即便是不太符合社會危險性條件但辦案人員進行了批捕,最嚴重的后果也僅僅是屬于辦案質量有缺陷,按照現有規定不會給予更多的懲罰。兩相比較,從最簡單的利益權衡考慮,檢察機關辦案人員更愿意只要構罪就將犯罪嫌疑人決定逮捕,有意無意地忽視對社會危險性條件認真把關。
(二)警檢合作,但單位分歧仍待彌合
審查批捕工作大多數時候需要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的高度合作,各地在落實社會危險性相關制度的時候,往往也是檢察院和公安局共同商定,共同推行。但由于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兩者負責的具體工作不一致,面臨的壓力也不相同,因此對個案是否需要批捕考量的具體指標可能會有差異。有的時候,公安機關會降低對社會危險性的把握,積極追求批捕。例如,如果某地一個時期對維穩有較高要求,公安機關是地方穩定的第一責任機關,為了實現有效打擊犯罪,很可能會追求高批捕率。在另外一種情況下,檢察機關可能會降低對社會危險性的標準,例如,在一些交通肇事案件、輕傷害案件中,時常會出現犯罪情節較為輕微,犯罪嫌疑人主動悔過態度也很明顯,但是因為經濟條件有限無法履行賠償責任,被害人一方對此意見很大,檢察機關如果不批捕,很容易出現不利的社會輿論,甚至引發被害人方上訪,故而檢察機關可能會積極追求批準逮捕的效果。
(三)規則細化,但條款內涵仍待細化
2012年修法本身就是對社會危險性條件的細化,但是這種細化仍然留給了基層辦案機關過大的自由裁量權,例如,五種條件中多次用到了“可能”、“現實危險”等充滿不確定性的描述,辦案人員很難在審查批捕的短暫時間內準確地把握這些細節。當然,大部分時候,檢察機關工作人員可以很輕易分辨出五種情形的適用,例如,上海市鐵路運輸檢察院解釋為什么該院的不捕率長期只有2%左右時,提出三點原因:鐵路犯罪嫌疑人大多為流竄作案,且有前科;鐵路犯罪嫌疑人多為外省市人員,如果取保候審,手續繁瑣;鐵路犯罪案件種類單一,毒品類犯罪比例高。[4]我們對這些情況下辦案人員采取較為慎重地處理方式表示充分理解。調研還發現,也有一些時候,地方做法雖有不妥但是難以簡單責難,例如不少地區將交通肇事賠償不到位的案件以“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的條件進行批捕,這其實就是對這一條件的誤讀,做法難以讓人信服,但是事出有因,似乎又在裁量范圍之內,不宜一味的否定。
(四)加強溝通,但各方參與力度仍待加強
在當前,批準逮捕在社會公眾心目當中還帶有較為明顯的懲戒性質,有些案件的批捕工作不僅會引起被害人一方的高度關注,有時還會發酵成為公共話題。課題組調研發現,某地對當地所有的交通肇事但沒有賠償到位的案件,均作出批捕決定,其目的就是為了規避上訪風險,從這一角度,做好說理工作,讓公眾了解不批捕的意義尤為重要。2015年震驚全國的南京養母虐童案中,在南京檢察院發布對李征琴不批捕的決定前,浦口區檢察院就是否批捕召開聽證會,出席聽證會的19人中,除7人未作明確表態,其余12人均建議不予批捕。[5]這種溝通機制就達成了較好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但目前還沒有形成制度進行普遍推廣。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研究項目《湖北省審前羈押必要性審查工作實證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4Q 069)
注釋:
①對此筆者有專文論述,參見拙作《我國新刑訴中逮捕必要性立法的局限性》,載自《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五期。
②圖中數據參見2011—2015年各年度《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來源于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其中2013年工作報告為前五年總結,為保持數據來源一致,故空缺2012年數據。
③這一數據來源于敬大力檢察長2014年9月在湖北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上所作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實施情況的報告。
[1]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編.《關于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立法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114.
[2]李娜.監所檢察審查羈押必要性可解“一押到底”[N].法制日報, 2012-07-19,(5).
[3]劉志月,戴小巍.因無社會危險性不捕4952人[N].法制日報,2014-09-26,(3).
[4]周彬,於乾雄,李怡文.有無必要關鍵看“社會危險性”[N].檢察日報,2014-4-13,(3).
[5]劉珍妮.南京檢方:不批捕虐童養母[N].新京報,2015-04-20,(A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