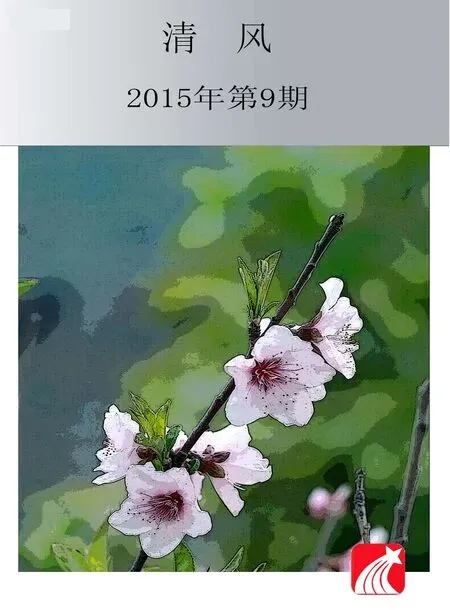說說美國的平等權益爭議
文_闕維杭
說說美國的平等權益爭議
文_闕維杭

關于美國社會爭取和捍衛平等權益的話題實在太多了。2015年6月26日,美國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表決結果裁定同性婚姻合法,這一歷史性的裁決意味著同性婚姻在全美50個州全部合法,對此,奧巴馬總統稱其是“美國的勝利,所有美國人都能從中獲得平等對待,因而我們都將會變得更加自由。”情況真是如此嗎?或許可以毫不掩飾地說,美國最高法院“順從”社會民意變化的裁決,為近年來美國社會準則的驚人改變畫上了一個驚嘆號,然而這卻遠遠不是爭議的終結,而是重大爭議的開始……
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茨(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 十年來首次成了少數派。在他執寫、宣讀的少數派聲明里明確表示,像這樣的決定事宜(涉及平等自由)交給人民投票或是按程序立法就行了,司法系統根本就不應該介入,并表示,參與此次表決的九名大法官從根本上就沒有權利把他們的觀點強加在全美國民眾的頭上。“難道現在就是憑借五個律師‘更好地理解',就到了讓最高法院來決定婚姻的意義的時候了?”
事實上,美國社會涉及平等權益的領域在民生、教育等領域更加突出,有些甚至積重難返危機重重,近日有兩個事件可以說明一些癥結:7月8日,美國聯邦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長卡斯特羅宣布,要努力兌現1968年《公平住房法》的承諾,建設種族相處的社區,遏制因住房等因素所造成的“隔離”。
據卡斯特羅當天在芝加哥南邊新公屋公寓樓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長期以來,聯邦政府在這方面努力不夠。芝加哥市長伊曼紐爾對此表示,聯邦政府選擇在芝加哥宣布新措施并非偶然,因為該市過去具有采用住房政策和地產開發慣例,以及通過這一舉措將非裔限制在貧困社區的歷史。
1968年,美國通過反種族歧視的公平房屋法案(Fair Housing Act),但從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密蘇里州弗格森到馬里蘭州巴爾的摩,不同種族分住不同區域的狀況仍十分明顯。公平房屋法案除了禁止直接歧視之外,還要求接受聯邦住房資金的各個城市公民,不論族裔、祖籍、宗教或者身體殘疾,都應該獲得平等機會和得到住房。但是,如今47年過去了,各方面很少解釋實施該法律“進一步平權”的要求與目標。
如今,我們必須正視的社會現狀是,民權運動高潮過去半個世紀之后,在涉及好社區、好學校、交通方便、就業、食品店和其他機會方面的平價住房領域,美國部分地區仍然以種族畫線,導致不同種族的人相互隔離。換句話說,仍然有相當部分族裔民眾被動地限制于不平等狀態之下。卡斯特羅說,一個孩子長大的地方不應當決定他們的未來歸宿。他引用圣路易斯一社區的數據為例:那個社區的孩子預期壽命要比10英里之外的密蘇里州克雷頓少18歲。
據悉,新規定要求全美各城市檢查自己的住房規劃是否存在按照種族區分的偏見,并且做到每隔三到五年公布結果。新規定還將進一步完善公平房屋法案,搜集并公布各城市的種族分布、貧困率、住房補助、公共房屋、學校品質、公交狀況等信息。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HUD)將據此分配幾十億美元聯邦資金。
而據7月10日另一則來自于《華盛頓郵報》消息披露,美國聯邦教育部長鄧肯(Arne Duncan)的子女要雙雙轉讀私立名校了。在奧巴馬內閣任職教育部長7年的鄧肯,不久前將一對兒女送回家鄉芝加哥,準備讓他們就讀私立名校——芝加哥大學實驗學校。此外,奧巴馬就任總統離開芝加哥前,他的兩個女兒也在這所學校讀書。鄧肯的太太卡倫(Karen)也將回到這所她原來工作的學校繼續全職工作。
在過去六七年中,鄧肯的孩子分別就讀位于阿靈頓的公立學校。2015年4月,鄧肯在接受Fatherly.com采訪時被問到,以一位父親而不是教育部長的身份,其如何看待美國的公立教育系統?鄧肯說:“我非常感激能讓孩子們就讀這么棒的公立學校,這里有優秀的校長和老師,他們都充滿責任心。我和太太都非常感激,在這里孩子們可以得到優質的教育,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成為老師良好的合作伙伴,做稱職的父母。”
然而,在即將來臨的新學年,鄧肯的孩子卻就讀于私立學校,這里不需要遵循由鄧肯部長及教育部為公立學校制定的各種政策,如為學生增加考試、按照教育部制定的“統一核心”(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標準,為學生做測評、以學生成績的好壞來判定老師及學校的教育和管理水平等。私立學校的學生們也不必為接受增加的考試而做長期準備,從而擠占諸如藝術類課程的時間。在私立學校,老師們有自己的工會組織,學校管理者充分重視老師的意見,老師的業績不與學生成績簡單掛鉤,因為他們相信成績不能說明所有的問題,其并不是衡量教學成果的唯一標準。
目前,這些在私立學校通行,在公立學校依然行不通。如今,美國教育立法仍然沿用前總統小布什2002年簽署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其主要特點是增加孩子閱讀和參與數學課程的教學時間,減少藝術類課程的時間;為學生增加統一考試和測評;將學生考試成績與教師業績測評更緊密地聯系起來;增加聯邦政府對地方學校及教師的評估和管理等。
據分析人士認為,將自己的孩子送入私校就讀,只能讓鄧肯更難考慮他和教育部為公立學校制定的政策,更難判斷這些政策對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帶來的影響。報道還披露,在鄧肯和教育部的支持下,美國各地的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s)迅速增加,而附近的許多公校隨之被關閉,使得許多家庭孩子無法就近擇校上學,為家長及孩子們上學帶來許多不便。
當前,聯邦國會就如何改革美國現行教育法繼續展開論辯。國會眾議院7月8日通過了大幅修整“不讓一個孩子掉隊”的現行教育法的新規,將大幅減少聯邦政府對地方教育政策的干預。
愈來愈多的社會各界人士相信,讓學校、老師、學生和家長成為美國教育政策的主要發言人,回歸美國特有的教育傳統——尊重個體差異,發掘和培育孩子的特質和潛能,廣泛涉獵各種學科、保護的創新能力,而避免讓增加的標準化考試限制學生和教師的發展,這才是教育改革的正道,更是實現教育機會平等的有效渠道。
從側面來看,教育部長鄧肯將自己的夫人和子女送回家鄉,不乏需要未雨綢繆,早點葉落歸根的打算,但他刻意將子女送入私立學校,與他這個主管和制定全國公立學校政策、規劃的教育部長,形成了絕妙的諷刺。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凸顯了教育機會平等與否在美國教育界的矛盾。畢竟,大多數美國人沒有足夠的能力和財力讓自己的子女選讀任何私立學校,甚至他們還被剝奪了就近選讀公立學校的機會與權益。
結合聯邦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長卡斯特羅要努力兌現1968年《公平住房法》的承諾,美國人又再一次發現:盡管整體經濟在發展,但是在許多城市的社區,住房隔離狀況改善極少甚至沒有改善。部分城市制定的可負擔住房政策雖然出發點和用意是好的,但卻可能在選址、分配中仍然存在隔離情況。長此以往,貧富不均的鴻溝日益難填,不同種族、階層子弟的人生道路會發生嚴重的差異,而這和美國立國《獨立宣言》倡導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賦人權初衷似乎相去甚遠!
因此,從切實改善住房政策、教育政策、擴大就業等涉及千家萬戶民生大計的領域入手,切實推動相關平權的法規與計劃實施,才是穩妥邁出平等社會的步履。哪怕那是漸進的前行和細微的變化,也將是推動全美國和美國人民受益的福祉。
(作者系美國《僑報》主筆兼美國西北地區主編,應邀為本刊撰寫專欄稿件)

小布什2002年簽署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