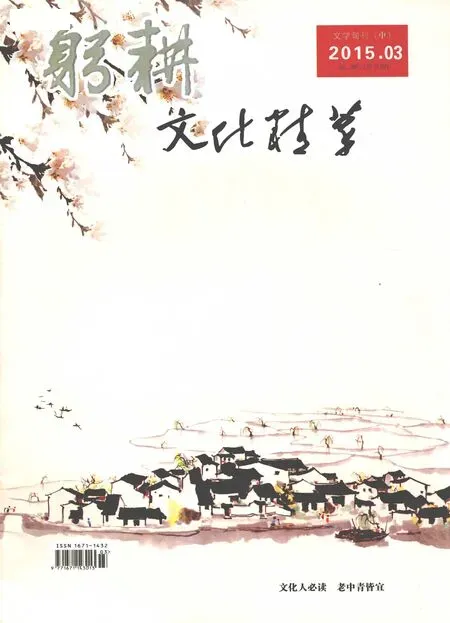憶起當年
◆ 羅秋淵
憶起當年
◆ 羅秋淵
從我記事起就知道奶奶金貴柴火。在那個物質匱乏、經濟拮據的年代,生活在街鎮的我家,父母又都有工作,吃、穿不是太大問題,短缺的是燒火做飯的柴火。因為我家沒有勞動力,是生產隊的最大缺糧戶,每年按工分分的柴火如花柴、苞谷桿、芝麻桿、豆秧等少的可憐。奶奶也只好在平時的生活中一點一滴地節儉、積累。
房屋后面是一大片樹林,最多的是洋槐樹,間或有椿樹、楝樹、桐樹等。每當秋風起,落葉開始飄灑,奶奶就拿個小掃帚把零碎的落葉掃成堆,攬回家里燒鍋。下霜的早晨,奶奶起的更早,看到一地的樹葉、柴梗滿是歡喜。把沾滿白霜、浸著潮濕的樹葉、柴梗掃起,堆在路邊,曬干后拿回家垛在灶房,慢慢受用。
離我家不遠的是中學,校院里有幾排高高的楊樹。我每年最渴望的是黃葉鋪滿校園的季節。姐姐總是挎著籃子,手拿小笤帚,不一會的功夫就是滿滿的一筐。姐姐大我六歲,我那時還小呀,就跟在姐的后面,用繩子串。繩子是奶奶給我制作的簡易工具:用一根鐵絲,一頭磨尖,一頭斡成鉤系上麻繩。我就用尖那頭來扎大的落葉,一片一片,捋在繩子上。很快一繩瓷瓷實實的滿了,我挎在身上與姐姐一起回家,奶奶自是高興,夸獎我背回了一個大錢串。
有趣的事情還有掃麥秸。那時麥收后,就把麥秸垛在生產隊的場里,冬春時節,扒下鍘成細段,拉到牛屋喂牛。我們隊的麥場與牛屋有一里多的距離。放學后我與幾個小伙伴,就在路邊等著牛車經過,搶掃散落在地上的麥秸,拿回家燒鍋。三叔是牛倌兒,那天看到三叔的車過來了,我立馬跑過去,正好在我面前散落了一堆,我趕緊攬在筐里。第二天,三叔又是在我面前散落一堆。我總是盼望三叔的車過來,我也每每滿載而歸。及至長大后我才明白過來,那是三叔故意的關照,而我小時候是多么的懵懂。
后來大一點了,就開始上地拾柴。我也知道,樹葉、麥秸,總是臟鍋灶,煙灰還多,奶奶想望的總是硬朗的柴火。上地拾柴主要是柴根。麥收后、玉米桿砍后,犁地時,柴根總是裸一地,我那個喜歡呀!我動作麻利,手頭也快,邊拾邊打土,很快就滿滿一蘿筐了。那時最苦惱的就是拾滿后我拿不動,父親在南陽工作,奶奶年邁,姐姐也身單力薄。很感謝我的堂兄勇哥總是給我們幫忙。有一次拾麥稈根,筐子快滿時,忽然下起了大雨,我和姐姐都沒拿雨具,又舍不得扔掉筐里的柴根,就擓著蘿筐,從地里往外跑。那個雨大呀,頭發貼在臉上,順著發梢流水,衣服濕透了,最可恨的是腳底下那雙手工縫制的幾近破爛的布鞋沾上了幾層厚的黏泥巴,走不動了,淋成了落湯雞。
到了冬天,晴朗的天里,我們扛著竹耙到河邊田埂上摟干枯的野草桿。疙疤草,夏日葳蕤,冬日枯黃還依偎滿地不肯離去,我用竹耙一摟,就滿滿一耙,很上手。在田埂上還有枯死的樹枝,最是我們的渴望,有刺扎手都不怕,怕的是田埂是生產隊的,樹枝也是公有,偷偷折斷枯枝不讓看林的許四伯看到還行,若看到了要扣工分的。扣工分可不行,我家少有的那點工分是姐姐禮拜天、假期跟著生產隊干活掙的學生分,還有大糞、土糞的積分,就指望這些工分分糧、分菜的,我是懂的。不行就利用鵝毛大雪、天寒地凍的日子去偷偷的干活。那個膽戰心驚、那個寒風刺骨呀,今天想起來還在發顫。有次還真讓許四伯逮個正著,那次是我與勇哥一塊,他有勁,擓著蘿筐就跑,我跑不及了。好的是許四伯是地主分子,我是貧下中農,他沒那么仗勢,另外我媽媽給他女人接生過孩子,他沒有對我多兇,就交待我以后別干了,我就趕快跑掉了!
后來奶奶年事已高,又中風留下后遺癥,半身不遂,就這也沒放下拾柴這檔事。那時為了方便照顧奶奶,我家搬到了媽媽上班的單位附近。在住房前面是柴草交易、集散的街市。每次集罷,奶奶總是拖著不太隨和的右半身,左手拿著笤帚把零散的柴草掃到一塊,等我們姐弟放學后攬回。
奶奶去世將近四十年了,想想小時候困頓的生活,苦中有樂。也多虧了奶奶的勤儉持家,使父母安心工作,我們姐弟四人健康長大。至如今,經濟發展了,老百姓富裕了,農村生活條件也都大大改善,液化氣、沼氣、電磁爐已經普及,煤爐基本淘汰,別再說那些秸稈呀、麥秸呀、樹枝呀、樹葉呀,已經無人問津,在田野里、道路邊廢棄,成了上個世紀的歷史文物了。但每每憶起那些拾柴火燒鍋的林林總總,內心總是彌漫著充實和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