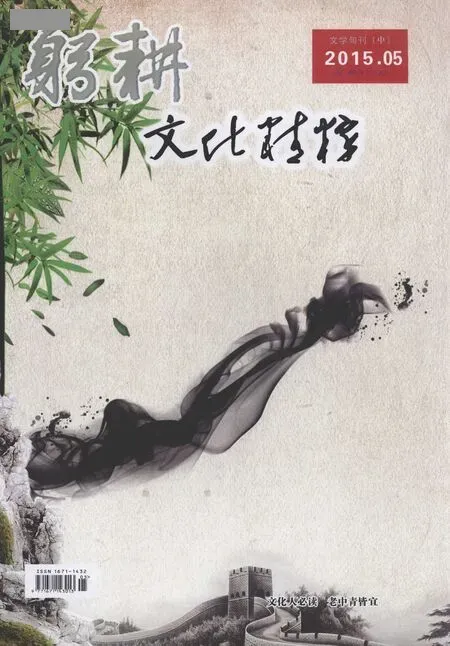穿梭于現實與浪漫之間
——評宋云奇的長篇小說《藍色寓言》
◆ 席 格
穿梭于現實與浪漫之間
——評宋云奇的長篇小說《藍色寓言》
◆ 席 格
地域文化,不僅能為作家的成長提供豐富的文化營養,而且可為其創作提供取之不竭的素材,進而促成作家富有地域特色文化烙印的創作風格。作為當代“中原作家群”核心構成和主要力量的南陽作家群,在南陽文化的滋養下,創作出了一大批富有“南陽文化”特色的優秀作品。宋云奇的長篇小說《藍色寓言》,延續了南陽作家對現實生活的持續關注,通過對掛職干部蕭劍平的官場、情場生活描繪,刻畫出了一批形態各異的中低層官員眾生相,從而以文學的方式,對權力、對情感、對人性進行了深刻的拷問。同時,小說為達到“現實與浪漫”并存的效果,也在敘事中引入了荒誕、象征等超現實主義的手法,并對敘事視角、敘事節奏、敘事內容,進行了巧妙的調整。
地域文化,文化品格,敘事角度。
近年來,文學研究的文化視角日趨強化,這雖與當前地域性作家群的蓬勃發展,地域文化產業開發和區域文化建設等因素的推動有關,但也真實地反映了地域文化對作家和文學創作的深刻影響。透過作家在文學創作中所使用的語言、所描繪的民俗風情、所展示的地域景觀等等,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的創作風格所具有的鮮明的地域文化烙印。作為當代“中原作家群”的核心構成和主要力量的南陽作家群,在南陽文化的滋養下,創作出了一大批富有“南陽文化”特色的優秀作品。這其中,就包括宋云奇的長篇小說《藍色寓言》。
一
現實題材是當代南陽作家群文學創作的重要內容。他們依據各自對人生、對社會、對生活周遭的感受,以獨具個人特征的文學筆觸,去展現人生冷暖,揭示社會美丑,深析人性善惡,同時他們又因受共同的文化滋養,而在整體上呈現出鮮明的南陽作家風格。在現實生活素材的選取中,政治生活領域乃是南陽作家關注的一個重要內容。如老一代的代表作家喬典運,他的《滿票》正是憑借對基層民主選舉深刻而精到的描寫,榮獲了全國1 9 8 5—1986年優秀短篇小說獎。宋云奇在《藍色寓言》中,延續了南陽作家對政治生活的持續關注,成功塑造了一批形態各異的官員眾生相,從而以文學的形式,對權力、對情感、對人性進行了深刻的拷問。
小說中的主人公蕭劍平,原本是市廣電局的“筆桿子”,由于不諳“為領導服務之道”,而失去提拔機會,但突如其來的“掛職鍛煉”,又讓其重燃升職的希望。自此,他從一個相對的“閑差”,而搖身一變為一鎮之長,開始了他的“領導生涯”。然而上任伊始,蕭劍平便領教了因為掛職而妨礙了別人提拔,從而遭到故意設置的“下馬威”——他從“代理鎮長”轉為“鎮長”的提案,在鎮人大例會上不予通過。他開始意識到“官場”規則和權術的重要性,意識到人心的“不可測”。他所任職的鄉鎮為了保住自身利益,在小學入學率檢查中,以各種方式蒙混過關;在計劃生育檢查中,為了能夠通過驗收,先是“威逼利誘”,而后“欲擒故縱”,使逃避計生手術的農民束手就范;在招商引資中,為滿足開發商的要求甚至提供性服務;在旅游開發中,一味迎合領導口味,而置百姓利益于不顧……這些咄咄怪事之所以能夠頻頻而真實地上演,其根本原因是為了撈到“政績”,以博得領導的賞識,獲取提拔的機會。這是中國社會“權力至上”現象的折射。人們對于權力的渴望,讓許多從政者喪失了應有的道德底線,喪失了應有的責任感,喪失了人性中的善良與美好。
官員在權力追逐中的自我迷失,更體現于官場人際關系中暴露出來的爭斗與傾軋,體現于利欲熏心者的陰險與狡詐。他人、朋友、愛人甚至自己的身體,都可以成為撈取權力的砝碼。鎮黨委書記與老縣長的曖昧關系;市廣電局辦公室主任趙逸兵為了提拔成副局長,不惜以卑鄙的手段利用與蕭劍平的朋友關系,甚至故意創造條件,讓自己的老婆與掌握生殺大權的曾局長發生性關系,可謂機關算盡,丑惡之極;市廣電局副科長薛玲玲雖愛慕蕭劍平,甚至甘愿以身相伴,但隨著自己職務的提拔之事,從而變得不可捉摸;侯清元的一意孤行,最終導致“生命谷”突發泥石流,即便如此,在搶救群眾生命的危急關頭,他還想著巴結縣委書記,不惜讓搶險隊伍拖延等候,要為縣委書記創造頭條新聞……可以說,宋云奇通過小說人物對因權力欲的無限膨脹而暴露出的人性惡,對友情、愛情、生命敬畏等基本道德底線的失守,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雖然他在小說中將蕭劍平與柳絮之間描寫為兩情相悅,卻終究無法回避蕭劍平作為公務人員有妻子有孩子的嚴峻現實,蕭劍平對柳絮愛之越深,說明他對妻子蘇亞玲、對婚姻、對家庭的背叛越厲害。這不僅僅有違于應有的法律約束,而且有違于基本的道德準則。但令人欣慰的是,作者通過對在抗洪救災中英勇無畏的關云山、為朋友而鼎力相助的馬仕龍等人物形象的刻畫,讓人重新燃起對人性之善的希望,看到了人間真情的所在。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了官場生態中對于權力的過度追求、對于人倫道德的背叛?是社會的轉型,是經濟利益的誘惑,還是人性的弱點使然?作者在小說的敘事中,并沒有給出一個明晰的線索,但是透過蕭劍平的為人,透過作者自身對南陽人文風情的熟稔,自然而然地為我們提供了解讀的文化視角。
南陽,在行政區劃上位于中原大地的西南部,但就區域文化而言,南陽文化在中原文化系統內卻富于獨特個性。對此,有論者就明確指出:“南陽地處中原文化與荊楚文化的交接帶上,兩種文化的碰撞、交融,鑄就了南陽地域文化的獨特品格:現實與浪漫并存,凝重與飄逸兼容,重質輕文,博大雄渾”。“這樣的文化品格,正是孕育作家的最好營養。當代的南陽作家群無不吮吸著這種文化營養,他們的創作也無不體現著這一文化品格”。宋云奇1955年出生于河南南召,1964年又遷居桐柏,大學畢業之后到南陽市文聯工作。作為生于南陽、長于南陽、工作于南陽的作家,自然而然在潛移默化之中深受南陽文化的影響。
宋云奇在《藍色寓言》的創作中,對南陽前輩作家關注和批判現實的延續,就文化維度來看理應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現實品格之影響。中原文化作為一種農耕文化,有著博大精深的一面,也有一些封建殘留觀念、與現代社會不相吻合的思想等。宋云奇在小說中,主要是針對中原文化中的一些消極觀念、負面觀念進行了批判。簡而言之,主要包括:首先,直指長期以來延續下來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蕭劍平的退讓與怯懦、趙逸兵的卑鄙與狡詐、侯清元的逢迎與陰險等等,都是因為崇尚權力,崇尚“官本位”而最終造成的人性扭曲。其次,通過對柳絮、何玉芳、薛玲玲、蘇亞玲等女性的形象刻畫,對傳統的男權中心、大男子主義觀念進行了批判。再次,通過對底層民眾生活現狀的書寫,揭示出農民性格中的的狡黠、生育觀念的狹隘等。
二
如前文所言,南陽文化作為中原文化與荊楚文化的交融匯合之地,所形成的獨特區域文化品格對南陽作家產生了深遠影響,即便是在講述政治生活、官場斗爭的現實題材小說,依然洋溢出一種獨特的浪漫氣質。而這種浪漫氣質的形成,就創作技巧而言,便是他們在堅持現實主義創作的同時,隨時調整敘事角度,通過虛實的有機結合,融入了荒誕、象征、意象、魔幻等多種藝術手法。如周大新榮獲矛盾文學獎的《湖光山色》,取材于農村生活的當代變革,通過農村變革來展示和反思權力、愛情與人性,但他依然保持了清新唯美的創作品格,究其原因就在于其對象征、意象等寫作手法的靈活運用,對敘事視角、節奏的不斷調整。
《藍色寓言》的浪漫品格,從小說題目的“藍色”便可見端倪。不僅如此,在小說章節標題中也可窺得一斑,如“盤古山讀月”、“天籟二闋驚四座”、“春江花月夜”、“東邊日出西邊雨”、“絕響《廣陵散》”、“漁樵問對”等等。隨著小說敘事的展開,作者通過蕭劍平與柳絮的感情糾葛之詩意、唯美的描述,充分展示了這部現實主義題材小說的浪漫特質。柳絮被作者塑造為一位文化站的工作人員,且音樂素養很高,為他敘事的浪漫性奠定了基調。她與蕭劍平之間的愛情故事,便是在月夜中傾聽她彈奏古典名曲《夕陽簫鼓》的浪漫范圍中拉開帷幕的:“我正在黑暗中望月遐想,半空里悠忽傳來一陣隱隱約約的琵琶之聲。那琵琶的聲音嘈嘈切切,叮叮咚咚,如絲如縷,時隱時現,聲似銀瓶灌水,又如珠落玉盤,音律舒緩自如,意境幽靜高遠……我仔細聽了一會兒,分辨出是中國古代十大名曲之一《夕陽簫鼓》。”隨著故事的展開,作者多次對柳絮的音樂演奏、甚至她與蕭劍平的性愛場景,都被賦予了唯美的浪漫情調。
該書浪漫品格的另一個重要體現,集中在作者對溪口村自然風貌的描寫:“果然看見前方半山腰間,兩座山壁斜峙聳立相倚相交,中間形成一個豎立的橢圓形山口,山口上部垂松倒掛灌木叢生,郁郁蔥蔥異常茂盛。山口的底部,有一道銀河般的飛瀑直瀉而出,飛瀑落天而下,洋洋灑灑出一幅生動無比的圖畫。透過飛瀑形成的水霧,隱約可見一條曲彎的石階小路攀援而上,直通上面的溪口……”正是溪口村的如畫風景,為蕭劍平在招商引資失敗之后,而轉向旅游開發提供了可能;同時也正是旅游開發中埋下的隱患,后來造成了泥石流的沉痛悲劇,進而推動了小說故事情節的持續發展。
在此需要強調的是,《藍色寓言》的浪漫品格,與小說描寫的官場權力爭斗的內容并不沖突,而是有機地穿插于其中,從而有效地調整了整個小說的敘事節奏,也舒緩了讀者因官場權力爭斗敘事而產生的閱讀張力,為整個小說注入了難得的清新之感。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包括宋云奇在內的南陽作家,之所以能在現實題材的創作中,有機地融入浪漫的氣息,就文化地理學的角度來看,顯然是和楚文化的浪漫、飄逸、唯美、富于想象力密切相關的。
三
宋云奇在《藍色寓言》中,為達到“現實與浪漫相結合”,也在敘事中引入了荒誕、象征、意象等超現實主義的藝術手法,并對敘事視角、敘事節奏、敘事內容進行了巧妙的調整。首先,敘事人稱在不斷的變換中融為一體,強化了小說的現實與浪漫并存的整體特色。小說的展開,是由作為作者的“我”的創作開始;待轉入小說正文,則是由第一人稱的“我”與第三人稱的“蕭劍平”之間交替進行;而在小說的結尾處,則又重新復歸于“全知全能”的“我”,讓小說人物與“我”之間,展開一場關于命運的對話。這種敘事視角的自然變換,為小說增添了如夢如幻的荒誕色彩。尤其是結尾處,小說人物因命運的安排與“我”發生的尖銳沖突,儼然在文學真實與現實真實之間形成了一種隱喻,仿佛人世間的一切都是由“上帝”安排的,作品中對官場、情場的所有描述,某種意義上就是對現實所作的一個“寓言”。
其次,運用象征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在為小說增添浪漫特質的同時,調節了敘事的節奏感。小說的女主人公柳絮,雖然有著性格上的弱點,在坎坷的命運安排中不敢抗爭,但卻是以男性的完美而理想的知音形象來塑造的。她清新秀麗,堪稱佳人;多才多藝,琴技頗高;為愛癡情,善解人意。她既沒有因為和蕭劍平的兩情相悅,而強迫蕭劍平為她解決工作調動問題;也沒有因為懷了身孕,而強求蕭劍平與妻子離婚。相反,柳絮事事為蕭劍平著想,非常體諒他的難處,最后選擇獨自離開,孩子出生都沒有告訴他。柳絮的形象,相對于當今官場腐敗,官員包養情婦(當然還有女官員為了進步提拔,甘愿獻身做男上級的情人)的丑聞頻頻見于報端的情景,無疑是一種極具諷刺意味的反諷。柳絮這個人物,可以說是那些缺乏責任感、道德感和道德底線的官場濫情者所夢寐以求的。當然,這僅僅是作者有意創造的一個“寓言”,小說中柳絮為了在泥石流爆發時拯救家人,最終香消玉殞,喪命于洪水之中。而柳絮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出現,就是以其藝術素養,來為在敘事中注入浪漫元素提供基礎的。
再次,運用藝術設置技巧,推動小說情節發展的同時,增加了故事的荒誕性。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作者以荒誕手法所設置的人物“姚書記”。在小說中,蕭劍平的下派掛職、與曾局長的微妙關系、能否順利提拔以及跟縣委書記、組織部長的關系等等情節,都維系于這位始終隱藏在幕后的“姚書記”身上。曾局長、趙逸兵等人都以為蕭劍平與市委姚書記關系密切,而實際上這只是他們的憑空臆斷,蕭劍平根本與姚書記就搭不上話,更不用說是“大樹底下好乘涼”了。所以,假借“姚書記”之名,在曾局長那里順風順水時,就連蕭劍平本人都覺得荒唐和“不好意思”。后來,趙逸兵經過反復追根探底,終于弄清楚蕭劍平跟“姚書記”沒有任何關系時,他也便徹底失去了提拔副局長的一切機會。
宋云奇的《藍色寓言》,以一種看似平淡無奇的市、縣、鄉鎮官場生態題材的生活片段,演繹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富于寓言色彩的離奇故事。無疑,這是一種對于現實社會官場生態的嚴厲批判。然而,這種批判又是巧妙的、智慧的、意味深長的。這種巧妙、智慧的對于社會現實的批判,可能與宋云奇長期從事文學編輯和文學評論工作所養成的理性、睿智有關,也可能與其對社會現實的廣泛持續關注有關。但就文化地理對文學的影響來看,這些都無法抹去特征鮮明的南陽地域文化對其文學創作活動的滋養之功。正是深深扎根于南陽文化,在宋云奇的現實題材創作中,才增加了與雄渾凝重和諧并存的靈動與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