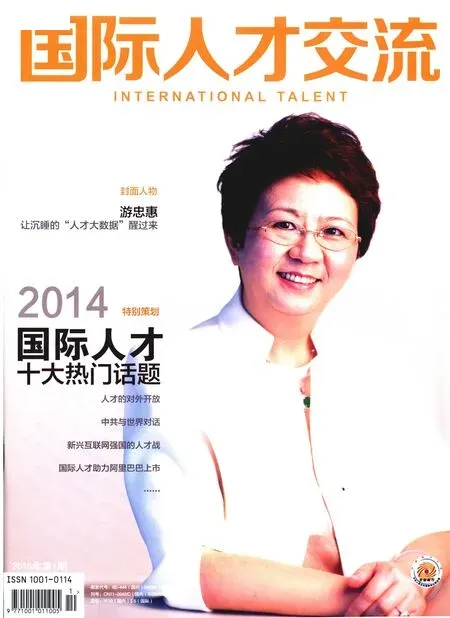海外投資的人才需求
文 / 本刊記者
海外投資的人才需求
文 / 本刊記者

首屆中國企業國際化論壇于2014年11月21日在三亞開幕
2014年11月21日至23日,首屆“中國企業國際化論壇”于海南三亞成功舉行。本次論壇的召開正值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額有望超過外商對華投資額的歷史時刻,吸引了300多位來自海內外的嘉賓,共同見證中國企業國際化轉型的歷史性時刻,共同開啟中國企業國際化元年。
跨國并購就是一個人才大會戰
陶景洲(美國德杰律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
國際兼并收購背后是一個人才的大會戰,需要很多的專業人才。比如說,審計師、會計師背后要做相應的評估,媒體聯絡、游說集團要為項目未來政治上的風險、大眾接受的程度作相應的分析。尤其是因為很多人都對中國投資者抱有懷疑的心理,這些工作就更為重要。
還有技術評估的問題:并購企業的技術在全世界保護的程度如何?這些技術我們是不是能夠消化?這又需要一個技術團隊。還有IPR(專利商標注冊權),有沒有侵權的問題?在哪些國家有侵權的可能性?這不僅需要法律的,也需要技術的人才。到底是直接在中國收購,還是通過在毛里求斯這樣的地方來收購,最大限度減少稅負?怎么把整個團隊有機地整合起來,把它變成一個真正的人才庫,又是一個問題。
國際兼并收購有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都有不同人才需求。第一階段是從計劃收購公司,到簽合同為止的這一段時間。第二階段是買完之后的整合期,包括探索怎么把交易做好,怎么才能夠產生互動,怎么和中國市場結合起來。第三階段是如果發生爭議,必須要退出、賣掉的時期。
收購階段要有這樣一幫有特別強的批評眼光的人才。這個項目我們能不能做,做了以后從長遠來看是不是一個合適的項目?有國際眼光的人才,要有敢于說不的精神。在交易階段,很多人起到了橋梁作用,特別是那些具有兩種或多種文化背景的人。怎么把中國的精神和國外的做法相結合,是這些人急需要完成的任務。
在整合階段,是不是能夠真正達到一個1+1等于2或者等于3的效果?過去中國的企業在國際上的形象總是很一般。很多大公司的高管不太愿意為中國企業服務,比如說,我原來替IBM工作,現在說我要替聯想工作,就會感到有點別扭。怎么能夠改善中國企業的機制,我們也需要做相應的工作。
最后一個是爭議階段。在這個世界上,大概有40%到50%的交易是不成功的。有20%、30%的交易是要進入到訴訟或者仲裁程序的。這不是中國企業做得差,而是交易就是這樣的,世界上文化的融合、在其他國家的投資都要承擔這樣的風險,所以我們要做好未來打架的準備。“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如果你前期沒有做出相應的安排,在合同里面沒有寫清楚,最終就要被所在國法院審,而不是國際仲裁了。
實現外交資源和企業需求的高效對接
吳建民(原中國駐法大使、外交學院前院長):
中國企業走出去,要增加對世界的了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認為發揮外交資源的作用非常重要。
我在美國常駐了10年。基辛格有次請我去參觀他的公司。我發現公司職員都是當年的外交官。我問他公司的業務,他說是做咨詢。“業務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當一家公司計劃‘走出去’的時候,我們來提意見,看它們到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可行不可行。第二,如果可行的話,企業到這個國家去需要找的關鍵人物是誰,也由我們來牽線搭橋。就是做這兩件事情:一個看你的投資能不能做,第二看能不能幫忙找到關鍵人物。”這次參觀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覺得基辛格所說的這兩件事情外交資源是能夠幫上忙的。目前我國出境投資超過入境外資,中國企業需要充分利用外交資源。
參觀基辛格公司之后我就給政府寫了一個報告,建議中國把外交資源用起來,到現在我這個愿望還沒實現。目前,我國的大批外交資源處于失散狀態,這是資源的浪費。
現在中國企業走出去需要的知識和資源外交官恰恰都有。如果有一種機制將上述的人才、資源和需求整合起來,中國的企業走向世界會越走越遠、越走越好。咨詢公司應該是個很好的辦法。
中國企業國際化將人才帶到世界
黃孟復(全國工商聯名譽主席):
中國企業國際化有幾個節點,第一個是2001年加入了WTO,不僅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進入了高速發展的快車道,而且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也非常明顯。第二個節點是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有可能在年底要超過外國對中國的投資。它又是一個新的標志和起點。
中國加入了WTO,使中國的產品走向了全世界,那么現在我們的比較優勢正逐漸淡化,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商品必須轉型升級。但同時,區域貿易發展的勢頭猛進,對我國企業國際化又是很好的機遇。
現在中國企業國際化已經是大勢所趨。根據工商總局的統計,我國民營企業有 1200多萬,一部分企業走出去,數量就會很大。在這種形勢下,中國政府一定會制定一套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形成巨大的支持體系。中國的錢到外邊去,既有利于投資國,也有利于被投資國,這是雙方都獲利的一件事情。以前我國的戰略是防止資金外流,現在中國政府已經明白對外投資是大方向。我國現在正在發起絲綢之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在大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這樣,中國企業走出去就會更加有成效、更加規范化。
將來,我國會有一大批民營企業成為跨國公司,還可能出現比跨國公司更國際化的全球化公司,在世界范圍內發揮非常大的影響力、作用力和帶動力,把中國很多企業、很多技術人才帶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