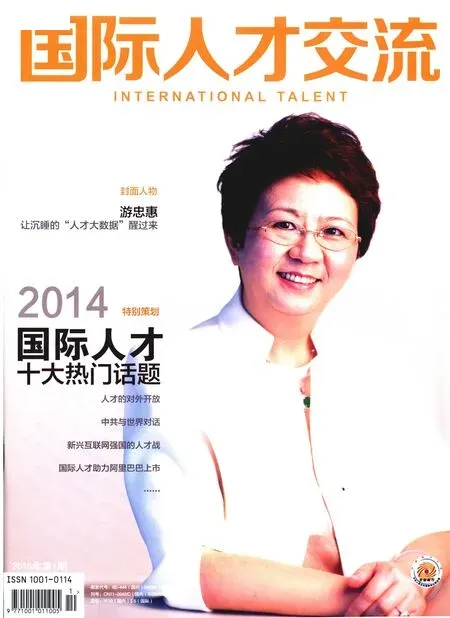世界的中國學——記2014年“漢學與當代中國”座談會
陳曦整理
世界的中國學——記2014年“漢學與當代中國”座談會
陳曦整理
漢學是一門研究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學科。如果從世界史意義上講,漢學又可以說是西方關于中國的一門學問。當16、17世紀的歐洲人越來越多地接觸到中國這種異質性文化時,他們出于或好奇、或崇敬、或陌生的心理以及了解中國的現實需要,開始對中國文化進行較深入的研究。
今天,我們稱之為“漢學”的這門學問已然蔚為大觀,成為一個囊括了中國哲學、歷史、文學藝術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內容的龐大的知識體系。漢學的內涵和外延也越來越豐富,開展漢學研究的國家和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多,漢學正逐漸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的“中國學”,成為促進世界各國與中國開展文化對話的重要知識領域。
漢學研究既有助于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幫助外國人認識中國,同時也有益于中國人深化對自我的認識。
2014年10月28日-30日,中國文化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在京主辦了“漢學與當代中國”座談會。此次活動共邀請到全球18個國家34位知名漢學家及學者參加。
海外漢學關注當代中國發展變化
蔡武(中國文化部部長):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增強,越來越多的漢學家開始關注當代中國的發展變化,將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及其對社會產生的關聯和影響作為漢學研究的新領域。漢學研究已經從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學、歷史、哲學等人文學科擴展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領域。漢學家們在世界范圍內構建了更為豐富的中國圖像,并且對一些國家的政策產生了影響。此外,不少國家和地區紛紛成立漢學研究會等組織。例如歐洲成立的歐洲漢學學會,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并出版自己的刊物,美國、俄羅斯等國都有活躍的漢學家組織,每年舉辦漢學交流活動。
文學交流寄希望于直譯作品
達西安娜(西班牙):
優美雋永的翻譯作品對傳播國家文化非常重要。欠佳的翻譯作品,就像讓讀者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艱難行走。而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西班牙文的最大問題在于,大部分現當代作品都是通過英語、法語轉譯成西班牙文的,譯者們很少懂中文并缺少相關語境的知識。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傳統做法就是邀請精通西班牙文的中國譯者把中國文學翻譯成西班牙文,在這方面中國外文出版社做了很大的貢獻,但在我看來,西班牙讀者閱讀這類譯書時,通常認為中國文化是和自己無關的遙遠異域文化,書中的語言也不是西班牙人理解下的真正有文學性的語言,我們應該走另外一條路。西班牙的大學目前已經有漢學的本科學位,我們寄希望于這些既學習、研究中文,又對中國文學感興趣的西班牙年輕漢學家能夠翻譯出更好的中國文學作品。
視覺文化穿越跨文化交流的壁壘
賈磊磊(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
跨文化交流中最難消除的障礙是人類無法共享一種通用的符號系統。很多學者和學術界的共識是,視覺語言有比其他的通過文字語言表達的文化意義更直接、更真切、更生動、更強烈的特點。在文字語言無法面對的區域實現視覺語言的溝通,不僅能夠克服各種文化壁壘造成的隔閡,還能夠跨越各種文化壁壘。
目前,在跨文化傳播中一般都依賴文字作為相互交流的工具。但除了法律的文本、合同、契約之外,人類基本上所有的交互方式都可以用影像來替代或者展現。一幅意境深遠的繪畫、一首舒緩悠揚的樂曲,對不同國家、不同信仰的人都能夠產生心靈的震撼。視覺文化的表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跨越很多屏蔽。孔子學院所推廣的文字教育雖然成本高、時間長,但效果穩固。在這種文字教育得到鞏固之前,視覺文化可以作為一種補充存在。我們可以采取更多元、多樣的方式來進行文化傳播。

距白宮僅幾個街區的校園內,一棟三層紅色小樓就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孔子學院所在地
學會用西方視角觀察中國
陸建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
我們一定要有一種寬闊的胸懷,多聽人家對我們的文化和文學做出怎樣的評價。這樣才能讓我們對自己更了解。舉個例子,中國人研究《詩經》,認為大部分作品都和宮廷、皇帝有關,有位專門研究中國古代風俗習慣的法國漢學家,卻從中看到中國民間習俗的細節。這種視角是長期浸潤在中國文化的中國人很難想到的,這種良性的溝通和交流,非常有利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研究。如果一個人一生只生活在固定的地方,他對自己的理解很容易受到限制。同理,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也要學會用他者的眼光來反觀自己和自己的文化。
中國當代文學在俄羅斯缺少推廣
羅季奧諾夫(俄羅斯圣彼得堡國立大學東方系常務副主任):
了解一國文化,閱讀該國文學作品是最好的辦法之一。近幾十年中俄兩國的文學交流嚴重失衡,自蘇聯解體后,年輕的俄羅斯讀者都被西方文學占領。1989-2014年在俄出版的中國文學作品只有38本。中國文學在俄羅斯傳播欠佳的原因是讀者對中國文學不了解,文化上存在部分偏見,但最關鍵的問題是缺少推廣。中國有一流的文學大師、一流的文學佳作,中國文學本身不需要改變去適應外國讀者的口味,而推廣的任務通過中國政府或者大出版集團也可以做到。我建議兩國政府簽訂合作協議去支持文學,不僅針對翻譯經費和出版經費進行投入,也要對這些優秀作品的宣傳推廣加大投入。此外,還要注意挑選適合外國讀者的作品,因為文化差異的影響,兩國讀者喜歡的作品未必完全一致。
當然也有幾個因素對中國文學起到了比較積極的推廣作用。第一,俄羅斯的孔子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聯合推廣中國文學。俄羅斯參加孔子學院的人,2013年超過了900萬。孔子學院現在也已經開始進行翻譯項目。第二,2012年莫言先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直接引起了世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矚目,也改變了對中國文學先天的偏見。第三,2013年俄羅斯政府跟中國新聞出版廣播總局簽訂了為期5年的讀一部書的計劃。這樣就有了政府對翻譯事業的支持。第四,2014年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發生對峙后,社會各界的眼光現在轉向中國。現在渴望了解中國的情況越來越多。第五,兩國政府合辦中俄友好交流年的活動,使我們從政治層面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中國學的幾大發展趨勢
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第一,漢學和中國學融合成為大趨勢。一部分研究傳統漢學的學者更加傾向研究當代中國,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又開始追溯歷史。中國學最后被劃分為三部分:傳統漢學、新興漢學和中國問題研究。第二,中國學的深度和廣度越來越大。深度,就是現代的向歷史延伸,歷史的向當代延伸,這二者之間的深度越來越大。廣度,就是空間的廣度,歐美國家的中國學、漢學向發展中國家擴展。還有一個廣度是傳統的人文學科向所有的社會學科擴散。第三,中國學向本土回歸。中國學誕生在西方,它是海外漢學界的研究領域,但現在很多中國學者自己研究自己,并借鑒海外中國學來研究自己,對“中國模式”的研究成為世界的顯學。第四,中國學也在“走出去”。大量中國的研究成果被海外學者引入。在中國學的研究領域內,海內外學者的交流空前頻繁。第五,新一代中國學的學者正在形成。老一代的中國學學者在海外學中文,再來研究中國,新一代的中國學學者在中國讀書、工作和生活,他們比前輩們得到更多資料,也比許多國內學者的研究范圍更廣。第六,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通”越來越多,他們愿意從中國學中吸取經驗,因為他們的祖國正在經歷中國曾有過的發展階段。第七,中國學本身正在轉化為各國對華政策的根據。
開展國際合作客觀研究歷史
葛劍雄(復旦大學教授):
從歷史到今天,中國和外界歷來缺少自覺的交流。自古以來,中國的傳統觀念只有天下觀,沒有世界觀。中國對自己在外界的影響有多大并不重視,就是對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也采取聽其自然的辦法。
近代以來,中外交流在物質上面已經沒有障礙了,但在精神層面,雙方都存在著扭曲。中國還殘留著以前天朝大國“天下之中”的觀念,往往不能接受外界的文化、傳統勝過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外界對中國也存在著諸多的誤解。所以,研究漢學與當代中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要真正地了解歷史,客觀地評價歷史。中國學者和各位國際漢學家,應該排除其他的干擾,開展國際合作,進行雙邊的甚至多邊的深入研究,具體到中國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國不同的文化,他們究竟對外界產生過什么影響。
所以我呼吁我們大家一起來合作,中國學者和國際漢學家一起。至少我們可以對其中一些問題產生一個共識。這樣才能真正使我們今天中國的學者,包括我們中國今天的政治家、國家的領袖能夠正確地把握我們未來文化的走向,能夠明確中國人對人類應該承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