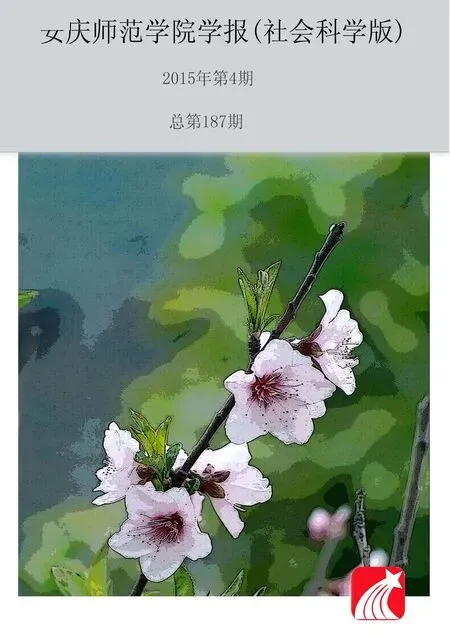勞倫斯短篇小說中的精神生態思想
葉 敬 霞
(安徽大學外語學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
勞倫斯短篇小說中的精神生態思想
葉 敬 霞
(安徽大學外語學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作為一個現代主義作家,勞倫斯十分關注現代文明對人性的異化,在其中短篇小說中生動地再現了人的自然本能與現代機械文明之間的沖突。勞倫斯小說中永恒不變的主題是對扭曲人性的機械文明的鞭撻和對自然人性回歸的呼吁。他認為只有回歸自然,恢復兩性的本來面目,才能使人類擺脫文明的夢魘,遠離機器的摧殘。
關鍵詞:勞倫斯;短篇小說;精神生態;工業文明
大衛·赫伯特·勞倫斯是20世紀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其作品受到國內外批評界廣泛而持久的關注。其短篇小說以主題鮮明、結構緊湊見長,往往被認為是勞倫斯最優秀和最出色的作品。國內關于勞倫斯作品生態解讀的論文雖然比比皆是,但是其中和精神生態分析有關的不到10篇,且多局限在某一部小說的范疇。本文希望通過對勞倫斯短篇小說的精神生態解讀,體現勞倫斯對人類精神生態失衡的關注,呈現他應對這種社會現象所提出的解決方法。
精神生態研究主要是針對人類精神生態領域的研究實踐活動。“現代社會過于注重技術、經濟、物質的發展,忽視了人類精神性的存在,形成社會生產力飛速提高,精神卻并沒有隨之發展的失衡現象,造成了精神生態危機。”[1]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更加關注精神生態,關于精神生態的研究也呈急劇增長的趨勢。精神生態批評由此而生。精神生態批評的使命是“應對現代社會的精神危機,清除精神領域的污染,維護人類精神生態的健康、潔凈”[2]116。在精神生態研究發展的過程當中,不斷地出現各種應對精神生態危機的對策,其中主要一點是回歸自然。“自然是人類身體和精神成長的基礎,它以其博大神秘啟示著人類,賦予人類以靈性。”[1]114勞倫斯在其短篇小說中,深刻地反映了他對人的精神世界的關注,向讀者展示了一幅幅精神生態危機的圖景。
一、 階層對抗與戰爭陰影下的人性淪陷
勞倫斯于1885年出生于英格蘭中部的一個礦工家庭。父親約翰·亞瑟·勞倫斯與母親莉迪婭“是一對不協調的夫妻”[3]3。父親出身卑微,而母親來自上流社會,受到良好的教養。目不識丁的父親無法理解母親,他們無法溝通,有時情緒激化起來還會上演廝打的場景。這一切在勞倫斯心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兩人身份的懸殊對勞倫斯身心的影響都體現在他的小說里。青少年時期勞倫斯還由于自己是礦工的兒子,受到了同學的冷落,他在成長的過程中體會到了令人窒息的階級壓抑。
勞倫斯于1912年4月邂逅了當時著名的威克利教授夫人弗里達,開始了二人的傳奇故事。弗里達的叔叔和父親都是男爵,是西西里島的貴族,地位顯赫,受人尊敬。據弗里達回憶,勞倫斯與她父親的第一次會面是這樣的:“他倆目光犀利地對視著——一邊是我的父親,純粹的貴族,一邊是勞倫斯,礦工的兒子。我父親不無敵意地請勞倫斯抽香煙。”[4]后來弗里達做了一個夢,夢中丈夫和父親打了一架,結果勞倫斯贏了。從這個夢境可以看出勞倫斯蔑視貴族、反抗貴族的階級觀念。現實生活中兩個階級對抗的情景被勞倫斯描繪在自己的小說里。
1913年勞倫斯和妻子弗里達來到德國的巴伐利亞,勞倫斯在這里完成了短篇小說《普魯士軍官》。小說講述的是一個上尉和一個勤務兵之間的故事。兩人的身份等級懸殊分明。上尉是一個普魯士貴族,飛揚跋扈,目空一切。一方面,上尉對勤務兵有著特殊的感情。他嫉妒勤務兵的朝氣蓬勃,“每當勤務兵伺候他的時候,他總不免要感覺到這個血氣方剛的人。那就像一團烈火,燒灼著這個年紀較大的人的緊張、僵硬、死氣沉沉、轉動不靈的身體”[5]3。他對勤務兵的感情像是著了魔一樣,愛戀、嫉妒、憎恨。另一方面,由于飽受壓抑,勤務兵對上尉的感情是恨多于愛。身份的差距使得上尉這種單向的無以宣泄的同性戀欲望受到了極大的挫傷,結果導致了上尉喪失人性而肆意妄為。他病態地發泄自己的欲望,不僅喜怒無常,而且對勤務兵總是吹胡子瞪眼,甚至拿著皮帶頭抽打勤務兵的臉,直到鮮血淋漓。上尉用這種殘忍的行為來獲得內心畸形的快樂。故事的視點聚焦于處于下層勤務兵的內心世界。由于受到長期的奴役和虐待,勤務兵極度痛苦地在自己的生存與世界的對抗中掙扎,最后終于忍無可忍,殺死了上尉。“年輕的臉上一副嚴肅認真的神情,他用一只膝蓋一下子跪到上尉的胸膛上,把他的下巴往樹樁的另一邊按下去。他按著,內心感到一陣松快,緊張的手腕也變得很松快。”[5]20在完成小說之前,勞倫斯就有自己的構思。勞倫斯的好友奧爾丁頓回憶說:“有一天他到沃辛去,見到了一些大兵,他們給他的印象極壞,他斷言他們是一群‘虱子和臭蟲’,他們遲早會殺了他們的長官不可。”[3]162可見,沃辛之行的產物便是《普魯士軍官》。小人物受到階級壓迫的后果被勞倫斯用放大鏡似的呈現在讀者面前。勤務兵的謀殺行為反映了勤務兵精神上的淪陷,他的這種行為已經超越了一般的正義行為,完全越軌了。精神的異化和扭曲是精神生態污染的根本表征。
如果說階級壓抑是人性淪陷的根源,那么萬惡的戰爭則加速了人性淪陷的速度。勞倫斯認為戰爭是一種致命的疾病,能夠導致人類尊嚴的崩潰。《普魯士軍官》雖創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但勞倫斯已看出戰爭對人性的毀滅。小說揭露了德國軍隊中毫無人性的等級觀念。“從默里的筆記來看,到1914年圣誕節前,勞倫斯的情緒開始受到戰爭的壓抑。”[3]156出自對戰爭深深的焦慮,他想逃離到一個叫“拉納尼姆”的“另一個地方”去。那里沒有齷齪的戰爭,沒有金錢。
勞倫斯創作小說《狐》時,已是一戰的尾聲。由于戰爭,男子奔赴戰場,女人則獨守空巢。女人和女人之間靠互助而生存,班福德和瑪奇就是這樣的兩位女性。在班福德父親的資助下,班福德和瑪奇經營一家農場。然而農場的經營非常慘淡,兩人過著艱辛無味的生活。
故事中兩位女主人公的命運自始至終都與戰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小說中雖然沒有硝煙彌漫的戰場,沒有慘無人道的廝殺,但是戰爭對人性摧殘的痕跡卻十分清楚。班福德和瑪奇在一起,是戰爭導致男人的離開造成的。“雖然她們平時十分要好,在長時間的孤獨寂寞中,她們對彼此還是容易變得有點兒煩躁,有點兒厭倦。”[6]45小說另一主人公亨利的出現是由于戰爭結束了,男人得以重返故里。亨利瘋狂地追求瑪奇,他將班福德視為自己的情敵。當他返回軍營,收到瑪奇的拒絕信時,不禁怒火中燒,人性的丑陋一面暴露無遺。“在他的腦子里,在他的心靈上,在他的全身,有一根刺刺痛了他,使他簡直要發瘋了。他非得把這根刺拔出來。”[6]101班福德就是他的肉中刺。誠如勞倫斯暗示的那樣,亨利如狐貍般陰險、狡詐、狠毒,最后不留蛛絲馬跡地干掉了班福德。如此干凈利落、不著痕跡地殺人,如果不是戰爭的歷練,對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恐怕是難以做到的。
二、 西方物質文明背后人類情感的扭曲
19世紀末20世紀初工業文明的興起和急劇發展對西方社會產生了劇烈的沖擊,“傳統遭到扼殺,人性變得扭曲,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變得極不和諧”[7]57。生活在英國工業革命迅猛發展的時期,目睹工業革命的歷史進程帶來的種種殘酷的現實,勞倫斯在小說中辛辣地揭露了英國工業文明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勞動人民生活的艱苦以及生活在重壓下的人性的扭曲。他的許多作品都反映了工業革命時期的社會生活。
勞倫斯敏銳地觀察到了工業文明背后人類精神的異化和自我的人格分裂。不僅人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被打破,人與人之間的紐帶也被活生生地割斷。為了揭露這種丑陋的社會現象,勞倫斯在短篇小說《木馬贏家》中更是不惜顛覆描寫母愛偉大的傳統,一步步描述母子之情如何遭受物質文明的腐蝕而名存實亡。《木馬贏家》創作于1926年,是勞倫斯較為著名的短篇小說。故事探討了勞倫斯所關注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尤其是母親與兒子之間的關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西方工業社會中金錢對健康、和諧的人際關系的扭曲。
母親海斯特表面上無比溫柔,在外人看來非常關心、疼愛自己的孩子,但是只有她自己明白,她是一個無法給予愛的母親。正因為沒有母愛,男孩保羅才渴望母愛。可悲的母親因為對金錢的追求已經窒息了母愛的天性,她喪失了愛的能力。房子里始終縈繞著一句沒有說出去的話:“得有更多的錢。”這句恐怖的話“在故事中反復出現,以其詩化節奏強化了故事的童話風格,也烘托了小說的主題,突出了現代社會金錢對人內心的腐蝕”[8]。一個偶然的機會,保羅發現自己騎木馬時可以預測賽馬的贏家,為了討母親歡心,為了讓那個惱人的聲音停下來,保羅瘋狂地騎木馬,達到了癲狂的狀態。開始時,每一次都能準確地預測結果,保羅贏得了很多錢。勞倫斯并沒有讓結局就這樣完美下去。他知道在物欲的刺激下,人的需求是無止境的。家里的聲音非但沒有消失,反而越來越大。在最后一次預測中,保羅從木馬上摔下來,力竭而死。文章中,除了保羅,母親、叔叔以及其他的人都為了金錢而犧牲了人的價值。
《公主》是勞倫斯住在新墨西哥陶斯農場期間所作。《公主》中有兩個對比鮮明的世界:一個是公主的那個與世隔絕的、脆弱的超現實世界;另一個是以現代工業文明為背景的庸俗的資產階級的現實世界。自稱有蘇格蘭王室血統的科林·厄柯特在混沌的現代工業世界中還保持著一份近乎“荒誕的”的純真。從女兒多莉出生以來,他就全身心地照顧著女兒,向女兒灌輸自己的一套理論。“在他的視野中世界已成了一片荒原,高貴者已所剩無幾,人性已被自私和冷漠的資產階級工業社會壓榨到只剩下綠色的惡魔永駐于靈魂的至深處。”[7]147多莉由于一直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下,以至于到38歲時還不知道怎樣與異性交往,體會不到男女間靈與肉的血性結合。父親的去世使她感到“四周的一切似乎全蒸發掉了。先前,她生活在一種溫室里,在她父親瘋癲的氣氛里。突然,溫室從她四周移去了,她到了陰冷、遼闊、庸俗的室外”[6]196-197。父親去世后,她來到西部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在這里她遇到了墨西哥人羅美羅,被羅美羅的相貌、聲音和氣質所迷倒。與羅美羅在山頂的獨處到最后的悲劇結局,其實是公主本人自導自演的結果:她心里想要得到羅美羅,卻又不敢被世人所知。與其說善良淳樸的墨西哥人羅美羅是死于槍口之下,不如說他是死于公主的愛無能。一直活在父親羽翼之下的公主,并不知道真正的愛情是什么,如何去愛別人。勞倫斯有意讓《公主》周旋于神話與現實之間,揭露了人們情感世界荒漠化的冷酷現實。
三、 回歸自然,尋找靈魂的棲息地
勞倫斯是一位先知的文學評論家。在小說中,他不僅揭露了人類精神生態的失衡現狀,也間接地提出了針對這種現狀的良方——回歸自然。勞倫斯本人親力親為,輾轉于世界各地,尋找理想的棲息地。他與自然親密接觸,一生游走在荒野鄉村,遠離現代文明而廣泛接觸異域文化,如意大利的托斯卡納地區、德國的黑森林、澳大利亞、美國的新墨西哥州、亞洲的錫蘭等等。他能站在其他同時代作家無法企及的精神生態高度去詮釋人類的生存狀態。
在《狐》中,那只充滿象征意味的狐貍讓瑪奇神魂顛倒。“每逢她陷入半沉思的狀態中,當她半入迷、半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眼前發生的一切時,支配著她無意識的思想,占有她沉思的空白的一半的,不知怎么總是這只狐貍。”[5]205小說的象征意義顯而易見,勞倫斯通過瑪奇的眼睛,看到了狐與人和諧地交融在一起。“他在擺脫英國社會世俗人生的羈絆之后,企圖到人類以外的生物界和大自然中去尋找他所向往的純真的力量和生命的魅力。”[9]
1922年,勞倫斯同弗里達來到了新墨西哥的陶斯農場,期間除了幾次短暫的歐洲之旅外,他一直住在墨西哥或新墨西哥。在新墨西哥柔和的高原夜色中,勞倫斯尋找到了創作的靈感。勞倫斯無限同情印第安土著居民的悲慘遭遇,痛斥西方文明。《騎馬出走的女人》便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女主人公生活在死氣沉沉、被人遺忘的西班牙小鎮上。“死氣沉沉”一詞頻繁出現在小說中,體現了當時的社會生存狀態。丈夫滿腔熱愛的只是工作,而女主人公則是丈夫擺布的物件,從來沒有一個人單獨出去過。在巴黎、紐約、倫敦待過的她萌生了要去印第安人住的地方。“她覺得她命中注定了該到山里去,到這些無始無終、神秘莫測的印第安人的隱蔽的居住地點去遨游一番。”[5]129當她獨自一人騎馬來到一個空蕩蕩的山谷時,她感受到的不是孤獨,而是奇妙與歡快。主人公逃離白人社會,來到印第安部落。從與印第安人的文化碰撞、摩擦到最終被接受,一直都在她的預料之中。甚至最終的犧牲,她都坦然面對。精神與肉體都得到了解脫與釋然。
以西西里為故事背景的《陽光》創作于意大利熱那亞附近的海邊別墅。小說女主人公居里葉與丈夫之間存在嚴重的問題,去西西里之前,她心里懷著深深的憤懣和挫敗感,丈夫和孩子攪亂了她內心的平靜。醫生對她的建議是進行陽光的理療。在西西里,經過多次與陽光的親密接觸,她情感中陰郁緊張的成分不見了,思想的枷鎖也解開了,疲憊冷卻的心開始輕松暖和起來。居里葉在與自然、陽光的接觸中,找回肉體與靈魂的平衡。“她勇敢地剝去現代文明的偽裝,置路人不顧而將自己裸露在美麗的陽光下,接受它的洗禮。這也是她掙脫一切桎梏,靈魂內血性意識的復蘇。”[7]28相比之下,現代男人的生存狀態卻岌岌可危。居里葉的丈夫由于長期遠離自然,在工業文明下掙扎。他骨子里蒼白無力,怯懦膽小,已經變成了機器的附庸。勞倫斯欲通過對莫里斯外在形象的貶低和丑化,來反映莫里斯精神層面的畸形,從而鞭撻工業文明對人性的摧殘,提倡與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結語
人與人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環境是一個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和諧發展的系統。生態環境的惡化勢必危及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態的危機已經成為人類不可忽視的問題。作為一個現代主義作家,勞倫斯十分關注現代文明對人性的異化,在其中短篇小說中生動地再現了人的自然本能與現代機械文明之間的沖突。勞倫斯小說中永恒不變的主題是對扭曲人性的機械文明的鞭撻和對自然人性回歸的呼吁。他認為只有回歸自然、恢復兩性的本來面目,才能使人類擺脫工業文明的夢魘,遠離機器的摧殘。
參考文獻:
[1]朱鵬杰. 中國精神生態研究二十年[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5).
[2]朱鵬杰. 范疇與體系:中國語境下的精神生態批評研究[J]. 鄱陽湖學刊, 2010 (4).
[3]理查德·奧爾丁頓.勞倫斯傳[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4]弗里達·勞倫斯. 不是我,是風[M]. 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6:10.
[5]勞倫斯.勞倫斯中短篇小說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2.
[6]D.H. 勞倫斯. 勞倫斯中短篇小說選[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7]汪志勤. 勞倫斯中短篇小說多視角研究[M].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2010.
[8]陳兵.勞倫斯《木馬贏家》中的俄狄甫斯情結問題[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1(3).
[9]毛信德.20世紀文學泰斗勞倫斯[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111.
責任編校:林奕鋒
Eco-spirituality in Short Stories of D. H. Lawrence
YE Jing-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China)
Abstract:As a modernist writer, D. H. Lawrenc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alienation of humanity. In his short stories,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natural instincts of human beings and mechanical civilization in modern times. The unchangeable theme of Lawrence’s short stories is the scourge of mechanical civilization which twists humanity and the appeal to natural humanity. According to Lawrence, only by returning to Nature and the original truth can men get rid of the nightmare of civilization and be away from destruction.
Key words:Lawrence; short stories; eco-spirituality;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中圖分類號:I561.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730(2015)04-0031-04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4.008
作者簡介:葉敬霞,女,安徽懷寧人,安徽大學外語學院碩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3-08-19
網絡出版時間:2015-08-20 12:55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820.1255.0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