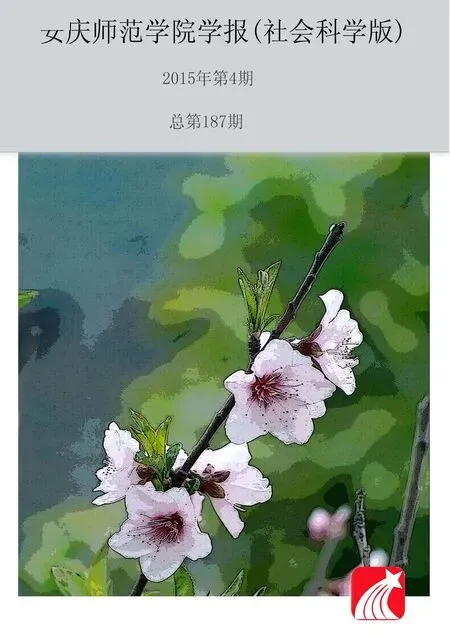明清時期安慶水利建設述論
汪 葛 春
(安徽大學歷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
明清時期安慶水利建設述論
汪 葛 春
(安徽大學歷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明清時期安慶水旱災害頻發,為患甚劇。安慶官民通過整治河湖水道、引水,蓄水灌溉、修筑圩田積極應對水旱為害。但是,水利建設強化了人們對水利的依賴,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程度的危害。
關鍵詞:明清;安慶;水利建設
明清時期,安慶水旱災害頻發,為害甚劇。安慶地區人民就地隨形、因地制宜,興建了一批或防洪或灌溉或者兩者兼備的水利工程。本文以明清安慶府下轄的潛山、懷寧、望江、宿松、太湖、桐城六縣為對象,運用相關地方志及其他文獻,對明清時期安慶水利建設情況做一考察。
一、整治河湖水道
安慶南部沿江一帶多是地勢低洼的平原,河湖縱橫,土質疏松,明清兩代圩田大盛。為防止江河湖水泛濫漫溢成災,明清時期,安慶官府和民間在沿江地帶修建了不少河湖堤防。就數量而言,清中期以前修建的堤防比較少,只有宿松康公堤、黎協堤、楓香堤,太湖翟公堤、萬柳堤,大多數堤防是清中后期修筑的。如宿松“道光后,江潮迭溢,于是外而沿江數百里之長堤先后修筑,內而濱湖各村莊地畝亦均筑圍”[1]408。著名的同馬大堤綿亙數百里,就是從道光到光緒年間逐步修筑成的。同馬大堤乃同仁、馬華二堤合稱,上起鄂皖交界的段窖,下至懷寧官壩頭,聯并同仁堤、丁家口堤、涇江長堤、馬華堤等,長達175公里,保護了宿松、望江、懷寧、太湖四縣141.5萬畝耕地[2]。除沿江大堤外,安慶民眾還修建了眾多擁護江堤的“復堤”和抵御湖水漫溢的“御湖之堤”。如宿松的南堤、御湖堤、綏豐堤、惠民堤、涇小后湖各堤、七段各湖堤等堤。這些堤防規模相對較小,多由官紳倡導,民間集資修筑,如同仁護堤就是“自道光十八年修建同仁官堤后,近堤紳民因湖水內溢,當即集資修建”[1]410的。這些大堤建成后,每遇大水堤決,多請官款補助興修。總之,江湖各堤依為唇齒,共同保護堤內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安慶境內諸河多發源于西北部大別山,明清時期河流上游過度墾殖造成植被稀疏、地表裸露,一旦“霖潦經時,洪流浩淼”,大水“一出平原則沛然莫御,沙隨水走,前者未去,后者復來,遂致河日高而田日低”[3]21。下游河床淤高,通暢水流能力減弱,若驟遇洪流,排泄無力,必然釀成泛濫、潰堤之禍。所以明清時期,安慶官民除筑堤御水外,也重視開挖疏浚河道以減水。如在桐城縣北有河一道,發源于龍眠諸山,由是而東而南,匯太湖、達長江,“其支流所引,為西南疆畝水利”。但每年春夏之際,眾流合聚,“激簡若雷,數年來壞民居而入,直沖郭下。”為治此河,康熙十一年夏,知縣胡必選組織人員對其“深浚,河流故道,束之不得他出”,當年秋年竣工,“計堤長七十有八丈,深一丈有三尺,橫亙稱之”,自此“河流式序”,“南畝資灌溉”[4]。
二、引水、蓄水灌溉
修建河湖堤防、開浚河道是防治水害;引水、蓄水灌溉則側重于減輕旱災造成的損失。安慶地區河流縱橫、湖泊眾多,如何因地制宜地導引如此豐富的水資源灌溉田畝是明清時期安慶人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的引水灌溉形式有引渠灌溉和提水灌溉等。
引渠灌溉就是開挖渠道,就近引溪流、河水、湖水進行農田灌溉。如懷寧縣的田地“近湖河者則各從所近之處引湖河入灌”。以該縣淥水鄉為例,其田畝灌溉用水就是分別從新河、長楓港、張家塞、大泊頭、白草湖、秦塘湖及長江引來的;廣泰圩內邱郎泊、泉潭夾、西夾湖、司公夾、小港、草扛湖、洲浦夾、墩子湖“引江水由鴨兒溝入灌田萬余畝”[5]101。桐城縣北郭外有桐溪,萬歷時縣令胡若思“鑿渠引桐溪水溉西郊民田數十頃,……名為桐渠”[6]。后世多有疏浚,康熙十年“歲旱,獨西南獲水利有秋焉”[7]。清初,宿松二鄧堰及茯苓阪田多塘少,居民董、周各姓倡議跨筑大河開溝,“長約五里有奇,闊八尺以至丈余不等,從大河挽水灌田近二十頃”[1]415。
提水灌溉是利用簡單的機械裝置將低處的水源提到高處灌溉農田的方式。明清安慶人因地制宜,山區農民利用溪流河水落差大的特點,安裝水輪和筒車,借助自然水流動力輸水灌田。如明御使刑址游潛山時,就曾見“溪旁有輪蓄水左右,曰水輪也。山雨溪漲,縛竹為筒,水驅輪轉,筒自挽水以灌田,無庸人力也”[8]。弘治宿松縣令施溥根據民間“筒車舊廢”的實際情況,“遇河流不竭者,令民為筒車五十乘,朝夕自運不停,民力少息”[9]。平原地區的農民則使用水車車水灌溉。如桐城“河田或取給于河水,以水車轉運,隨時蓄泄”[10]。宿松張劉堰久廢,田荒,光緒二十年重新挑筑后,引鏧山南流之水注之,“遇田旱時,張、劉兩屋車水灌田,駕車五乘,以一天為一度,周而復始”[1]414。
安慶地區山地丘陵崗地眾多,地勢陡峻,地表蓄水能力薄弱且流經的山溪、河流多短促,一遇干旱,水量減少甚至有斷流之虞。因此,直接引水灌溉并不理想。為保證山地丘陵崗地的灌溉,就得解決灌溉用水的攔蓄問題。明清安慶人多采用陂、塘、堰等水利型式攔蓄灌溉水源。陂、塘名稱雖相異,實際大抵相同,都是指能潴蓄水潦的池子;堰是指修筑在河流上攔截水流以積蓄水量的水利工程。
明清安慶山區、丘陵地帶各類陂塘堰灌溉工程星羅棋布。如桐城“有山必有塘,塘大小長短淺深不一,山田亦有山塘”[10]。懷寧“懷田山阪錯雜,水多仰給塘陂”[5]101。當然,明清時期,安慶除了新修一批陂塘堰外,也重視對舊有工程的修復和整治,如對著名的吳塘堰的修治。吳塘堰位于潛山境內潛水南岸,為東漢末揚州刺史劉馥創筑,建成后“溉田三千七百余石,約萬有一千余畝”,后世歷代均有修葺,“以故他壤告饑,而堰以下獨無恙”。但及至明中葉,因失修而荒廢。嘉靖元年,安慶知府胡瓚宗重修吳塘堰,“乃筑于上流,鑿山麓之石為渠,凡二百余尺,廣有八尺,深加廣四之一”,結果“水入石渠順其性,安流徐行,以達于土溝,以灌于田,歲乃大熟”[3]22。此后,萬歷時于廷寀,康熙時常大忠、蔡廷等均有所修治,一方百姓也深得吳塘堰灌溉之利。
三、修筑圩田
圩田是在地勢低洼多水的地區,臨水筑堤,將水與農田隔開以抵御洪水內犯,堤內密布管道,堤上建閘,澇時開閘以泄積水,旱時開閘引外水入灌的工程,因其“有堤有閘,故列水利之中”[3]23。圩田把防水防旱的功能集于一身,以期達到旱澇保收。明清時期安慶地區水旱頻發,同時特別是清中期以后生齒日繁,人口增長與耕地不足矛盾日益加深,旱澇保收的圩田開發迅速,長江沿岸、丘陵地區、大別山山前平原的湖泊、河汊、蘆洲、淺沼、草蕩多被開辟為圩田。根據相關地方志記載,安慶地區圩田在道光以后尤盛,圩田分布廣泛,如在桐城,“孔城出街西往縣城西南,往樅陽皆有圩田”,“自下樅陽以東至于陳家洲,東北盡于老洲頭盡皆圩田”[10]。至清末,宿松有圩田60座,潛山11座,懷寧超過37座。
安慶地區最著名的圩田莫過于望江西圩。關于西圩的起源莫衷一是,其面積、范圍,明以前史載不詳,亦不得而知,但自明以后歷朝屢有修治。據記載,其“圩周三十余里,岸長三千九百七十余丈,腳闊十丈,高二丈;內包西湖、小陂、后湖,為田三萬七千余畝”[11],是望江縣的糧食主產區,“居民千有百余家,國賦參邑之半”[12]。又如地跨懷桐兩縣的廣濟圩,舊名廣泰圩,嘉慶八年懷寧淥水鄉人王大本等倡議修筑而成,道光六年、同治九年逐步擴建至桐城境內,圩堤長達百里,分元、亨、利、貞四大號,“凡從前各小圩名目極多已盡包在內”, “由是懷桐兩縣居民共數十萬畝益鮮水災,城垣亦籍資障護”,因所濟者廣,遂改名廣濟圩[5]104。當然,像這樣萬畝以上的圩田比較少見。大體上,安慶東部圩田面積較西部為大,如懷寧圩田很多能達到數千畝,宿松圩田多為數百、幾十畝的規模,甚至有的圩田只有數畝,如宿松的劉家小圍僅6.4畝、羅圍僅2.5畝、羅殿英圍僅1畝等。實際上,大型圩田也多是由眾多小圩聯并在一起而成的。如上述的廣濟圩內部就包括永豐圩、安樂圩、太平前后圩、長生橫圩、張家橋圩、小河埂圩等眾多小圩。眾多小圩聯并在一起,統一規劃布局,加固堤岸,清理溝洫,減少圩堤滲漏,增強排灌能力,可以更積極、有效地防御洪水侵犯。明清安慶地方官民都十分重視對當地圩田的興修與維護,并形成了許多規范化的管理制度,如設立圩長負責領導加固維修圩堤、管理涵閘等,不少圩區如望江西圩,還制訂了圩規圩約防治人為破壞。
四、水利建設治理水旱災害的反思
明清安慶官民的一些水利建設活動,如緣坡開溝、臨水筑堤、開墾易澇地、修筑圩田,使得荒野化為膏腴、城垣房屋免遭漂沒、人口繁衍興盛,但人們享受這些水利建設成果帶來的紅利時,農業生產、生命財產安全更加依賴于水利。水利的興衰制約著人們生產生活的好壞。在水利建設已然大發展的背景下,一旦社會動蕩,水利設施維修不力,不顧公利的水利利用盛行,某些自然條件變化使水利出現衰退時,洪魔旱魃的危害性將成倍增強。如宿松柴家圍、劉紀人圍等39圍,原系濱河泥灘,明時河道寬廣,泥灘多沒于水中。雍乾后,“河漸淤漲,灘壅愈高,附近居民于是傍河筑圍,開墾田畝”,共開得田14頃62畝多,“當各圍初建之時,正值乾嘉間江潮低落,湖水不波,所墾之田豐收有慶;自道光后,連年大水,潰決之患幾于無歲無之。是昔之易荒原為膏腴者,今又變膏腴為荒原。”[1]413懷寧鄭家圩筑于受泉白洋湖口,有田數千畝,白洋湖是該縣獨秀山以西之水匯聚之處,自乾隆年中筑此圩后,“水下流泄常遲滯,湖內田七千余畝,時時被菑”。嘉慶四年,又在湖口建朝天閘,“水益壅不得出,每遇山洪即成積潦,有業者苦之”[5]106。太湖“大河繞縣城北東南三門,舊有民修土堤,成毀不常,歲多河患”[13]。
簡而言之,明清安慶水利建設得到了很大發展,各類水利工程數量多,分布廣泛。然而,明清安慶地區水利災害的頻度、強度及造成的破壞卻沒有相應地消減,甚至于強化了。這似乎是一個悖論,值得我們去反思。
參考文獻:
[1] 張燦奎.(民國)宿松縣志(二)[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408-415.
[2] 杭宏秋.簡論安徽沿江圩垾的歷史演變[J].中國農史,1988(4).
[3] 劉廷鳳.(民國)潛山縣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21-23.
[4] 胡必選. 修河紀事[M]∥胡必選.(康熙)安慶府桐城縣志·卷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239.
[5] 舒景蘅.(民國)懷寧縣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101-106.
[6] 焦竑.玉堂叢語·卷二·政事[M]. 顧思 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35.
[7] 胡必選.(康熙)安慶府桐城縣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23.
[8] 張楷.(康熙)安慶府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772.
[9] 石葆元,汪景祥.(道光)宿松縣志·卷六·水利志[O]. 道光八年刻本.
[10] 金鼎壽,廖大聞.(道光)桐城續修縣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290.
[11] 龍子甲.(萬歷)望江縣志[M]∥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二〇冊).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2:734.
[12] 沈鎬.邑令馬駿修西圩碑記[M]∥曹京,鄭交泰.(乾隆)望江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620.
[13] 李英,高壽恒.(民國)太湖縣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55.
責任編校:徐希軍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730(2015)04-0093-03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4.022
作者簡介:汪葛春,男,安徽潛山人,安徽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明代災荒中的民間應對機制研究”(12BZS064);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明代災荒中的官民互動”(13YJC770014)。
*收稿日期:2015-04-04
網絡出版時間:2015-08-20 12:55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820.1255.0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