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生命的回歸之途—楊櫻與她的藝術
作者_楊小彥
穿透生命的回歸之途—楊櫻與她的藝術
作者_楊小彥

>> 少女的夏天-楊纓(絹本設色) 50cmX100cm.(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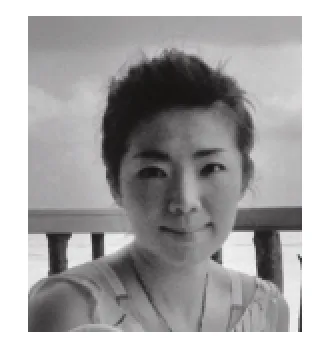
>> 楊纓 (Denise Ying Yang) 又名燈燈,專業畫家,現在廣州美術學院國畫系任教。
好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到了楊櫻的“透明”。當年她還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女孩,初入社會,對什么都充滿了好奇,也充滿了疑惑。那份率真,那份任性,全都表現在她的畫中。所以她的畫既率真,也任性,既好奇,也疑惑,是對未來生命的注視,也是對自我認定的探索。我無以名之,就把她的藝術稱作“透明”。我覺得楊櫻式的透明表達,是女孩的,但不完全是女性的,而是有幾分頑氣,幾分胡為,幾分較真。
“透明”是一種坦然 是自己
當時我就覺得,用中國畫傳統的術語,什么“意境”,什么“筆墨”,什么“取舍”,什么“詩意”,都不能概括她的藝術。她就那樣,把大多數人所認定的各種“水墨傳統”放在一邊,因為她不需要、更不知道如何去運用那些“傳統”。她年輕,對生命有一種朦朧的預感,所以她并不需要借助人們所認定的“傳統”來表達。對于楊櫻來說,她只需要表達,而且表達得順暢自由就可以了,而不管畫種的限制,不管各種關于國畫的定義,更不管什么“傳統”不“傳統”。所以我用了“透明”兩個字來述說她的畫。關鍵是,在我看來,楊櫻式的“透明”并不指稱一種風格,一種可以讓人辨識的水墨符號。“透明”是一種真實的狀態,是一種坦然,是自己。楊櫻把自己擺進藝術中,所以她的畫就具有了個人力量,具有了與人交流的底蘊。我想,沒有什么藝術風格,哪怕已經有了定評的藝術風格,會比這“透明”更讓人感動。
現在想來,我當時一定是被楊櫻的“透明”感動了,我在她的畫中看到了她,一個“透明”的女孩。
幾年過去了,楊櫻在學業上已有了驚人的發展,在藝術上也有了獨到的認識。我相信,在她求學的歲月中,在做老師的教學實踐中,這個昔日“透明”的女孩已經成長起來。藝術之于她,如人生一般,有了更深厚更豐彩的色澤。
然而,在我目睹了她的近作之后,我驚訝地發現,楊櫻依然保留了她那份“透明”,只是,這“透明”多了一層底蘊,多了一層對人生的體悟。
“透明”是一種感性化的表達方式
她感性,但這感性是有歷練在的。楊櫻的題材全是個人幻想,甚至是個人內心的夢境,為現實世界所無,又不比現實世界的存在更簡單。多年來她就是一個感性的人,“透明”恰恰是她的一種感性化的表達方式。如果說,當年的感性更像絮語,今天楊櫻的感性就是低吟了。她在感性當中獲取靈感,在感性當中自滿自足,原因是,這感性成了她的一種標志,一種性格,一種語言。她需要這份感性,然后才能裝點她所渴望的藝術。
她幻想如故。現實的一切不是以寫實的方式進入她的思維的,這和當年一樣。可是,當年的幻想免不了天真,甚至天真成了一種述說。今天,成熟了的楊櫻已然擺正了她和現實世界的關系。她依然拒絕去模仿現實,除了水墨畫本來就沒有西方式的模仿傳統外,在楊櫻看來,模仿就是一種獻媚,表達了對表面世界的屈服。而人的價值正在于不屈服,更不獻媚。看來,幻想有兩種,一種是逃避,一種進取。當楊櫻采取了進取的態度以后,幻想就不再虛無,而是自我情感的有力折射。楊櫻耽于她的幻想,是她相信在如訴的幻想當中,她建立了與現實世界溝通的橋梁。她站在這橋梁上,然后堅定地走向彼岸。
楊櫻的藝術是水性的存在
她“傳統”了,但這只表明她對傳統有了個人體認。當年的楊櫻拒絕傳統,是因為絕大多數的傳統都和她的人生無關。筆墨不關她事,碑帖不關她事,宋山元水不關她事。她的生活是開放的,唯獨沒有“傳統”。但是,楊櫻并沒有刻意去反什么“傳統”,那種方式只是一種姿態,擺的。楊櫻不需要這個姿態。所以,楊櫻不是要反“傳統”。她之所以選擇了“透明”,是因為這“透明”與她的人生有關。我懷疑從童年開始,楊櫻就憧憬著透明的存在。現在,她開始傳統了,是因為她發現了與自己有關的傳統。比如說,她發現了絹這種材料。我可以想象當她發現絹以后,她對紙就產生了一種回避。毫無疑問,絹是傳統的。但我堅定地相信,絹這種材料之所以感動了楊櫻,不是因為中國歷史上早就有了絹畫,而是因為絹的質地整個地就是楊櫻本人的質地。她在絹上發現了一個自己。由此,她開始尋求歷史上的絹畫,在這些歷史塵封的古董當中尋找青春的氣息。
絹和水有關系,也和渲染有關系。在水的作用下,色彩與墨色混為一體,暈染成片,當中的偶然性常常讓人感動。在紙上暈染自有紙上的效果,可一旦把水、墨、色與絹結合起來,那種天然渾成的肌理就成了楊櫻為“透明”尋找落腳處的依托。正是在這依托上,楊櫻把感性、幻想、傳統與青春融為一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楊櫻的藝術不僅是透明的,而且是水性的存在。
(摘選自《穿透生命的回歸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