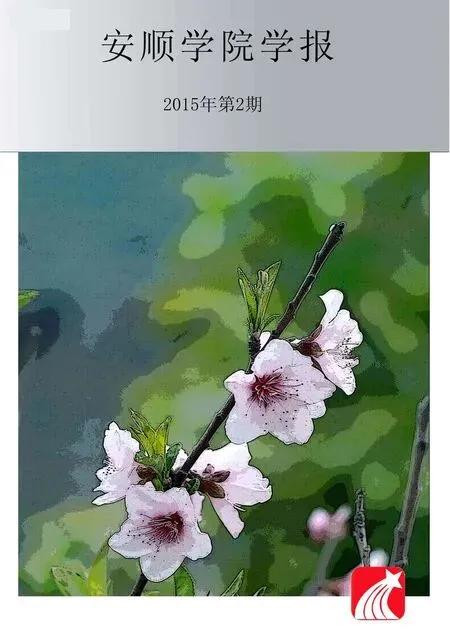唐代佛教雕塑的“繪”與“雕”
王 勛 趙玉芳
(1.合肥師范學院藝術傳媒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安徽文達信息工程學院財經學院,安徽 合肥 231201)
唐代佛教雕塑的“繪”與“雕”
王 勛1趙玉芳2
(1.合肥師范學院藝術傳媒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安徽文達信息工程學院財經學院,安徽 合肥 231201)
文章主要從雕與繪兩個方面分析唐代佛教雕塑的風格與特點。在中國雕塑的歷史中,繪與雕從未分離,“雕”使“繪”的線型表達趨于真實,“繪”使“雕”的立面造型更加流暢。繪、雕結合的特點,經歷彩陶、青銅器、陵墓石刻等雕刻形式,到唐代佛教彩塑達到了歷史的高峰。活潑宛轉的線條、堅實有力的造型、繽紛迷眩的色彩交相輝映,糅合融通,奏出了中國雕塑藝術的最強音。
唐代佛教雕塑;造像;線條;色彩
佛教在唐代達到全盛,建寺造像之風遍及全國。隋末唐初佛教造像樣式日趨統一,逐漸孕育為圓熟洗練、飽滿瑰麗的盛唐風格。唐代佛教雕塑的制作主要采用了雕與繪兩種形式:“雕”指雕刻刀法、塑造能力與造型特點等雕塑自身因素,“繪”則指雕塑對于繪畫元素的借鑒與運用。經過長期的探索與努力,唐代佛教雕塑終將二者熔于一爐,創造出中國雕塑的特有樣式。
一、唐代佛教雕塑的“雕”
1、雕刻刀法精進
唐代佛教造像雕塑刀法的精進,一方面表現為人物衣紋用刀的變化。唐代之前,主要以陰刻的直平刀法表現衣紋,無法體現衣紋的形體結構。唐初發展為向下凹入的新圓刀法來表現衣紋,“衣紋線在保留前朝的‘鐵線描’中趨于圓潤的‘蘭葉描’”[1]。高宗、武后以后,又發展出完全凸起的圓刀技法,表現各種衣紋變化,可是仍未能完全擺脫前代平面化、程式化的衣紋刻法。中唐之后,造像細部衣紋的處理,不再謹守固定樣式,刀法更加運用自如,流暢宛轉。例如,敦煌莫高窟第一百九十四窟菩薩像,衣紋凸凹有致,富有變化;第三百二十八窟阿難像,紋飾蜿蜒起伏,舒卷曲折:既具線的韻律,又有體的厚度。另一方面,不斷探索出塑造肌肉和形體的新刀法。在吸收印度雕刻刀法的基礎上,逐漸開創出能夠塑造真實立體感的各種新刀法。這些刀法善于表現起伏的肌肉和堅實的形體,雕刻出了很多肌肉夸張、雄武赳赳的形象。山西五臺山南禪寺天王像、河南龍門石窟盧舍那龕金剛像皆為其中佳作。
2、寫實能力提高
中國藝術受道家文化的深刻影響,重意輕形,不求寫實。然而,佛教雕塑從一開始就不是供文人雅士品鑒賞玩的藝術品,而是為貧賤百姓焙制的精神鴉片,它的首要義務在于將佛陀、菩薩等無行跡、超自然的上天力量轉化為具體可感的人間形象,使人們更易于接近、理解和領悟。因而,走向寫實是佛教雕塑藝術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佛教造像于北周后期已初顯寫實之端倪。隋代時,雖然有些佛教造型在造型、結構、比例和動態上依然不太準確,所創造的形象不盡完美,卻愈來愈呈現出寫實的傾向。到了唐代,佛教雕塑的真實感與寫實性達到新的高度,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比例適宜。在中國佛教雕塑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對于人物造像比例,始終沒有明確的規定。即使在佛教發源地印度,也直到公元10世紀左右才有了統一佛像標準的《造像量度經》[2]。按照地位尊等不同,佛像、菩薩像、天王像、金剛等各有不同的身形比例,例如,佛像為十拃度像,菩薩像九拃度像(《造像量度經》以手指寬度作為基本測量單位,12指寬等于一拃)。經文中規定:“十拃度像頭部占二拃(肉髻、發際、頸、喉占一拃,面相占一拃),上身三拃,下身五拃。九拃度像頭部占一拃半(發際、頸喉占六指),上身三拃,下身四拃半。”[3]如此,佛像頭部與身體的比例應為1∶5,菩薩像約為1∶6。根據實際勘察測量,魏晉南北朝、隋代佛像與菩薩像的頭部與身體的比例多在1∶3至1∶4之間,因而顯得頭大身小,不合比例。唐代佛像與菩薩像頭部與身體的比例則在1∶4至1∶6之間,與《造像量度經》相差不大,也基本符合人的身形比例。
其二,圓雕塑造。中國早期的佛教雕塑,小到洞窟石壁雕刻,大到摩崖石刻,多采用浮雕形式。有些佛像“雖然以圓雕表現,但其背部緊貼壁面,觀者無法從四周進行觀賞”[4]。而唐代的匠師們卻可以雕刻出供人們四面圍看的圓雕,尤其在造像的側面和背面處理上,不再顯得簡略、粗糙。
其三,形象豐富。唐代佛教雕塑的題材較前代更為多樣。除了佛、菩薩兩個基本內容以外,高僧、羅漢、天王、金剛、力士、弟子、僧尼、飛天等都成為了雕刻對象。龍門第322窟那身形健碩、怒目圓睜的天王像,西川巴中南龕第68窟那飄然若飛、漫游自如的飛天像,莫高窟第45窟那豐頰方頤、神情怡然的阿難像……這些塑像被雕鑿得窮形盡相,無不契合各自的形象特點與精神氣質。
3、世俗形像刻畫
在形象刻畫上,唐代佛教雕塑沿著世俗化、現實性的方向繼續前行。其中的原因是多個方面的:從藝術創作主體的層面看,印度佛教造像儀軌傳入國內后,中國匠師通過數百年的借鑒、學習,不斷總結、積淀,無論在技法上還是認識上都形成了豐厚的積淀,具備了開創自主風格樣式的基礎;從藝術接受客體的角度看,虔誠禮佛的蕓蕓眾生需要具有本民族容貌特征的佛像,以更好地獲取視覺與心理上的認同感;從藝術創作的來源看,許多佛教雕像取材于佛經故事,而這些佛經故事又深刻、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與世俗民情密切相連;從藝術創作的環境看,唐代社會風氣開明,對于文化藝術創作的限制較小,有助于新風格樣式的孕育。最終,在各種因素的促導下,魏晉佛教造像威嚴、玄秘的神性氣質逐漸轉為唐代溫馨、慈悲的人性精神。
唐代雕塑這種對人的關注體現于各大石窟造像之中。龍門奉先寺廬舍那佛像沒有受限于印度理想化造像原則,完全依照武則天本人的相貌刻成,面容豐潤、微露笑容、神情微妙,既不失帝王的威嚴氣勢,又體現佛陀之雍容大度,堪稱這一時期造像樣式的典范。莫高窟彩塑造像面相圓潤,體態豐腴,軀體比例協調,民俗化、世俗化氣息非常濃郁,例如第150窟的供養菩薩像細眉修目,面容清麗,宛如豆蔻少女。太原天龍山和甘肅炳靈寺雕刻的那些飽滿豐壯的人物形象,更是突破了佛教禁欲、出世的思想限制,表現出對愛欲、現實的關照。
如上所述,唐代佛教雕塑不但在雕刻技巧與塑造能力上趨于成熟,而且擺脫了印度理想美造像樣式的約制,實現了朝向世俗、關注人生的風格轉向。
二、唐代雕塑的“繪”
1、流暢的線
宗白華先生認為:“希臘的繪畫和雕塑是統一于雕塑,而中國則統一于繪畫。”[5]的確,中國雕塑蘊含著許多繪畫因素,尤其對線條、色彩的運用堪稱絕妙。以線條來傳萬物之神是中國美術的顯要特征。線條既游走于畫筆之中,又舞動于刻刀之下。唐代佛教雕刻非常注重線條的運用,首先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審美意趣相關。誠如李澤厚所言:“線的藝術(畫),正如抒情文學(詩)一樣,是中國文藝最為發達和最富民族特征的,它們同是中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的表現。”[6]其次,匠師們在雕像之前大都先勾勒線描稿,或者參照經典造像粉本。這樣,線稿與粉本中線的因素也就自然地融入雕塑之中。再次,中國人物畫對佛教雕塑影響重大。魏晉南北朝佛教雕塑繁榮興盛時期,正是中國人物畫蓬勃發展之日。南朝張僧繇“面短而艷”和北齊曹仲達“曹衣出水”的繪畫風格,引得當時的雕工塑匠競相模仿。到了唐代,曹仲達的曹家樣、張僧繇的張家樣、吳道子的吳家樣和周昉的周家樣,更是被奉為佛教造像的經典樣式。這些人物繪畫名家的線條或緊勁綿密、或鏗鏘頓挫、或輕盈飄逸、或輕淡簡逸,都被匠師們巧妙地運用于雕塑之中。此外,唐代有一批杰出畫家皆兼善雕作,如韓伯通、宋法智、吳智敏、安生、孫仁貴、趙云質、薛懷義、吳道子、王溫、程進、張宏度等等[7]。當這樣一個善于駕馭線條的繪畫群體集體參與到佛教雕塑創作中去,不難想見線的因素會得到怎樣的彰顯。
唐代佛教雕塑對于線條的運用主要體現在衣紋的處理上。有時變化多端,如大明宮菩薩石雕,雕刻者以工巧細致的手法,“從輕軟的帔巾、腰彩到精麗的胸飾和貼體的薄裙都顯示出優美和諧的線條的交織,從而把一個少婦菩薩的豐腴軀體和婀娜的風采襯托得更加富有魅力”[8]。有時簡潔洗練,如龍門石窟奉先寺龕,幾根疏密有致的衣紋線,既具有裝飾美感,又不至破壞佛像端莊肅穆的整體效果。
線條的韻律還蘊含于雕像身姿、體態的變化之中。有的姿態優雅,右臂自然下垂,左臂微微彎曲,雙腿交錯而立,如莫高窟第194窟菩薩像;有的體態婀娜,頭、肩、臀、腿極力扭動,形成優美的曲線,如四川邛崍石荀山第5窟樂伎;有的嬌媚多情態,胸廓與胯部左右錯動,呈S型轉動,如天龍山唐窟菩薩像。
2、華麗的色
中國雕塑具有上彩的傳統。從新石器時期彩陶、兩漢畫像石(磚)、戰國漆盒彩繪、唐三彩、清掐絲琺瑯器,直到現今的泥人張,色彩一直是雕塑藝術的主旋律。唐代彩塑常用顏色主要有石青、石綠、朱砂、土紅、金、黑、白等。由于顏料多是從礦物中提出而出,因而顏色鮮麗、經久不變。雕工們會根據不同的人物形象,施以不同顏色。菩薩像多涂白色“相粉”,以示肌膚瑩潔,素面如玉;天王、弟子則涂成紅色或赭紅色,唇涂朱紅,衣飾青綠。從著色風格上看,唐代佛教造像較前代更加明亮、華麗,描金畫彩,富麗堂皇,充分體現出盛世大唐的繁榮景象。在裝鑾技巧上,彩塑佛像由初步的能描繪出現實人物衣服質料的各色紋樣,進而能充分地描繪出各色各樣的衣服質料,不僅描繪出最現實的衣服質料的紋樣,而且又能以瀝粉堆金來妝飾雕像細部。極富代表性的是敦煌莫高窟第45窟,其中的菩薩像玉面紅唇,肌膚白皙,肩披土紅色帔巾,腰纏石綠色紗裙,石青色點紋滿綴其間,再飾以重彩描金的峨冠和瓔珞,使得整具塑像絢麗斑斕,光彩照人。
古代西方也有很多彩繪雕塑。古埃及的雕刻工匠要為法老像刷上膚色和服飾的色彩。古希臘的一些雕塑家從模仿自然的角度出發,也時常為雕塑作品畫上顏色。不過,古羅馬以后,西方雕塑逐漸淡化了色彩因素。德國藝術史家邁約在《希臘造型藝術史》中認為,上色的古代雕塑只是雕塑的準備階段,應該把它排除到真正的雕塑以外。然而,唐代佛教彩塑雕像絕不是雕塑的準備階段,而是以錯彩鏤金、線色交織的手法鑄就了中國雕塑的成熟樣式。
結語
唐代佛教雕塑不像西方雕塑那樣地拒斥繪畫元素,而是應塑則塑,當線則線,需彩則彩,充分體現出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的美學精神。事實上,在中國雕塑的歷史中,繪與雕從未分離,“雕”使“繪”的線型表達趨于真實,“繪”使“雕”的立面造型更加流暢。繪、雕結合的特點,經歷彩陶、青銅器、陵墓石刻等雕刻形式,到唐代佛教彩塑達到了歷史的高峰。活潑宛轉的線條、堅實有力的造型、繽紛迷眩的色彩交相輝映、糅合融通,奏出了中國雕塑藝術的最強音。
[1]尹遠洋·從臨摹到創作——以唐代佛教造像為例談衣紋研究[J].藝術科技,2014(10):107.
[2](比利時)魏查理·造像量度經研究綜述[J].羅文華譯,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2):63.
[3]閻文儒·中國雕塑藝術綱要[M].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83.
[4]伍小珊·敦煌彩塑的繪畫性[J].雕塑,2012,(6):69.
[5]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8.
[6]李澤厚·美的歷程[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168.
[7]王子云·中國雕塑藝術史[M].長沙:岳麓書社,2005:372.
[8]易存國·圖說中國雕塑藝術[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74.
(責任編輯:顏建華)
“Painting” and “Carving” of the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ang Dynasty
Wang Xun1Zhao Yufang2
(1.The School of Arts and Media,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China)
(2.The School of Finance & Economics, Anhui Wonder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Hefei 231201, Anhui, Chin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tyle and character of the Buddhist sculpture in Tang dynasty from these two aspects.“Painting” and “carving” have never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ulpture. With carving, the expression of line styles made by painting tends to be more real world. With painting, the elevation modeling presents by carving becomes even more fluent. This character of sculpture, which a mixture of painting and carving, reached the summit in the Buddhist sculpture of Tang dynasty, after experiencing painted pottery, bronze ware, engraving in tombs——successive sculptural forms. The indirect lively lines, solid and strong sculpt, dazzling and diverse colors combined and mixed, played the strongest tone in Chinese statuary art.
Buddhist sculpture in Tang dynasty, statue, line, color
2014-12-08
1.王勛(1980~),男,安徽合肥人,合肥師范學院藝術傳媒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藝術理論與美術教育。 2.趙玉芳(1981~),女,江蘇淮安人,安徽文達信息工程學院財經學院教師,碩士。研究方向:古文獻與文藝理論。
J305
A
1673-9507(2015)02-002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