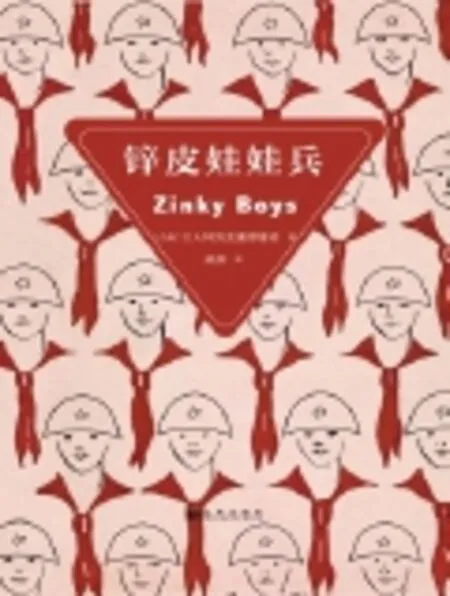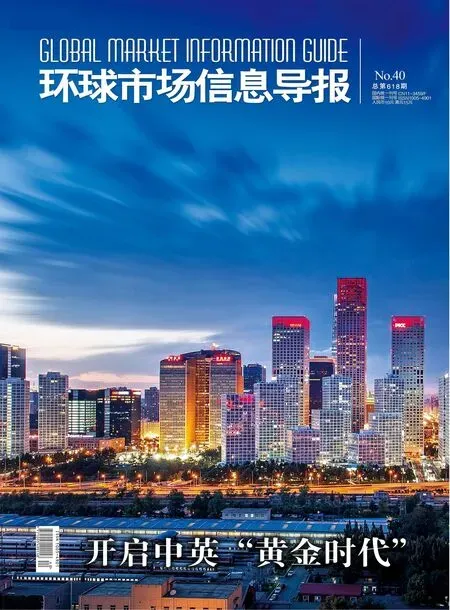回到中國:從鮑明鈐到許章潤
回到中國:從鮑明鈐到許章潤
Point
中國傳統(tǒng)的法律智慧真的能給現(xiàn)代中國的法治帶來什么嗎?這似乎是一個不言自明,而又亟需聲明的問題。從某種狹隘的,線性的歷史決定論來看,落后的過去只是美好的未來的墊腳石,在傳統(tǒng)里面沒有什么好留戀的東西。傳統(tǒng)的信仰即是迷信,傳統(tǒng)的揚棄即是進步。這樣的一種看法,對于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和今天這個處在發(fā)展初期的中國而言,具有特別的吸引力。
一
三年前在北京,我赴約前往中國政法大學,拜訪一位我敬慕的教授,那是我在美國修習法律的第一年暑假,在那里,我背負沉重的學業(yè)、未知的前途,還有迅速消退的信心。北京同時也是某種巨大的失望,我覺得過去一年我在美國努力學習的東西離這里的生活是如此之遠,這里沒什么人能和你討論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或者美國媒體上熱炒的同性戀婚姻訴訟,大家關心的是VIE,避稅和移民。在和那位教授吃了一頓糊里糊涂的飯后,我接到一件意外的禮物,一本厚厚的、有暗紅色封皮的《鮑明鈐文集》。
我從未聽說過他,但是書的開頭對他經(jīng)歷的簡單介紹卻讓我拿起了這本書。他是獲庚款去美國留學的民國學人之一,在美國學習政治學和神學,回國后在多所大學任教,教授政治學和法學。1932年,他因為自己的政治活動被迫短暫逃往菲律賓,他的書遭到查禁,而且他本人也被禁止在任何國內大學擔任教職。后來他去了已經(jīng)淪陷的東北,卻一直拒絕與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戰(zhàn)勝利。內戰(zhàn)期間,他同情共產(chǎn)黨,反感腐敗的國民政府,但解放之后,因為院系調整卻沒有事情做,而且一直拒絕思想改造。1956年他莫名其妙地被捕入獄,5年之后他病死在獄中,時年67歲。
那本文集中絕大多數(shù)的文章,都是在他1922年從美國回國到1932年他流亡菲律賓之間的十年間寫成的。那是時局動蕩,但也是思想激蕩的民國時代。鮑明鈐的所有思考與寫作,都和那個時代中國的歷史走向息息相關。他反思臨時約法的缺點,談論民主政體在中國的興起和帝制的復辟,他談論廢除督軍制的必要和憲制國家的建設,他比較當時世界上所有的先進國家間政體的優(yōu)劣:內閣制和總統(tǒng)制,聯(lián)邦制和單一制,他探討立法機關的構造、組織、職務及權力,行政機關的選舉和權力,司法機關的獨立,解釋中國的省為什么要有一個高度自治的政府,還有政黨政治的條件以及對于國民私權的保障。
從今天的目光看來,這簡直是一本實現(xiàn)共和憲政的指導教材;更讓我意想不到的是,這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用英文寫成,后來再被翻譯成中文出版的。他用英文著述的原因,是想讓國際社會相信,中國已不復是那個腐朽的、落后的、不文明的國度,而是完全可以通過改革,吸納西方文明的成果,加之自身的本位文化,最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民族。他讓自己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是想引導當時國內少數(shù)的精英,為民國政治的困局打開新的出路。他以政治學的基本原理為基礎,結合自身對于清政府立憲到民國中期這二十余年間中國政治史的觀察和反思,也以中華文化本位的精神,總結出所謂“中國民治主義”的學說。
在美國繼續(xù)學習的第二年,在埋頭于企業(yè)并購、公司上市、跨國糾紛的眾多資料案例之余,我也在斯坦福浩瀚的東亞圖書收藏中,發(fā)現(xiàn)了一大批讓我振奮的作品。吳經(jīng)熊、張佛泉、錢端升、王寵惠,他們都和鮑氏相似,是早年留學歐美的學習政治、法律的留學生,都試圖以現(xiàn)代的法治精神改造中國,都希望改革后的中國,不為世界諸強所輕視,在內繁榮富強,在外平等獨立。他們的理念不完全相同,但是都對自身的學說和理念持有相當?shù)淖孕藕陀職狻_@樣的自信和勇氣,不僅僅是在面對外在的政治壓力和迫害的,而且是在各種思想大潮下,做到獨立的思考和陳說。他們都認為東西方之法理智慧不可偏廢,在實現(xiàn)“正義”和“良善”這些終極目的上,學習西方和因襲中國傳統(tǒng)并不互相抵觸。可悲的是,他們在當時都或多或少為現(xiàn)實政治所拋棄。因為他們都不是某一個政黨,某一種單一價值理念的良好代言人,而我們在建立歷史博物館時,卻無意把他們收納其中。他們屬于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里的那些人。

二
中國傳統(tǒng)的法律智慧真的能給現(xiàn)代中國的法治帶來什么嗎?這似乎是一個不言自明,而又亟需聲明的問題。從某種狹隘的,線性的歷史決定論來看,落后的過去只是美好的未來的墊腳石,在傳統(tǒng)里面沒有什么好留戀的東西。傳統(tǒng)的信仰即是迷信,傳統(tǒng)的揚棄即是進步。這樣的一種看法,對于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和今天這個處在發(fā)展初期的中國而言,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圣人的訓諭是要不得的,因為圣人從未見過洋槍;傳統(tǒng)的文學是要不得的,因為文學付不了賠款;傳統(tǒng)中國的整個制度都是應當廢棄的,因為廢棄了這制度的日本不僅打贏了中國,還打贏了西洋的俄國。這是清末民初的普遍情緒。
到了今天,這一情緒的表象變化了,可是內核并沒有什么改變:中國富裕、強大了,是因為我們向西方要來了先進的技術,是因為我們終于不管他是白貓和黑貓,不管是中國外國,只要是能捉到老鼠賺到錢,那就是上帝,那就是真理。按照這樣一種樸素到近乎愚蠢的邏輯,向后看是沒有什么意義的,我們終于擺脫了歷史的枷鎖和束縛,可以大步向錢。因此,還有什么必要談論中國的傳統(tǒng)呢?
這種荒謬的,根本上是反歷史的看法,今天成為大多數(shù)人所謂的“歷史觀”。在此一片荒蕪之上是復興不出什么東西的,甚至連做夢也都是空洞的。文化本來就是一個變動的連續(xù)體,中國文化不是例外,雖然經(jīng)歷了二十世紀人為的撕裂,但是再沖擊、再斷裂,中華文明整體巨大的體量,和其長期的歷史延續(xù)性和豐富性,也能充分吸納這些沖擊。那些積累已久的地層,雖然不曾言說,但是總會在默默中塑造今日的風景。
從法學本身的角度,這里可以稍舉一個小例子,來說明認識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化道路上的重要性。中華帝國在漫長的時間中形成了獨特而復雜的土地制度。在這一點上,中國和西方的產(chǎn)權制度的歷史演變是非常不同的。對于佃農的權利保障,還有農業(yè)生產(chǎn)資料(如土地、水源、道路)相關的爭議解決方案,中國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中,形成了獨特的,和西方基于土地財產(chǎn)權的成文法完全不同的一套法理和習慣法體系。20世紀中國盡管經(jīng)歷了多次大規(guī)模、極端的土地改革,執(zhí)政者一次又一次,出于意識形態(tài)和自身利益的原因改革土地制度,但是在廣大的中國農村,古代中國形成的一種基本習慣:土地及其相關的生產(chǎn)資料的使用權和在地社會成員的地位緊密相關這一原則,仍然普遍適用。在農村中,當?shù)厣鐓^(qū)的核心人物(不管是具體何種職務的人),在解決土地糾紛問題上仍然擔任了法官和行政主管的職位,對本地人利益的保護,對外地人的普遍懷疑,還有對土地使用權的干涉,這些都和傳統(tǒng)中國的習俗是相連的。
拋開傳統(tǒng)中國的這些習俗不論,僅僅以所謂的“市場經(jīng)濟”的名義征用土地,無論其代價是公平還是腐敗的,其過程是“合法”還是“違法”的,都一定會遭到反抗、抵制甚至激起社會運動。縱觀近代中國一百多年的土地改革歷程,所有價值判斷先行的改革,都失敗了,而結合中國傳統(tǒng)和本地實際的改革都成功了。在土地這一基本問題上,你不需要馬克思、亞當·斯密和諾斯,也許你只需要稍微向前看一些,看看民國時的梁漱溟、費孝通。不過你要真的會看他們,而不是僅僅會在講話稿上念出他們的名字。這只是一個小例子,看到許章潤教授的新書《漢語法學論綱》,我覺得一個一個的小例子找到了可以棲身的光明大殿。清華大學法學院的許章潤教授是“文革”后第一批法學的本科生和碩士生,年屆三十又遠赴澳大利亞攻讀博士學位,學成后歸國任教,自身著述和編撰叢書成績斐然。這本新出版的小書實際上是由他之前在法學專業(yè)期刊上的論文和《南風窗》上發(fā)表過的一篇采訪結集而成,主旨在于倡導中華的、漢語的法學體系和法學研究。雖然他上溯戰(zhàn)國春秋,下至當代,但是看得出來,他最關心的還是如何接續(xù)民國以來,他所謂的“新學時代”的中華法學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是由接受了西方近代法律文明,卻又設身處地地為當時中國思慮的那批法學家和法律人所開創(chuàng)的。按照許章潤自己的話說,他談論的“漢語法學”,可以說是“清末以還五代以上中國法學家群體的百年奮斗,所要集成者”,其主要思路,是“自由民族主義的共和法理”;最終的追求,是建立一種“以法權相籠統(tǒng),賴法權以措置,借法權來伸張”的法律文明秩序。全書即圍繞以上幾點展開,分別申說了他所謂“漢語法學”的綱領,“法學歷史主義”的綱領,最后以德國為比較個案,說明了當代中國在轉型時期,為何歷史法學登場既有學理依據(jù),亦有現(xiàn)實必然。這是一本小書,卻包含了許章潤全面重思當下中國法律體系的雄心,和他對中國下幾代法律人的寄托。這是本名副其實的“論綱”(Discourse), 有處理重大問題的視野,宏大的論調和斬截的判斷。但是這本書并不好讀,在仔細看了全書的2/3時,我甚至告訴自己,在中國,學習法律的人也沒幾個人能耐下性子仔細讀完這本書。和鮑明鈐簡單、清新的語言不同,許章潤用詞華麗、古雅,但是在許多說理的段落時卻帶有強烈的口語化風格。他的書是需要用他自己著名的、抑揚頓挫的語調讀出來的,那有一種法官宣讀判詞的氣勢,可是從閱讀本身來看,他字里留給讀者的空間太少了。如果說中國古代法律的傳統(tǒng)智慧他有一點錯過了的話,那就是沉默的智慧。傳統(tǒng)中國經(jīng)典的惜字如金,和對于某些話題的刻意回避,反而給讀者更大的啟發(fā)。排山倒海、飽含情感的申說,完全可以由更為節(jié)制的語言闡發(f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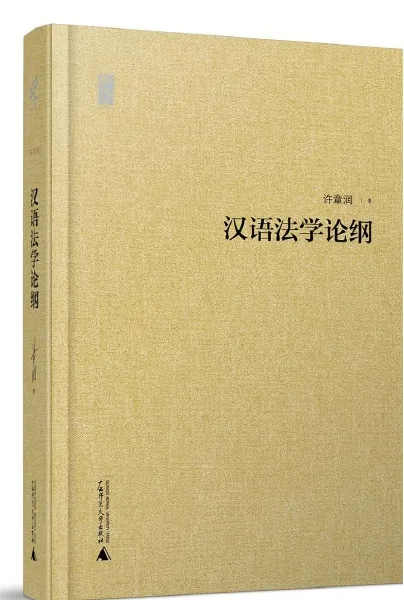
三
其次,在這本書中我期待更多的具體、詳細的實例,來說明漢語法學的傳承究竟有哪些。許章潤在提到有限的幾個例子時一般是蜻蜓點水,但是這樣的例子其實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僅需要簡單一提就可以。
我們埋葬了觀念意義上的“傳統(tǒng)”,并常常不惜一切代價摧毀實際存在的延續(xù)的“傳統(tǒng)”,那么,到底有哪些中國傳統(tǒng)需要被重建,到底有哪些還未被摧毀,需要我們在全盤西化的法學體系中加以調整?這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更具現(xiàn)實關照,和支撐“漢語法學”這一宏大體系更有說服力的論據(jù)。威廉·布萊克在批評雷諾茲爵士的論綱的時候曾說“泛泛而談是愚蠢之舉,具體細論本身就是一種優(yōu)點。”博而能約,才是理想之境。
不過,沒有什么瑕疵可以掩蓋這部著作整體價值關懷的重要性。其實,無論是在法學,還是歷史學,哲學,美學,甚至是金融學,新聞學這些所謂更“實用”的領域中,我們都應重新閱讀那些被遺忘的民國著作,我們都應該在接續(xù)傳統(tǒng)的基礎上,再開始談論什么“創(chuàng)新”。這才是真正的進步。可悲的是,在這個簡單的歷史進步主義占領絕對主流的國家中,我們的歷史卻一再陷入循環(huán)。今天,唯一滾滾向前的是我們的GDP數(shù)字,統(tǒng)計本身既不完全可靠,而且即使可靠,也無法反映經(jīng)濟的實際情況和人民的經(jīng)濟生活水平。
歷史有的時候真叫人感喟:1922年,鮑明鈐在離美回國前,給時任霍普金斯大學校長、著名憲法專家古德諾(F.J.Goodnow)寫了一封告別信。在信中他寫道:“如果我只考慮個人利益,我會選擇一個獲利更多和風險較小的職業(yè),而不是去從事公共服務事業(yè)。但我已享受的非同尋常的特殊利益,我的道義感卻推動我要走一條敢冒風險的道路。我相信上帝和我的人民不會使我失敗。”從1952年起就賦閑在家,后來又被抓捕的他,不知是否曾想起這封信里的話,他的內心又是什么樣的感受呢?然而如果他泉下有知,知道他的文字在八十年后又被人認真閱讀,曾經(jīng)照亮了一顆迷茫的心靈,他是否也會有一些欣慰呢?

(文/方墨,原載于《經(jīng)濟觀察報》)
好書推薦
阿彌陀佛么么噠
本書是大冰繼百萬暢銷書《乖,摸摸頭》之后的又一力作,依舊是獨一無二的江湖故事、特立獨行的潑墨文筆,卻愈發(fā)有情有義、有俠者魂、有赤子心,有如一碗酒,可以慰風塵。原來和《乖,摸摸頭》一樣,《阿彌陀佛么么噠》一書的這些主人公、這些故事都是真的;原來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人在過著你想要的生活:既可以朝九晚五,又能夠浪跡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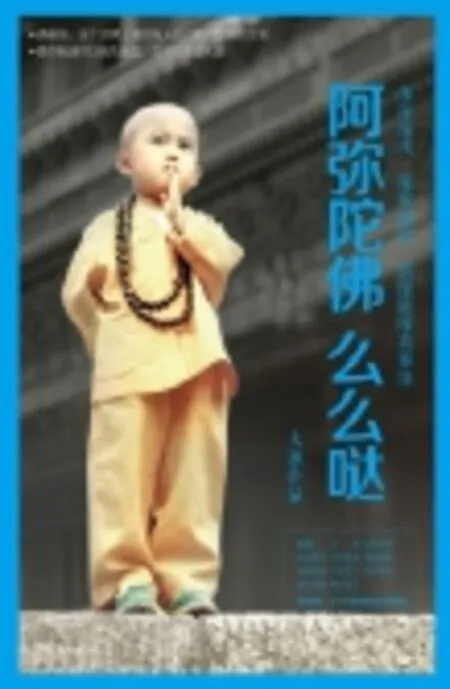

鋅皮娃娃兵
本書為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S.A.阿列克謝耶維奇所著。本書記錄了阿富汗戰(zhàn)爭中蘇聯(lián)軍官、士兵、護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血淚記憶,是20世紀紀實文學經(jīng)典作品。最令人難忘的是那些娃娃兵的母親,尤其是當娃娃兵被裝到鋅皮棺材里運回家時,母親們在墓地里講述著兒子們的事,就好像他們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