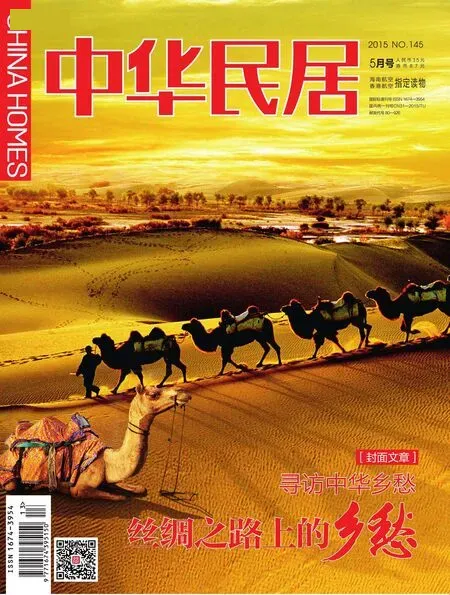千年土崖上的高臺民居
撰文/嘎瑪丹增 向明 攝影/嘎瑪丹增 姜曦 張新斌 技術審稿/譚洪起
千年土崖上的高臺民居
撰文/嘎瑪丹增 向明 攝影/嘎瑪丹增 姜曦 張新斌 技術審稿/譚洪起
喀什人民廣場上,有一尊毛澤東的巨型塑像,他揮手的時間應該是上世紀60年代末。偉人停留在不變的手勢里,俯瞰著南疆這座最繁華的城市。時間沒有在偉人肩頭存留,很多建筑的高度,已經一次又一次超越了他。只有在他的身后,東側以北的高崖上,時間卻是靜止的。緊鄰寬闊整潔的艾提尕爾廣場,有一條名叫吾斯塘博依巷的小街,穿過它,就是維族人集居的黃土高崖。當地人習慣稱其為“東營高地”或“高臺民居”。用黃泥和楊木搭建的房子,既像積木又像紙盒,密布在黃土高臺的東南坡地上,層層疊疊,錯落無序。

喀什艾提尕大清真寺,始建于1442年,是全疆乃至全國最大的一座伊斯蘭教禮拜寺,坐落在艾提尕廣場西側,曾是傳播伊斯蘭文化和教育培養教職人才的主要經堂。

高臺民居
高臺民居高高矗立在千年土崖上,眺望喀什新城,看云卷云舒,聽大地律動。


喀什老城的建筑明珠
公元九世紀中期喀什拉汗王朝時,一次洪水把黃土高崖一分為二。從那以后,手工業者居住在南坡。而王宮貴族居住在南坡北坡。
闊孜其亞貝西巷,翻譯成漢語意為“高崖上的土陶”。關于這條站在時光深處的小巷,完全可以忽略文字和史籍。時間和歷史,依然原原本本地靜臥在那里。公元893年,喀拉汗王朝(黑汗王朝)都城——怛邏斯(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江布爾),被薩曼王朝攻占,汗王奧古爾恰克率領所屬部眾遷都喀什噶爾。一些手工藝人也在那個時期,將住宅和作坊建在了緊鄰王宮的黃土高崖上。當年建成的闊孜其亞貝西巷,還就是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式樣。時間,在這里累計停留了1100多年。這個地方,就是喀什噶爾老城。
高臺民居蘊含著古人先進的居住理念和生態觀,對現代生態建筑的設計有著深遠影響。
高臺民居最大的特點就是原生態。首先,這里的房屋建設均就地取材,用泥土和楊木搭建而成,無須費多少周折,便直接壘成土房。楊木去枝之后,亦無須刨削加工,直接用來架構和支撐屋頂、閣樓和陽臺。建筑外墻均為手工建造,凹凸線腳不多,墻面大方流暢,多用土坯砌成,直接抹上麥草泥便成矣。這種“純天然”的民居,總給人一種這樣的錯覺:整個居民區看上去都是松松垮垮、晃晃悠悠,恍如“空中樓閣”。但神奇的是,這“空中樓閣”卻很牢固,千百年來風采依舊。

關于高臺民居的原生態,還有一點不得不提的是,高臺民居的厚墻小窗。眾所周知,西域地區晝夜溫差較大,高溫可達零上四五十攝氏度,低溫會降至零下十幾攝氏度。厚墻小窗的結構,夏季可以阻隔熱量侵入室內,冬季可以最大程度上減少冬季熱量散失,很好地發揮著“空調作用”,保證室內的溫度不至于波動太大。
高臺民居原生態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過街樓遮陽,保護巷道不至于遭受暴曬。這里的居民仿佛有意將房屋和巷道的概念模糊,要給人一種家的舒適感和歸屬感。數量龐大的過街樓群形成了連續天井,房連房,樓連樓,巷道狹窄而彎曲。走進巷道,仍猶如置身小院。過街樓擋住了熱量,使巷道在夏日里多了幾分涼爽。還有些樓房的擴建也不全然跨街而過。只從巷道露出一側,似展似縮,略顯出幾分含蓄。因挑梁只占巷道一半,便被喚作“半街樓”。

居住在闊孜其亞貝西巷的維族人,都有著強烈的戀家情結,使得這座高崖人口的密度遠遠超越了上海和北京,多數家庭數代同堂。太多人不愿意離開高崖新建住房成為極大的難題,只能充分利用空間發展。這里,隨時都在拆舊房蓋新房,建的樣式還是喀拉汗王朝的樣式,但用的材料顯然已經不是原色的泥土。然而,也正是這種高容積率,使得高臺屋能抵御大漠風沙的侵蝕,千百年來穩居崖上。與四處漂泊的游牧民族的帳篷相比,高臺屋顯然多了一些“抱團取暖”的智慧。
每每走到十字路口時,往往容易碰到一座更是奇特的房屋。房屋懸空于十字路口中間,四面又與其他民房相連,猶如一個哨崗,又如一個戲臺。在一些非十字岔路口,講究的維吾爾居民則會對岔路口處的房屋進行人性化改造。比如,若是在陡急的轉角處,房屋的側角往往要被削切。如此,既帶來了舒緩的環境感觀,又減低了潛在風險。正因維吾爾居民對建筑風格和平面設計的不拘一格,在這些隨意建造的樓上樓、樓外樓之間,形成了許多縱橫交錯、曲曲彎彎、忽上忽下、或陡或緩的小巷,如一張大網連通著這里的家家戶戶。
整個高臺民居的巷道忽上忽下,蜿蜒百轉,縱橫交錯,目光所及之處又及其相似,宛若一個巨大的迷宮。有許多外來游客來此游玩都曾迷路。尤其是有兩個意大利人曾在這里直繞到了天黑都沒走出,最后還是通過向民警求助才得以順利“逃脫”這座迷宮。當然,這里的土著居民是不會迷路的。他們是在利用巷道鋪裝的不同材質進行方位辨別。比如,鋪著六角磚的是通道,鋪著小磚塊的是死胡同,門前有光滑石子路的則大都是富裕戶或旅游接待人家。如果沿著用六角磚砌筑的道路行走,不論從哪個方向都可以輕易地走出迷宮。
經歷了數千年歷史的發展和積淀,土崖上形成了今天奇特的 民居景觀:房連房,樓連樓,層層疊疊,縱橫交錯。

過街樓

懸空樓

半街樓

隨著旅游業的發展,高臺婦女們用傳統手藝制作紀念品出售,她們經常聚集在一起織繡,交流比拼技藝,既度過了悠閑的時光,又能為家庭增加經濟收益。

隨著現代日常生活用具的進入,大多工匠的手藝失去了市場,原本世代以此為生的技藝逐漸消失。鐵匠艾買提大叔,成了高崖上為數不多的手藝人之一。
維吾爾居民的庭院內,綠色生機取代了外部的沙漠成為主導生活的力量。那是一種人對抗大自然的力量,同時夾雜著人性與自然的芬芳。
九曲庭院盡顯民俗風情
在高臺民居里穿行,樓房巷道縱橫交錯,幾乎分辨不出哪是誰家的院墻,哪是誰家的窗戶。只有一扇扇大門告訴你,這里又有一戶人家。戶外大門,多為兩扇門,莊重厚實,門上鑲有圖案花紋的銅質或鐵質護板壓條,吊裝兩個碗大的門環,那是用來上鎖用的。
當然,這里的居民多深居簡出,更多時候門是不上鎖的。只是,這門縫里面同樣掩藏著獨特的民居文化:大門如是一扇門緊閉,一扇門虛掩著,那么這一家有婦女和老人在家,通常只有熟人才能方便進去;如是敞開著,便表示主人們在家,等待客人的隨時造訪。維吾爾居民熱情、好客,尤好以歌舞相迎。昔日唐三藏取經歸途中,就曾在這里住過一夜。這不是傳說,而是《大唐西域記》里的真實記載。
踏入大門,便是高臺民居里的另一個世界。高臺民居的庭院布局也不拘一格。各種院落不盡不同,有的大、有的小,地形高低不同,空間利用也多不相同。但它們有著唯一的共同點:環境幽雅,果樹成蔭。無論是走進任何一所院落內,一種帶有濃郁西域風情的生機撲面而來。居所內,種植著大量的花朵和草木。院落、窗臺、柵墻、房頂、閣樓平臺,到處都擺滿了花草,猶如花園般的五彩繽紛。
維吾爾居民對院落的設計也頗有講究。富裕的人家在庭院內部的磚墻上也利用燒制的不同形狀的磚拼貼出美麗的圖案,與院內美景相映成趣,融為一體。一些大一點的庭院屋前一般設有回廊。回廊立柱上雕刻有各種花卉圖案,雕工精美,栩栩如生。回廊下設有護欄條,整體排列,井然有序。穿過回廊,便可走進居民的室內了。



驢車是維族人傳統的交通又運輸工具,至今仍在廣泛使用。
高臺民居內室的豪華和精致,完全有別于黃土粗泥的外觀。楊木雕飾的樓檐和欄桿,造形別致的花格窗戶,精心裝飾著居室空間。墻壁和地面由精美的花紋圖案組成,地上鋪著華麗的地毯,餐桌上整齊地擺放著銀亮的餐具和品種繁多的瓜果。所有的家具上均有雕飾或圖案。當然,最重要的是家家戶戶的壁龕或房間里最高的地方,都擺放著一本《古蘭經》。
高臺居民的小院總是溫馨而生機。這個封閉內向的庭院就是一個小的獨立世界,也是他們的專屬空間。他們設計的庭院與人及自然融合統一,恰是舒爾茨所描述的 “場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里的維吾爾居民是天生富有“場所精神”的,他們憑借著對大自然與自我的感知和體悟,創造了獨特的理想居所。

喀什高臺民居闊孜其亞貝西巷內一角
勤勞樸實的維吾爾居民是一個喜愛裝扮的民族。他們總樂于把自己的小庭院、小居室打扮得“花枝招展”。

維族少女帕子來提

高臺居民的生命始終與這方土崖緊緊聯系在一起。他們給了這片土地以生機,這片土地也給了他們以財富。
神奇的色格孜
早期維吾爾居民在修屋建房就地取材,并沒有發掘這土地里的“寶藏”。直到大約八百年前,有一個燒制土陶的匠人首先發現了這里的獨特土質。這種泥土質地細膩,粘性極強,是制作土陶器的絕好材料。人們叫它“色格孜”。于是,從那時候起,這座土崖上就建起了第一家土陶作坊。隨后相繼有很多土陶藝人在高崖上開設土陶作坊,生產土陶制品。
在過去的歲月里,土陶制品與維吾爾族人民的生活緊密相連。生活中一日三餐不離的“塔瓦克”(泥巴碗)、盛水用“庫甫”(陶缸)、挑水用的“庫扎”(土陶水桶)、洗手用的“吾肉克”(陶壺)、洗衣用的“臺西臺克”(陶洗衣盆),甚至包括嬰兒搖床、便具,還有捕鳥獵具等等,多達百種,全部取材于“色格孜”。神奇的“色格孜”無孔不入,滲入維吾爾居民生活的各個角落。
正是“色格孜”發揮著無所不能的作用,也催生了大量土陶作坊的繁衍。土陶歷史上鼎盛時期,高臺上有一百多家土陶作坊。當時全喀什市土陶作坊全部集中在這土崖上,所以這高臺民居又被當地居民喚作“土陶崖”。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許多土陶手工藝品都在漸漸退出歷史舞臺,手工土陶作坊亦在日漸衰落。如今高臺上僅現存古老土陶作坊已僅剩十余家。這僅存的十幾家土陶作坊,都是經過五六代祖輩留傳下來的,其泥土選料、過篩、和泥拌揉、坯體成形、彩繪、琢雕刻花、上釉、入窯燒制,出窯晾干等十數道工序,全是手工工藝。盡管現在可以用電動裝置旋轉成型轉盤,可以省去繁重的體力勞動,但是這些陶器藝人不愿取巧,仍在沿用傳承了八百多年的古老傳統方法,他們依然腳踏旋轉坯盤,用手捏塑,用草木燒窯……用于給土陶彩繪,上釉的顏色及加工方法也是祖傳配方。經過十余道繁重的體力勞動加工而成的土坯造型,最終成了一件精美的彩釉陶器或藝術品。尤其是陶罐和陶壺,提耳和把手都進行了夸張的設計,加上上面刻著的樹葉和蔓藤,被賦予了充足的民族特色。
如今的高臺土陶制品,更多地從原來的生活用品變成了藝術品。這是人們對土陶制品品質的肯定和褒揚,不僅因為工藝,更因為那糅合其間的厚重歷史。今天,依然有不少國內外的考古家、藝術家、收藏家不遠千里趕來高臺,只為一睹高臺土陶的“真容”。
正是維吾爾這個富有藝術天賦的民族,創造了高臺民居這座龐大的藝術城堡,守護著高臺民居這座歷史厚重的“維吾爾族活著的民俗博物館”——那是茫茫大漠中的一片獨具特色的西域文化綠洲,寄托著世人的景仰,也寄托著萬千西域游子的鄉愁。

清真寺

傳統土陶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