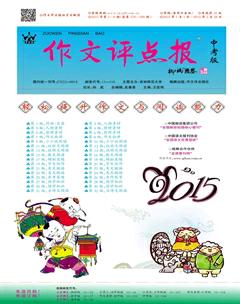進德與修業
黃濟
《論語》開篇第一章便是《學而》,可見“為學”在一個人生命中的重要位置與非同一般的意義。今天我們之所以要講“為學之道”,就是幫助同學們在重視道德修習的同時,重視提高文化水平。我們向先賢學習為學之道,從經典中汲取為學之法,許多經世流傳的道理,至今仍然指引著我們,在我們“學海無涯”的漫漫求索之路上,如明燈一般照耀著我們前行。
論“為學”,讓我們從至圣先師孔子論進德與修業講起。孔子的人生目標是修己以安人,要達成修己以安人,就要進行進德與修業,進德是導向,修業是基礎。
曾子在《大學》中,把他的修己、安人和進德、修業的思想概括為“三大綱領”和“八大條目”,也就是“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要達成這“三大綱領”,就要實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個條目。其中又以修身為本,前四者是修身的基礎,后三者是修身的施展。前四者又包括了修業和進德,后四者包括了修己和安人。如此,同學們可以感受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文”和“道”是密切結合、不可分割的,也就是提高道德修養與提高文化水平缺一不可。
為了說明孔子的修己、安人的人生目標,我們再舉在《論語·公冶長》篇中有關孔子和子路、顏淵師生三人各談志向的故事:“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愿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愿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段話講的是孔子、顏淵、子路談志向。子路說:“愿意拿出自己的車馬、衣服、皮袍,同我的朋友共同使用,用壞了也不感到遺憾。”顏淵說:“我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長處,不表白自己的功勞。”子路又向老師孔子說:“我也希望聽聽老師您的志向。”孔子便說了:“我的志向是讓年老的安頓,交朋友講信用,對少年關愛。”也就是說要做到撫老、攜幼、交友有信。對前輩、后輩和同輩都要有個正確的態度,以達成“安人”的目的,實現修己安人的理想,也就是曾子在《大學》中所概括的“三大綱領”和“八大條目”的內涵,體現著進德與修業的完美結合。
在孔子的修己、安人和進德、修業的思想中,也體現著力行與學文的統一。關于這個問題,《弟子規》講得非常辯證:“不力行,但學文;長浮華,成何人。但力行,不學文;任己見,昧理真。”就是說,如果只是背誦文化典籍,而不去身體力行,就會滋長浮華自滿的風氣,對于為人沒有意義;相反只注重行為表現,而不去增強文化修養,也容易固執己見,而不能通曉真正的道理。這說明了進德與修業是相互依存,不可偏廢的;力行與學文是相互作用的;文與道是密切結合的。
最后,還要談談在學習中的苦與樂的問題。學習要有所得、有所成,是需要下點苦功夫的。在《三字經》中講了許多勤學苦讀的故事,如:“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如負薪,如掛角,身雖勞,猶苦卓。”他們的苦學精神,值得青少年好好學習。《三字經》也講了許多學有所成的故事,蘇老泉二十七歲時“始發憤,讀書籍”,終于成了唐宋八大家之一;梁灝八十二歲時“對大廷,魁多士”,是老有所成的典范。除了這樣的苦學典型外,對于儒家來說,更為重視的是好學與樂學,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孔子提出的要求和所樹立的典范。他因而強調指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對于我們今天的同學來說,應該從多方面提高學習興趣,苦中求樂、以少勝多,把苦學與樂學恰當地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