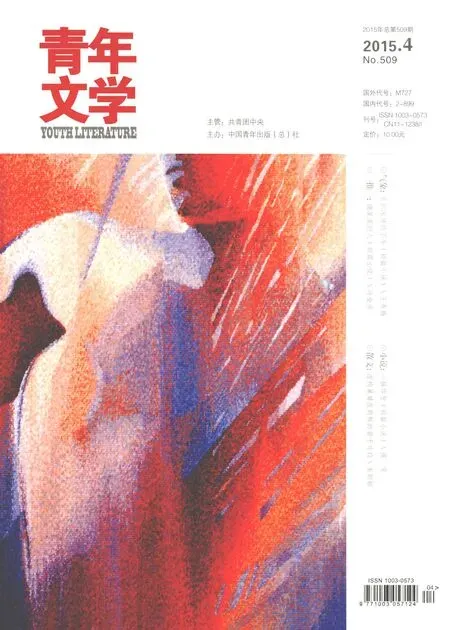草 暖
⊙ 文/黃詠梅
草 暖
⊙ 文/黃詠梅

黃詠梅:作家、文學碩士。作品散見于《人民文學》《花城》《鐘山》《收獲》《十月》等刊。出版有小說集《一本正經》《把夢想喂肥》《隱身登錄》《少爺威威》等。
【作品】
草暖今年三十歲了,她給自己未來的十個月定下一個莊嚴神圣的任務——每一天她都要想兩個不同的名字,一個男的,一個女的,當然最前邊的那個字是根本不需要考慮的,“王”字是她肚子里的寶貝今生今世的定語,當然也是草暖她今生今世的最前邊的一個姓氏。“王陳草暖”,這是草暖在二十七歲結婚后的名字。
王明白對草暖說,其實真的不需要這樣,結個婚難道連老爸姓什么都給丟了不成?我姓王,你姓陳,過去姓陳,現在還姓陳,只要你還姓陳就是我姓王的老婆。
草暖說,那還是不一樣啊,我是你王家的人了,當然跟你姓啊,你看香港臺新聞經常出來的那幾個女人,什么陳方安生、葉劉淑儀啊,不都是跟丈夫姓的嗎?再說我也沒有丟掉我老爸的姓啊,陳字還不是排在王字后邊,不是還在那嗎?別人一看就能知道我老爸姓陳。
王明白沒有吭氣,他一個大男人每天應對公司的事情那么多,對這些細枝末節的事情從來不想考究,名字嘛,不就是一個人的標簽罷了,又不是什么商品的品牌,非做得那么考究干什么?實際上他公司里的同事見到陳草暖都喊她“王太太”,根本沒有人知道她姓陳,名草暖,更加沒有人知道她把自己喚作“王陳草暖”。
但草暖還是在自己的朋友里邊堅持喚自己為“王陳草暖”。多么麻煩的稱呼啊,所以那些朋友無論跟陳草暖真熟還是假熟,都一律自覺地喊她——“草暖”。
自從三月份草暖懷孕以來,對名字的執著簡直就到了變態的地步,好像十個月以后生下來的是一個名字,而不是一個男孩或者女孩。
變態!有一次王明白真的就這樣說草暖。草暖沒有說話,眼睛里充滿了懷疑,好像懷疑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跟王明白沒有任何一點關系一樣。王明白那天在公司里跟董事長產生了一些不愉快,心情比較煩躁,所以順口就說了草暖這么一句。
草暖當然不會跟王明白爭吵的,懷孕前不會,懷孕后當然更不會了。草暖說懷孕了不能夠發火,要不然會把孩子氣掉的,也不知道她從哪里來的根據,但是這畢竟對草暖是件好事情,更不用說對王明白了。草暖這個人就是這一點比較適合當老婆,整個人就像她整天掛在嘴邊的那個口頭禪一樣——“是但啦”。只要有人征求她任何意見,結果別人總會得到她這句話,剛開始別人以為草暖有教養謙讓別人抓主意,久而久之就發現草暖真的是很“是但”。在廣州的白話方言里,“是但”就是“隨便”的意思。結婚后王明白甚至覺得草暖這樣“是但”的優點,比草暖煲的湯做的菜,比草暖長的樣子穿的衣服,比草暖瘦瘦的小腿尖尖的乳房等等都要好出很多倍。
可是,王明白卻不明白為什么草暖什么都可以“是但”,唯獨對姓名這東西卻不肯“是但”,對“王陳草暖”以及無限個還沒有確定下來的“王××”,她從來沒有說過“是但啦”。
從小學讀書開始,草暖就有一個綽號——“公園”,因為在廣州,草暖等于公園,這是誰都知道的。草暖公園位于廣州的越秀區,東風路的末尾,火車站的旁邊,是廣州流動最多人的一個地方,所以,草暖公園既是一個公園,也是一個公交車站的站牌。草暖不喜歡人家喊她“公園”,公園啊,聽起來就像公廁那么糟糕,再往下想草暖就會更加不高興了。
因為這個名字,草暖問過她的媽媽,她記得很清楚,就那么一次,后來媽媽跟爸爸離婚了以后,她想再問,就找不到媽媽了。那一次草暖放學回家,看到媽媽在家里熨衣服,那種很笨重的鐵熨斗,底部經常被草暖用來當鏡子照的,那個年齡草暖比較喜歡照鏡子,只要能看到自己的臉的發亮的東西,都可以被草暖當作鏡子來照,不管是一塊放學經過的櫥窗還是一小片窩在陽臺上的積水。草暖長得很像她的媽媽,越大越像了。草暖的爸爸也是這樣說的,包括草暖后來的媽媽也是這樣悄悄跟草暖的爸爸說的。也就是說,草暖一天一天地照著鏡子長大,奇跡還是沒有發生,她太像媽媽了,而媽媽長得太普通了。
當草暖問媽媽為什么要給自己取一個公園的名字的時候,草暖的媽媽稍微愕然地抬起頭看著已經高到自己肩頭了的草暖,然后放倒了鐵熨斗,熨斗的底部正正對著草暖的臉,草暖依舊習慣地朝著熨斗照了照。
草暖記得媽媽是這樣回答的——起個名字,是但好聽就得了,草暖,幾好聽啊!
媽媽很“是但”的回答令草暖很失望。說實在的,她多么希望媽媽能給她一個浪漫的解釋或者氣派的解釋,比如說她跟爸爸是在草暖公園認識的,比如說她跟爸爸在草暖公園散步的時候想到給未來的她取這個名字的,比如說草暖公園那個時候是他們單位共同修建的,比如說草暖公園有一棵杧果樹是當年他們將核埋進土里然后長成的……
但是草暖是個公園啊,媽媽。草暖不死心,總希望媽媽隱瞞了事情的真相,像她看到的很多言情小說一樣有著一段愛恨纏綿的情節。
公園?公園不好嗎?春天來了,草最早就暖了。你不記得了?小時候整天纏著爸爸媽媽要帶去公園的啊?媽媽繼續熨衣服,低著頭處理衣服上很難熨到的皺褶。
可是去公園不是去看草啊,公園有游樂場啊。草暖還要繼續追問。
那你就當自己是個游樂場好了!媽媽笑著刮了刮草暖的鼻子。草暖的鼻子跟媽媽的一樣,塌塌的,刮在上邊,跟刮在一張平臉上沒有什么區別。
如果草暖是個游樂場,草暖也許就會很快樂了。可是草暖是公園里的草啊,春天來了,草就長了,暖了,春天走了,草就矮了,黃了。一年春天有多長啊?尤其在廣州,冬天和春天簡直沒有任何界限,冬天走了一暖就叫熱了,成夏天了。
再說了,媽媽后來也沒怎么帶草暖到游樂場。在草暖十三歲那年,草暖的媽媽就搬離了草暖的家,她不知道媽媽為什么要離開草暖和爸爸,她從來沒有聽到過爸爸和媽媽吵架,但是媽媽卻忽然消失了。草暖什么感覺也沒有,好像媽媽只是離開她一陣,過幾天就會回來的。直到不久學校召開“單親家庭家長會”,老師遞給草暖一份油印的通知書,爸爸參加了,回來的時候摸摸草暖的頭說,明年,明年我們就不參加這個會了。果然,到了第二年,草暖就有了新媽媽。
長大一點草暖才知道媽媽跑到香港了,跟她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的表哥一起,說是去發展,誰知道呢?總之,草暖再也沒有媽媽的消息。
不知道為什么,草暖總認為是爸爸不要媽媽的,因為爸爸長得比媽媽好看,媽媽能找到爸爸那么好看的人,也算是前生修來的了,媽媽有什么資本挑剔爸爸啊?媽媽也更加沒有資本嫁到香港去才對啊。關于這些,草暖和爸爸沒有任何交流,因為新的媽媽一來,草暖的媽媽簡直更加人間蒸發得徹徹底底了,只是草暖這張臉偶爾會成為某種記憶的禁區。大概因為這張臉的緣故,草暖覺得爸爸不是很希望她結婚后再經常回家。
還好有王明白,他可以順利地將草暖的人生從春天過渡到夏天以及其他別的季節,反正只要春天過了就好,過了就是說開好了頭了,開好了頭后就沒什么大不了的了。
王明白既是草暖的初戀也是終戀。草暖二十六歲遇上王明白,那時候王明白從學校分配來廣州,是一個外來人口,沒有戶口本,只有一張戶口紙,夾在公司一摞厚厚的集體戶口里邊,輕飄飄、亂糟糟的。
草暖跟鄰居一起認識的王明白,本來也沒有什么相親的意思,只是周末單身漢約著一起湊熱鬧,打發打發,人越多越好,所以鄰居就把草暖拉上了。那次是到白鵝潭的酒吧街吃燒烤,大約有十個人,彼此都不是太熟,一個帶一個就組成了一幫。鄰居向他們介紹陳草暖,照例有人提到了草暖公園,草暖照例笑了笑沒做什么解釋,后來不知道是誰接著問草暖有沒有弟弟,草暖納悶地搖搖頭說沒有啊。那人說,如果有的話應該取名陳家祠。于是人群就都有了笑聲。草暖也笑了,頭一回有人將她跟陳家祠聯系起來。陳家祠跟草暖公園相隔遠著呢,在中山八路,是過去西關大戶陳氏的舊址,里邊是老廣州的生活模式,已經成為文物被保護起來。
人群挨著珠江邊吃起了燒烤,樣子都不是特別雅觀,但各自都跟各自靠近的聊起了天,邊吃邊聊,一直到了都看不清腳底是陸地還是珠江了。
草暖混在里邊,屬于人問一句自己答一句的那種。歷來如此,草暖在人群中就是不起眼的,樣子不起眼,說話也不起眼。
旁邊居然有人很準確地喊她,陳草暖,要不要來瓶可樂?
草暖很驚詫,側過臉去看那個人,一張陌生的臉,雖然剛才每人都被介紹過了,但是草暖一個也沒記住。
這個人居然能記住草暖的姓和名。
草暖回家以后是這么想的,既然這個人能完整地喊出自己的名字,那就是說這個人注意到自己了,注意到自己了也就是說對自己有好印象了。相反,草暖不是太能看清楚這個人的樣子,在夜色里只是覺得這個人不算高,有一張稍圓的臉。
所以第二天王明白打電話約她出去吃飯的時候,草暖自然就去了。
后來王明白就有秩序地跟草暖交往起來。
一年以后,草暖跟王明白去登記了。草暖帶著登記有草暖的爸爸和新媽媽的戶口本跟王明白到民政局登記那天,是夏天,廣州的熱浪熏得草暖覺得很不真實,好幾次草暖回過頭看王明白圓圓白白的臉上掛著幾粒黃豆大的汗珠,每次快要滾下來的時候,草暖都用自己的白手帕將它們接住了,然后換到另外一面再給自己擦擦。到了民政局,王明白從胸前的口袋里掏出那張薄薄的戶口紙擺在桌上,跟草暖那個有封面的戶口本一起,草暖翻到有自己名字的那一頁,攤開了,看看自己的名字,然后看看王明白的名字,心里才開始一陣高興——自己嫁給王明白了。
在王明白二十七歲到三十歲之間,不僅身邊多了個草暖,而且還多了很多下屬,短短三年,王明白像坐直升機一樣,一下子躥到了部門經理的位置。草暖笑嘻嘻地過上了好日子,換了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最近王明白還買了車。
“旺夫唄,有什么好說的?”草暖美滋滋地對自己的朋友說,她結婚后跟女朋友交往比過去密切了很多,話也自然多了。
實際上,草暖那張一點特色也沒有的臉,實在看不出什么“旺夫益子”的端倪來,鼻子不高,天庭不飽滿,兩頰無肉,下巴不兜,怎么看怎么普通。幸虧草暖不喜歡張揚,要不然妒忌她的人不準會說出什么話來損她。基本上她的朋友在她身上得出的結論是——好人還是有好報的。草暖是個好人,好人的定義在她們看來就是:不刻薄,不顯擺,不漂亮,不聰明。所以草暖這個好人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關于草暖的“旺夫益子”論,王明白雖然嘴上不以為然,但心里還是有一些相信的。客觀地說草暖這個老婆還不錯,很顧家,不奢求,不多事。可是王明白更多地想到自己一個大學生,這個時候不冒尖,這輩子要冒尖就很難了,看看周圍跟他經歷類似的年紀也差不多,現在不像那種熬資歷的年代了,更多的講究抓機遇,機遇錯過了就回家帶孩子好了。這聽起來好像比較殘忍,但事實如此。
而草暖只是不偏不倚地與王明白的機遇同時出現而已。
關于王明白的機遇論,草暖雖然沒有回應很多,但是心里也還是承認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王明白就是草暖的機遇。還有,草暖現在肚子里的“王××”,也是一個機遇。懷上了“王××”,草暖才明白,人要尋找機遇并且逮住機遇,是多么微妙的一件事情啊。
懷孩子是草暖提出來的。
王明白剛買車那一陣特別喜歡帶草暖出去,打打牙祭,吹吹山風。有時是為了吃大良的雙皮奶開車到順德,有時是為了泡泡溫泉開車到清新,有時甚至為了吃一個牛肉丸開車到潮州……只要離廣州半徑不超過五小時車程的,王明白都喜歡帶草暖出去,草暖坐在王明白的身邊,系著安全帶安靜地聽王明白車上放孟庭葦的歌,孟庭葦據說是王明白學生時代的偶像,一直喜歡到他當上了經理,并且開上了私家車了,還是初衷不改。草暖不喜歡孟庭葦,她還是比較喜歡聽粵語歌,什么梅艷芳、劉德華的,她都喜歡,她覺得用粵語說話,高高低低,長長短短,味道都很婉轉,光是說話就像唱歌,更何況唱歌?
這一次王明白帶草暖到東莞說是看一場內衣秀。草暖不是很想去,可是王明白想去,他說他們公司有幾個經理都會帶家屬開車去看。這樣一說,草暖就覺得有必要去了。草暖是王明白的家屬啊,能不去嗎?再說,看的是內衣秀啊,當然要帶家屬去了,難道要幾個男經理一起去?不太好吧?草暖當然去了,而且穿得很整齊,好像是去觀禮一樣。
到了東莞,草暖跟另外幾個家屬坐在一桌,男經理們則坐在另外一桌。那些穿著內衣的“內模”讓草暖看得很陶醉,草暖覺得真美,不是內衣美,而是身材美,女人美,她承認,女人美起來真的連女人都會被打動的。其中有一個草暖就特別喜歡看,每次輪到她上場草暖的目光都不會離開她。草暖看那女人的時候偶爾也會想想自己,如果自己穿上那些內衣也會這么好看嗎?其實這還用問?當然不會啦,草暖小時候很喜歡照鏡子,長大以后就不怎么喜歡照鏡子了,穿著外衣的時候不怎么照,更不用說穿著內衣照鏡子了,草暖早就記下了鏡子里的那個自己,普通得沒有任何奇跡的機會。
真是美啊,男人們不知道會怎么想?其中一個家屬由衷地嘆。
美有什么用?她們很慘的,找不到好老公才拋個身出來給人看的。另外一個家屬接話,有些嫉妒的成分。
也是,她們就是因為找不到好老公才出來當“內模”。草暖在心里這樣認同但沒有附和。側過頭去另外一桌看王明白,他跟幾個經理一起,講講笑笑,也猜不出在說臺上的還是別的什么。

⊙ 徐俊國·鋼筆畫9
一個沒有方向的未來,
多遼闊。
一顆風起云涌的心,
隨時飛。
看完內衣秀回家的路上,草暖的手機響了,是草暖一個久不聯絡的表妹,剛說不了幾句,手機就沒電了,于是草暖用王明白的手機給打過去,并吩咐表妹將她家里的電話發短信到王明白的手機上,王明白不經心地瞥了一眼短信就把手機閉了。回到家,草暖問王明白表妹家的電話是多少,王明白看也沒看手機就把號碼背了出來,草暖不相信,要王明白拿手機給她看,王明白給她看了那條短信,居然一個號碼不差!草暖心里忽然有一種恐慌,莫名其妙的。王明白的記性原來是天生的好!
那當然,我的記性在讀書的時候一直都是班上最好的。王明白很得意地笑了。
一直都那么好?那么準,那么牢?草暖求證。
又準又牢,所以考試總是考得好,現在記客戶名字和電話也記得很準確。王明白大概覺得這是自己的絕活,也是自己升職的一個訣竅,沾沾自喜地窩在沙發上,蹺起二郎腿翻報紙。
草暖想起那個白鵝潭的夜晚,王明白準確地問她,陳草暖,要不要可樂?連名帶姓地。
王明白不認識草暖這個表妹,也許壓根都不知道草暖還有這個表妹。草暖并不害怕王明白認識這個表妹,她只是害怕王明白的記性。
這種害怕隨著草暖幾個月后踏進三十歲一起踏進了草暖的心里,就跟三十歲這個年齡一樣,趕都趕不走了。
三十歲生日那天,草暖覺得有必要去發廊修修頭發了。草暖平時做頭發喜歡在附近的一個小店里,店不大,也不是什么名店,但是對付草暖那簡單的一把長頭發,綽綽有余了。草暖習慣到那里,一是因為師傅都熟悉了,二是因為師傅都不愛跟客人說話。是的,草暖剛開始以為師傅是不愛跟自己說話,后來她觀察過了,他也不太跟別的客人說話,只是喜歡在鏡子里盯著客人的頭發而不是眼睛看,這讓草暖感到很自在,師傅專心對付的僅僅是一把頭發甚至是一把亂草而已。她不喜歡別的那些發廊,無論是師傅還是小工都圍著自己團團轉,一會兒問她的工作怎樣,一會兒看著鏡子里的她夸她臉上的某個器官,一會兒還問她家里的先生如何,諸如此類的。草暖是個人問一句就答一句的人,即便不會多說,但總是不忍心不回答不理會,所以但凡問了就會回答,而且回答大多準確。所以,草暖只去這家發廊剪頭發,喜歡這樣無聲無息地坐在椅子上,偶爾看看鏡子里的自己,更多的時候是翻看理發店的雜志。
吃飯前,草暖的頭發就被洗濕了。照例拿起一本時尚雜志來看,一翻就翻到了一頁,大概因為人翻的次數多了,所以不由得草暖的手控制,一滑就滑到了那一頁。
這一頁是心理測試題。標題是——看看你生命中的最愛是什么?
類似這樣的測試題,草暖看過無數次,幾乎翻開每一本時尚雜志,做得光鮮、花哨的,基本上后邊都會有不少這樣的測試題,測感情的,測理財的,測魅力的……不需要看對象的,叫DIY,就是自測的意思。
在每道題選擇答案的地方,都有人用筆打了鉤。其中有一道很簡單,上面有五個人的字跡的。
題目是這樣的:
如果你在沙漠里迷路了,不得不按順序放棄你身邊所帶領的動物,它們是:老虎、大象、狗、猴子、孔雀,那么你放棄的順序是怎樣的?(結果請查看121頁)
草暖看了看已經有人選擇的順序,有兩個選擇將老虎放在前邊,有一個是猴子,有兩個是孔雀。
草暖不知道那代表著什么結果。
此時師傅將草暖頭頂那縷頭發暫時掀到了前邊,這樣草暖的整個臉就被擋了,埋在頭發里,草暖將那些動物排了個順序:老虎——大象——狗——猴子——孔雀。
她設想,自己在沙漠里,沒有食物、沒有水,自己都顧不上自己了,當然要先舍棄一些大塊的包袱了,要不然跟它們攬著一起死不成?也許,放了它們它們還能夠憑本能逃出生天呢,而猴子和孔雀是最需要保護的。
草暖生怕自己忘記了這個順序,在嘴上喃喃地念了兩遍。
臉上的頭發被撥走了,后邊的師傅看了看草暖,草暖的眼睛在鏡子里正好跟師傅的眼睛對接了一下,草暖的臉一下子紅了起來,而師傅卻沒有任何表情,把眼光挪回到了草暖的頭發上,大概是習慣客人都會翻到這頁做這道題吧。
沒準師傅是最早做的一個呢。草暖心里偷笑。
按照題目后的提示將雜志翻到了有結果的121頁,也是很容易一翻就到了。
草暖看了一看,心里就樂了。
這些動物原來分別代表著每個人人生里的一些東西:大象——財富,老虎——事業,狗——父母,猴子——孩子,孔雀——伴侶。
草暖心里一樂,接著就糊涂了,她記得自己的順序前邊是老虎,接著是大象,后邊是狗,沒有錯,但是最后兩個,是猴子在前還是孔雀在前的?她有些犯糊涂了,翻回到題目那頁看題目,老虎、大象、狗、猴子、孔雀,這是題目的順序,自己不可能按照題目的順序一成不變地選擇的啊,那就是老虎、大象、狗、孔雀、猴子?好像也不是啊。
草暖就這么猶豫著。
如果按照答案,那么轉換成的結果就是:事業——財富——父母——伴侶——孩子(或者孩子——伴侶)。
草暖還真沒有想過在伴侶和孩子之間,自己到底會先放棄誰。但是,她從來沒有想到過要放棄王明白,而孩子,因為沒有出現,更加談不上放棄了。
知道答案以后,草暖就再選不了最終的結果了,到底是猴子在前孔雀墊底,還是孔雀在前猴子墊底呢?草暖永遠沒有自己的答案了。
頭發終于做好了。師傅拿出一個小鏡子,讓草暖對著眼前的鏡子反看后邊的頭發形狀,草暖很笨拙,小鏡子總是對不準后邊的頭發,有好幾次從大鏡子里看到的小鏡子里竟然是身邊的師傅一張嚴肅的臉。草暖有些尷尬。
很好了,謝謝。其實草暖壓根就沒有看到自己后邊的頭發。師傅當然也知道,但是沒有吭聲,笑了笑,說,下次再來啊。
走出發廊,草暖不知道是因為修理過了頭發還是什么,居然覺得感覺良好,風一吹,有些許飄逸的味道。草暖路過櫥窗看了看,年輕了一些似的,依稀看到了少年時代滿馬路找櫥窗照的那個自己。
晚上王明白帶她到花園酒店的扒房吃西餐慶祝生日。
兩人在燭光下吃得一半,忽然草暖想起了那道簡單的測試題,就同樣拿來讓王明白選擇。
王明白想了一下,給草暖一個順序:孔雀——猴子——狗——大象——老虎。
草暖一聽,愣在了那里。
她問的時候沒有想到過王明白的答案,現在王明白做了答案,就出問題了。換算對應的結果順序是:伴侶——孩子——父母——財富——事業。
草暖心里很不舒服。
我的順序剛好和你的顛倒過來。現時,草暖可以肯定她最后放棄的是孔雀而不是猴子,并且是堅定地肯定,為了跟王明白完全顛倒。
這些東西都是騙人的,虧你還去相信。王明白看出了草暖的不舒服。
可是這是你心里選的,除非是你心里騙自己。草暖反問王明白。
你想想看,這是常識嘛,在沙漠里迷路了,當然先甩掉那些沒有幫助的甚至拖累自己的東西了,保存實力,出去了再返回來拯救它們啊,像孔雀猴子狗之類的。王明白跟草暖辯白。
可是,那些有實力的可以自救啊,先放棄它們,它們或許還可以活命啊,放棄那些弱小的,返回來肯定找不著了。
王明白想了一下,把手中切割好的一塊牛扒放到草暖的碟子上,說,這簡直都不是一個維度上的比較,完全兩種思維,你不要去踩這些陷阱,不要庸人自擾啊。
草暖想再說些什么。但看到王明白把肉放到了自己跟前,不由得就動手去叉那塊肉來吃,黑椒醬是王明白的最愛,草暖逐漸也喜歡上了那股胡椒的辣味。
那天晚上回家后,王明白要做愛,草暖就決定要有個“王××”。
一決定了,草暖就懷上了,王明白既不知道草暖的決定也不知道草暖那么容易就懷上了。
那就生下來吧。王明白無任何疑問。
那樣,草暖的肚子就一天一天地自由散漫地大了起來。
草暖肚子里的“王××”還沒有來到草暖和王明白的生活里,古安妮就先一步來到了草暖和王明白的生活里了。
王明白的女秘書叫古安妮,像一個混血兒的名字,可是草暖知道她不是混血兒,是江蘇人,長得高瘦,頭發烏黑發亮,臉上光光白白的,眉毛淡淡長長的,說不上很美,但是很有味道。對于草暖這樣長相普通的人來說,古安妮算是一個打不敗的對手了。當然,古安妮不是草暖的對手,她只是王明白的秘書,是在上班時間照顧她丈夫王明白的人。
草暖不是沒害怕過古安妮跟王明白會成為那種“經典關系”,但事實證明他們不是這樣的關系。
這是事實。
王明白有一天回來很氣憤地對草暖說他的秘書古安妮肚子大了。
當時草暖的肚子也開始大了,可以從肚子的外形想象孩子的頭手腳了,所以她一聽到王明白氣鼓鼓地說有個女人肚子也跟她一樣大了,她首先想到的就是,有多大了?幾個月了?孩子踢媽媽沒?
很顯然王明白并不是想跟草暖說古安妮的肚子,而是說古安妮。
古安妮是誰?
古安妮是我秘書,去年來的。
古安妮的肚子大了又怎樣?
古安妮是江蘇人,我面試的時候將她招來的。顯然,王明白真的不愿談古安妮的肚子。
古安妮的肚子大了不能在你那干了嗎?草暖關心的是古安妮的肚子。
古安妮很能幫忙,做事情很有條理,而且態度好。王明白還要跟草暖說古安妮這個人,可是草暖并不太想知道古安妮這個人,只想知道她的肚子,因為她不認識古安妮,也從來沒有見過。
但是后來草暖還是見著古安妮了,這個大了肚子的女人。草暖代表王明白去找古安妮,當然王明白并不知道。
草暖想到要去找古安妮,并不是因為古安妮跟自己一樣都是大肚子的女人,也并不是因為古安妮的肚子跟自己的肚子有什么關聯。只是,這個大了肚子的古安妮影響她的丈夫王明白的睡眠質量了。
自從王明白告訴草暖說他的秘書古安妮肚子大了之后,草暖發現王明白就在一種焦慮狀態中,吃不香,睡不安,最重要的是,經常莫名其妙就義憤填膺,也經常莫名其妙就很無奈。
古安妮的肚子跟你有什么關系嗎?草暖問王明白。但是她相信不會有什么關系,倒不是草暖有多自信,只是因為王明白下班一進門就告訴草暖這件事了,讓草暖覺得好像是他們夫妻倆要共同面對的一些雜事,比如汽車被人撞壞了車燈要索賠,比如小區的管理混亂經常有傳銷商進來很不安全,諸如此類的。王明白就是當成一件事來告訴草暖的。
當然沒有。王明白很坦白。
那,古安妮的肚子跟誰有關系?
她說是董事長的。
那,你為什么要生氣?草暖有些納悶。
我生氣是因為她不告訴我,她居然跟董事長有一腿。王明白像個受傷的小孩。
這種事情還要匯報你,經得你同意?草暖真覺得王明白有時候很令人哭笑不得。
她是我的秘書,我親自招來的。
可,她又不是你的人。
王明白聽草暖這么一說,就更加來氣了,在房間里走來走去,不坐也不站。
草暖后來才一點點地知道,古安妮告訴王明白,她被董事長看上后兩人就同居了,董事長開始承諾會跟他老婆離婚娶她的,誰知道,她等了一年也沒見董事長有什么離婚的動靜,于是就故意懷上個孩子來威脅董事長,已屆中年的董事長不吃她這一套,壓根就不當回事。眼看著肚子一天天大起來了,她只好警告董事長說,如果不跟她結婚她就把孩子的事告訴她的直接上司王明白,讓他身敗名裂。董事長聽了之后,冷笑一聲說,他王明白算個球,我開了他!
關鍵不是古安妮的肚子,而是董事長那聲冷笑。當古安妮把董事長的話照搬給王明白聽之后,古安妮的肚子已經不是一個已婚男人和一個未婚女人的庸俗故事了,成了一個男人和一個男人之間的糾葛了。
男人和男人之間的糾葛,當然不是指情感的糾葛啦,權力、金錢、尊嚴等等等等,更能成為男人和男人之間的糾葛。
那個中午,兩個挺著肚子的女人,桌子前放一杯清水,那是草暖的,古安妮喝的是咖啡。草暖很想告訴古安妮書上說懷孕的時候喝咖啡對胎兒不好,可是草暖克制住了,這不是這場談話的重點。
我覺得你這樣行不通的。草暖說話開門見山。
他會心軟的,他是愛我的,只不過放不下他的孩子。古安妮說話跟接電話時一樣好聽。
可是你和他的孩子還在你自己肚子里啊,他又看不到的。
可那終究是我和他的孩子啊。
他的孩子已經會代替他太太撒嬌了,你的還沒出生。
可是孩子終究是會出生的啊。
要么你辭職把孩子生好了跟他結婚,要么你辭職把孩子打掉離開他。草暖接連用了兩次辭職,她希望這個美麗的古安妮能離開王明白的公司,不管她要不要這個孩子。好像只有古安妮辭職了,王明白跟董事長的糾葛就從此煙消云散了一樣。草暖是這么認為的。
沒想到過了幾天,草暖就真的聽王明白說,古安妮辭職了。
草暖心里一陣驚喜,也顧不上問古安妮的肚子是不是還在。
王明白看上去卻有些悵然。
吃飯的時候,草暖問王明白,那個古安妮美不美的?
王明白想都沒想就回答草暖說,美的吧。
草暖的肚子越來越大,已經進入生產倒計時了。她忽然有些舍不得她的孩子離開她的肚子,好像孩子出生了,她的肚子就空空洞洞了,而她每天琢磨的那個“王××”一落地,性別、模樣、名字、一生,這些,就在世界面前揭曉并且塵埃落定了,也許孩子在肚子里的種種理想就會變成神話,每天過得都像等待奇跡一般,而草暖知道,等待奇跡的日子其實并不很好過的。
那個黃昏,草暖就這樣傷感地想著,坐在沙發上,也不知道時間什么時候過去的。直到王明白下班開門走了進來。
草暖慢慢撐著腰走過去接王明白的公事包,然后拉著王明白的手說,我想好了,要是生個男孩就叫他王家明,要是個女的,就叫她王家白,好不?
王明白沒來得及細想,心頭一陣感動,點了點頭。等到自己換好了拖鞋轉過身來,看到他的老婆,王陳草暖,挺著個大肚子,窩在淺綠的沙發上,穿一身紅底黑點的裙子,像極了附在草葉上的一只披掛著鎧甲的大甲蟲。

⊙ 徐俊國·鋼筆畫10
年華似水,陽光蕩漾。
每一個值得懷念的下午,
內心都是屬于芳香的。
作家自述
關于“草暖”這個人
⊙ 文/黃詠梅
《草暖》寫于二〇〇四年,是我在二〇〇二年開始的小說生涯中的第五個短篇。在我的心里,這不是一個短篇,而是一個人。
這個世界上,知道得越多,謎團就越多,縱使如此,我依舊覺得人的潛意識是最大的謎團。《草暖》這個小說發表之后,并沒有像我寫過的那些小說那樣離開了我。我在《南方都市報》寫評論專欄的時候,好幾年來,一直沿用“草暖”這個筆名。直到我遷居杭州,離開了廣州。
“草暖”這個詞,其實是位于廣州火車站邊的一個街心公園的名字。記得當年我大學畢業到廣州工作,一下車站,看到的就是這個“草暖公園”。這個名字是多么富有詩意啊,相比這座烏泱烏泱的大城市,這個烏泱烏泱的火車站,這個雖然不大的公園,卻顯得如此格格不入。如同那個剛從校園畢業仍懷著詩意進入這座物質之城的我,也是如此格格不入。在廣州生活幾年后,我開始學寫小說,就想著要用“草暖”這個詞做人名。出于對當初那種格格不入的紀念,或者出于對這個名詞強烈的南方意味的珍視,至今不得而知。但是,反諷的是,我那種格格不入的感受,一旦落到“草暖”這個人的身上,卻變成了巨大的想要融入這個地方的意欲。“草暖”這個人,“不漂亮、不刻薄、不顯擺”,沒有過多的甚至可以說沒有自我,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跟隨著飛黃騰達的丈夫王明白,過著安逸、安全的家庭生活,她是很多女權主義者所鄙夷的“附著物”。事實上,在我身邊,生活著很多這樣的女性,她們持家有方,以丈夫兒女為軸心,她們滿足于這樣的生存智慧。當時,在她們眼里,像我這樣一個三十歲仍不結婚生子,還堅守著文學理想不放的女人,才是格格不入的。我不清楚,當時寫這個女人的時候,潛意識里,是自己也想要做“草暖”這樣的女人,還是提醒自己不要做這樣的女人?
十年之后,我已為人妻,重新看這個短篇,我已經能理解“草暖”的那種不安和惶恐,同時,也能理解當年的自己,是懷著怎樣的糾結去寫的。這是她的天性和弱點,同時也是上天賦予她好命運的理由,因為,她的愿望如此單純和美好。
再也沒有如此單純美好的愿望了。就像那個“草暖公園”,這篇小說發表兩年后,就被夷平了,如今,那個地方建起了高大的建筑物。對于“草暖”這個名詞的記憶,除了出現在550公交車那個長久不更新的報站器上——“下一站,草暖公園”,還有就是,出現在我對十年前那個女人的懷念里。是的,我懷念這個叫“草暖”的女人,她一度被我擋在了家門口,被我嘴角那抹輕蔑的冷笑傷害過。實際上,她與我血脈相連。這一點,早就在我的潛意識里被鑒定過了,只是到今天我才明了。
賞析:弋 舟
又是一篇寫于十年前的小說。彼時的黃詠梅似乎能夠從這篇小說中向我們走來。她在自述中已經寫明白了作者與這篇小說相互糾結的程度,而一個作家的少作,在我看來,也的確能夠反映出作家本人和這個世界的關系。
不,我不是在說草暖即是黃詠梅,我是在說,也許如草暖一般,當這個虛構的人物在猜度自己腹中孩子性別的時候,提筆之初的黃詠梅,也在猜度著自己的文學立場。我用了“立場”這樣一個硬朗的詞,也許是嚴峻了些,但我覺得,就像大多數時候都“是但啦”的草暖一樣,黃詠梅也會在某些嚴峻的時刻,偏執地橫下心來。她在自己的寫作之初,就已經毫不“是但啦”地選擇了自己的文學態度——以最敦厚的心情去想象世界,以一種近乎平視的姿態去打量人間。這種態度決定了她的文風:散淡甚至閑適的敘述語言,風平浪靜乃至波瀾不興的情節設置。但,卻在散淡與閑適之中飽含深情,在風平浪靜與波瀾不興之下暗流涌動。這種文風的選擇,在某些作家那里,也許會是一種強迫性的遴選,而它之于黃詠梅,卻更像是某種水到渠成的必然。但是,我們一定不能輕視黃詠梅的自覺,要知道,相比于這種文風的反面,一個作家的寫作之初,往往更加容易陷入某種夸張的、矯揉造作的泥潭。人在初啼的時刻,往往會身不由己地想要嘹亮,而黃詠梅則可貴地順應了她的本性,只是發出了輕微的吟哦。這不但令她沒有被語言的狂歡劫掠而去,還令她一提筆,就有了一種寬大與寧靜的氣質。
相較于魯迅先生那著名的“不憚于”,敦厚的心情也許顯得不那么令人過癮,但它力量別具,反倒容易在平易之中教化了人心;而相較于俯瞰,平視的姿態當然更容易喚來人間的親切。平易與親切不重要嗎?當然重要,它們所能帶來的那種與塵世“血脈相連”的效果,從來是,也應當是文學的重要功能之一。當我們在文學中時時被振聾發聵的時候,那些低淺的吟哦與喟嘆,卻有力地平衡了我們的文學世界。
我還想要說的是,這個短篇的結尾寫得漂亮極了——“王陳草暖,挺著個大肚子,窩在淺綠的沙發上,穿一身紅底黑點的裙子,像極了附在草葉上的一只披掛著鎧甲的大甲蟲。”這個結尾,在我讀來,甚至不遜于卡夫卡那個著名的開頭——“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兩只甲蟲在文學的譜系里會面了,而這,正是文學那迷人的魅力所在。
散文
【銳散文】
⊙ 虛構舅舅在朝鮮的若干片段/朱朝敏
⊙ 草生/周 偉
【人文·地理】
⊙ 青海湖,請把我抱在懷中/郭建強
⊙ 暴雨上學路/趙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