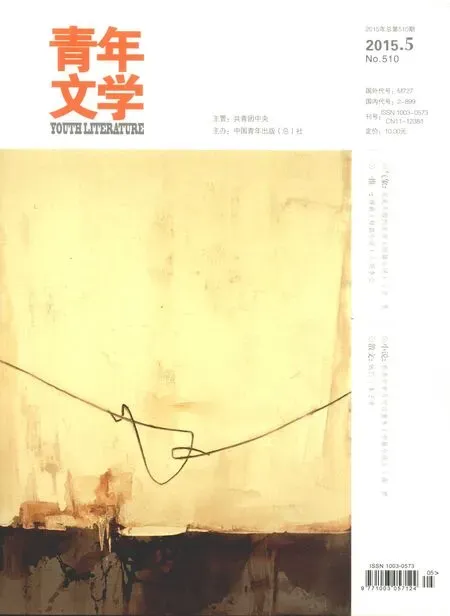文學創作的難度和收獲的喜悅
⊙ 文/張 檸
文學創作的難度和收獲的喜悅
⊙ 文/張 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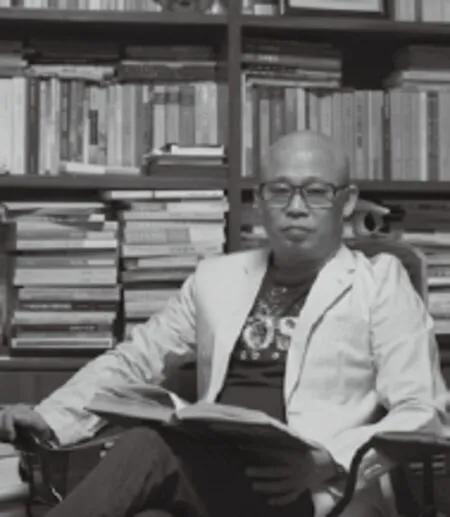
張 檸: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委員會委員,一級作家,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
北京師范大學2014級文學創作研究生班的十位學生,都是通過了普通研究生碩士入學考試之后選拔出來的。盡管他們在本科期間也寫過一些習作,但就小說藝術而言,基本上可以說是從零開始。我擔任他們的基礎課《文學創作》的首任教師。課程設置中不再有純理論環節,而是采用“實戰演習”的方式,直接進入寫作操練,并通過課堂討論和即席點評,激活他們的想象力、表達力,還有藝術結構意識。動筆之前,我給了限制條件:一、不統一命題,各寫各的,題材或主題不要重復;二、采用第三人稱限制視角;三、不要寫個人的經歷,要通過想象和虛構,展現“無中生有”的創造力。然后,要求他們每周在課堂上朗讀自己上周創作的小說片段,師生一起討論、切磋。八周之后,他們每人提交了一篇五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說:何慶平《錦衣夜行》、張鈺弦《電光幻影》、王怡《說不出的疼痛》、曹玥《敬愛的領導》、郭茜《喝酒之后》、于茜《再見,鄉村醫生》共六篇,還有被《青年文學》雜志資深編輯選中的、我下面將要點評的另外四篇。
這些小說盡管有青澀氣息,但我更多的還是欣喜。首先,十位作者對“虛構性敘事藝術作品”的創作方法有了基本了解,特別是有了自覺的文體意識,也就是將語言當作藝術要素來使用的意識,細節設置和情節布局與整體結構之關系的意識,審美情緒與敘事流動感之關系的意識。這種訓練,終結了他們以往寫作的隨意性和盲目性,使他們對藝術創造的難度有了切身的感受。綜觀十部短篇小說,藝術上各有千秋,寫的也都是作者自己未曾經歷過的陌生經驗,初步顯示出了他們的藝術虛構能力。如果單純地從當下流行閱讀所強調的“爽感”角度來看,未入選的作品中還有閱讀效果更好的,但遺憾的是,這并非純文學刊物的選稿標準。這也從另一個側面提醒年輕的作者們,文學創作的內核,不是將語言作為工具,去生產一些能夠引起“快感”的文字,也不是腦門兒一拍一個點子的所謂“創意”;而是對語言使用的創造性、對世界感受的敏銳性、呈現方式的獨特性;從這個角度看,雜志編輯所選中的這四篇小說,藝術上相對成熟一些。
于文舲的《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敘事動力來自對“快樂”的肯定,敘事目標似乎是要塑造一個“快樂者”的形象。但一開始,小說就進入了一個敘事的泥淖,顯得困難重重。這個困難不僅是于文舲的,也是中外文學史的。所謂“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寫苦難和悲劇更能引起共鳴,寫“快樂者”常常會事倍功半。于文舲的敘事,執意要穿越雙重障礙:“鬧劇”(虛假的快樂)和“悲劇”(現實生活),抵達敘事目標。主人公老K,一位被禿發所折磨的洗發水推銷員,一位被虛假快樂信息所糾纏的不快樂者,一位就著方便面喝酒、連夢都沒有的“屌絲”,雙腳離地被這個世界推向“快樂”。結尾“他閉上眼睛,忽然又笑起來,吹了聲口哨。現在世界上真的只剩下他一個最快樂的人了”。結果有點荒誕。但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敘事展開過程,也就是克服敘事阻力的過程。于文舲氣喘吁吁地完成了這個小說,效果還不錯。但也有問題,那就是敘事技術壓倒了整個小說的情緒,顯得有點生硬。
學醫出身的封文慧,入校前曾經寫過流行小說。這一次訓練對她而言,是一個折磨,也是一次提升。她的《煙花綻放》,把敘事焦點對準了底層生活。這種題材很容易寫得平庸,或者說隨心所欲地寫成一個所謂的“底層報告”。但這無疑不是本次“小說藝術”訓練的內容。如何在五千字左右的篇幅中容納這些蕪雜的內容呢?封文慧在結構上下功夫。敘事從“八小時前”開始,五小時前、三小時前、半小時前,以倒計時的方式聚焦到最后的時刻(焰火或者爆炸)。整個敘事過程中,形形色色的命運和表情呈現于作者筆下:拆遷工作人員的手忙腳亂、空巢老人的忐忑心情、青年女工將命運的改變寄望于相親、被騙光積蓄的男人每夜爛醉不醒……人物的速寫大多到位,諸多細節也勾勒出故事背后更廣闊的生活場景。但問題依然有,總體上還是給人雜亂的感覺。布局結構很重要,但它與意義結構之間的關系更重要。
萬芳的《門里的女人》,寫上海街道上的故事,顯示出作者對城市經驗敏銳的感受和捕捉能力。小說主要描述一位少女(咖啡館服務生家珍)眼中的成熟女性形象。一個居住在城里的女人,以一位旅人的形象出場,拖著拉桿箱,反復出現在咖啡館,陌生而神秘。其實它不過是觀察者家珍的自我形象的投射。我對小說敘事中那種曖昧不清的氣息感興趣,它傳遞了都市文化中特有的孤獨感和陌生感。這種描寫其實很有難度,在這一點上萬芳寫得不錯。我曾建議她修改小說中對話的方言,但她堅持保留。畢業于政法大學的萬芳,有很好的藝術感覺,但語言還是不甚圓熟。
王瑜的《之子于歸》,一個有古老詩意的標題:艷若桃花的姑娘出嫁了。但王瑜所寫的并非一個“宜其家室”的故事,而是對婚姻的疑問和恐懼。小說敘事不自覺地采用了兩條旋律并置的“對位法”:一是主人公奔喪后回憶爺爺奶奶幸福生活的回憶,一是主人公林西與男友沈培的情感糾葛。前者是敘事的目標,后者是敘事的阻力,但兩條線平行過多、交織不夠。王瑜的長處在于,敘事語言情緒飽滿充沛,有感人之處。她的問題在于技術簡單了一些。
總之,我對這些九〇后作者充滿期待。獨創性不僅僅取決于想象,也取決于閱讀量。技巧的熟練也需要時間,人家庖丁解牛十九年才達到那個境界。有些問題需要時間來解決,這背后有歷史哲學問題吧。近來有一位爆得大名的九〇后寫手在媒體上似乎是說,他們這一代不好懂,老人們不懂裝懂,云云。我覺得不要把自己說得那么嚇人,好像不能理解似的,你又不是類人猿,猿身上還有基因演變史呢。當我們用“歷史”和“審美”的雙重視角,來對一個“文本”給出“事實判斷”的時候,誰也無法逃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