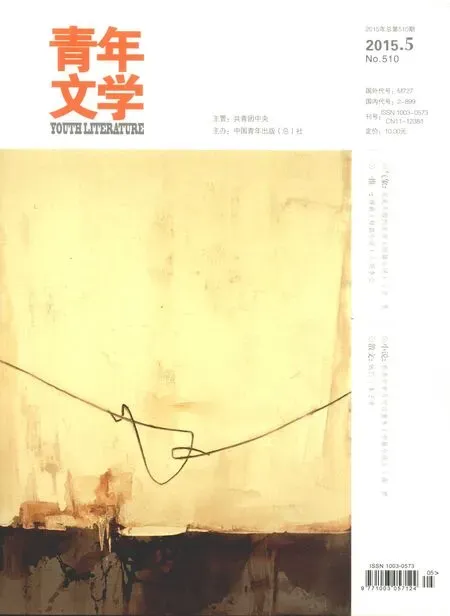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 文/于文舲
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 文/于文舲
于文舲:一九九一年出生,現為北京師范大學首屆文學創作方向碩士研究生,師從張檸教授、詩人歐陽江河。二〇一一年起嘗試各文體寫作,詩作入選伊沙主編《新世紀詩典(第三季)》,劇作獲首屆“戲文杯”全國校園戲劇劇本征稿比賽三等獎。
老K手中的離職材料已被汗水浸濕了大半。他站在走廊里,向老板辦公室挪動兩步,又退回來。從臨街的窗戶看出去,對面寫字樓的玻璃墻閃著明晃晃的二手陽光。玻璃墻下的汽車仿佛都是銷聲地行駛著,路邊的人那么小。他就在這時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
“喂?”他說。
“啊!”電話那頭的男人短促地叫了一聲,“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你說什么?”
“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你不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嗎?我看了你的故事。”
“不,我不是。”
“你應該是!”男人嚷道,“你應該——”聽筒里隱約傳來呼哧呼哧的喘息聲,“我是說,你需要快樂呀。”
天底下只有一類人總是比你自己還清楚你需要什么。作為推銷員——作為即將離職的推銷員,老K太熟悉這副腔調了。他忽然產生一種過來人的傷感。
“快樂?”他說,“謝謝啦,我不需要。”
掛斷電話,他的目光又被吸引到窗外巨大的玻璃墻上。光線和陰影都在游動。他發覺明暗之間有一張臉,頭發往上翹,胡子也翹著,像極了牌桌上的黑桃國王。想當初那幫吃飽了混天黑的鐵哥們兒,專愛舉著黑桃K大喊“老克(K),老克(K)”,然后反其道而行之,把李克叫成了一張撲克牌。黑桃國王是老大呀,滿臉都是氣派,老K想,那才是他們說的什么——最快樂的人。而他自己不過是個冒牌貨。老K低頭沖回辦公桌。他把衣領豎起來,還是能聽到同事們細碎的咳嗽聲。他們背著老K交換的眼神在空中吱吱作響。高矮胖瘦的黑桃國王坐在辦公室里,帶著不容置疑的笑容。
他突然明白了。怪不得,剛才電話里從頭到尾都帶著哧哧的笑聲。一出下流的惡作劇,老K想。他掐了一下大腿。的確有哧哧嗤的笑聲,他聽得出來。環顧四周,黑桃國王憤憤地埋下腦袋,他嘆了口氣。“老K,老K,”他對自己說,“你白叫了這么個好名字。你可真是黑桃K的名字,紅桃3的命。”
一周前,老K開始掉頭發。淋浴的水淅淅瀝瀝地灑下來,像在澆灌一棵七扭八歪的盆景植物。他雙手托住腦袋,弓著背,左腳猛地跨出去,右腳往后撤。水花發出怪叫。他張開雙臂保持平衡,沒有挪動半步。兩大團頭發像蟑螂爬向下水道,他踩住了它們。他俯下身去看,濕漉漉的地面映出一張老頭子的臉。拇指和食指插進去,攪碎那張臉。他捏起一縷一縷的黑發貼在墻壁上,仿佛洞穴深處的結繩記事者。
一個禿了頂的洗發水推銷員,實在有點不像話。何況三十來歲,也實在到不了禿頂的年紀。老K又把手心的汗往離職材料上抹了抹。必須要找出那個打電話的渾蛋,他在心里說。黑眼圈架在他鼻梁上,像望遠鏡。窗外的玻璃墻比太陽還要亮。桌邊的花草全都大頭朝下。胖老板倚在門框上,瞇縫著一只眼睛。老K貓下腰,瞪著他。一陣風吹過,老板打了個哈欠,他頭頂上千萬只小爪子揮動起來,像要順著門框一直爬到天花板上去。這個胖子,他在笑。笑容就像他開會訓話時的聲音那樣陰陽怪氣。
老K咬了咬指甲,攥緊一只拳頭。他死死地閉上眼。眼眶陷進去,望遠鏡變成萬花筒。他用另一只手扶正了帽子。
老婆把帽子戴在他頭上的情景,老K總也忘不了。那天,他發現浴室門口有個小姑娘探頭探腦,驚出一身冷汗。小姑娘踮著腳尖像在跳舞,她穿過蒸騰的熱氣,站在他跟前。他這才認出來了,是他老婆。結婚六年多,這個小他半歲的女人包裹在白茫茫的水霧中,看起來只有一丁點大。他使勁盯著她。他又想起那個滿臉褶子的醫生,五年前,他向老K保證,作為男人,老K壯實得很呢,他們生不出孩子,完完全全是他老婆的毛病。醫生還拍了拍他的肩膀。
墻壁上的頭發都被她攥在手心里了。她穿一條白色吊帶裙,拖鞋像兩只船。她伸直手臂,舉在身前,瞪著自己的拳頭,眼睛跟兔子似的,又紅又圓。醫生意味深長地微笑。老K搖搖頭,打了個寒戰。他接下她遞過來的干凈衣服,從里到外,也都是小小的。她幫他系扣子,像在裝扮自己的布娃娃。老K深吸口氣,把啤酒肚縮進去。衣服最下面壓著深藍色的帽子,窄帽檐撒滿月亮和星星。高樓大廈之間,太陽烤化了柏油路,他頂著這片搖搖欲墜的夜空,迎風走鋼絲。
他終于走進了老板辦公室。紅木椅子硌得他屁股底下生疼。他跟老板說他病了,好像還病得不輕,他把能想到的所有可能引起掉頭發的病往自己身上安了個遍。他語速飛快,偶爾搖一下腦袋,月亮和星星就跟著升起又落下。“我看你是太累了。”老板打斷他,“像你這樣勤勤懇懇的員工,還是應該找份更適合自己的工作,這樣也能快樂些。你需要快樂,對吧?”老K觸電似的抬起頭。老板右邊的嘴角抖動了一下,似乎就要笑起來,左半張臉卻看不出什么動靜。老K瞪著他,頭皮發麻。
老板又說了什么,老板在他的離職材料上簽字,老板把鋼筆捏得嘎嘎響,老板的胡楂冒出來了,密密麻麻全是小黑點,老板左眼中間有塊黃斑。這時他發現老板有根白頭發。在腦袋頂上偏右一點的位置,對著燈光閃閃發亮。這位胖老兄,老K舒了口氣,忍不住嘻嘻地笑起來,他想起平日里老板講得唾沫橫飛,濃密的頭發甩開一面大旗,直到散會,還是一絲不亂的。他摘掉帽子,拿在手里扇了兩下。老板收住話頭,仰臉瞧著他。白頭發也瞧著他。老K欠身鞠了個躬,把星星扣在白發上。“噓,”他說,“你需要這個。”
走出辦公樓,老K整個人空空的直往上飄。古怪的電話仍在耳邊回響。“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你不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嗎?”老K學著電話里的腔調說。誠實一點的話,他得承認,這聲音其實也沒那么像老板。老K望著自己的腳尖,笑了笑。電話對面的小子應該比老板還年輕些,氣喘吁吁好像有點興奮,可不知為什么,老K總覺得那聲音皺巴巴的,像揉爛了的牛皮紙。他莫名其妙地哼了一聲。
然而后來接二連三的電話和短信竟沒一個找他老K的,人們像是約好了,個個都聲稱要“找世界上最快樂的人”。老K渾身的神經又緊繃起來。“打錯了,”他說,“這里沒你要找的人。”可他們卻說:“沒有錯,我就找你。”他們賭咒發誓,老K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胡扯,”老K撇撇嘴,“難道你們比我自己還清楚我是什么人?”
“那當然,”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我們看了你的故事啊。我們這叫‘旁觀者清’。”
老K覺得這幫人都該進精神病院。他漫無目的地游蕩,從這條街奔向那條街,遇到路口,再拐回來。他的身體薄得像張撲克牌,一會兒向前倒下去,一會兒向后仰。紅綠燈發出他聽不懂的嗡嗡聲。
他又看到那個大肚子的男孩。灰白條的背心太小,堆在肚子上面。尖尖的腦袋連著長長的脖子,長長的胳膊和腿像風中拉扯的電線,墜了個巨大的燈泡。這讓男孩每動一下都帶著“吱呀,吱呀”的回響。他站在兒童福利院門口,用食指戳自己的肚皮。

⊙ 李云雷·光影11
老K跑過大大小小好幾家兒童福利院,這事他沒告訴任何人。他在街邊站定,咬住下嘴唇。他聽見自己對著電話說:“好吧,你讓我相信我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那你給我講一個我的故事。”他騰出一只手,揉了揉眼睛。還沒到下班的時間,街上人不多。兒童福利院的大鐵門生著銹,青色油漆剝落的地方冒出幾朵小紅花。男孩不見了。人們告訴老K,他是怎樣向電線桿脫帽致意、怎樣在下水道遇見一只貓、怎樣為玩具鼓手吹喇叭、怎樣往臉上抹口水假裝眼淚然后陰錯陽差撞進馬戲團……
老K聳了聳肩膀。他仰起頭,攤開臉龐望太陽。
他還記得昨天見到男孩時,自己的褲兜里有兩顆薄荷糖。他用拇指和中指捏住一顆,食指一彈,另一顆就滾到口袋深處去了。他把手中的糖遞給男孩。“嗯,我想,吃糖是不會死的。”男孩撕開塑料紙,摳出糖豆扔進嘴里。他的腮幫蠕動,像食蟻獸。其實老K也沒見過食蟻獸,但他就是覺得像。“吃糖不會死,”老K重復了一句,“嗯,是啊,是不會。”
“那也不見得。”男孩糾正說,“得小心,必須得嚼碎些。你看,我肚里的瘤子有這么大,我的胃都擠到嗓子眼去了。”男孩在肚皮上比比畫畫,勾勒一幅戰略地形圖,“我每天吃得很少,得嚴格控制,而且絕對不能太硬,否則胃脹起來會把瘤子弄破,我就得死了。”男孩的聲音從腹腔深處傳來。
“放心吧,你不會死,”老K對著肚皮說,“只有我這樣的老頭子才會。”
“可你不是老頭子。”
“跟你比我就是。”
“那我叫你爺爺吧。”
“不行,你得叫叔叔,”老K摸了摸帽檐,“我兒子比你還小些呢。”
老K的電話又響起來,他一激靈。男孩在記憶中往后退了一步,瞪眼瞧著他。他掏出手機,是一串陌生的號碼。
男孩說:“你這人真麻煩。你兒子?他怎么受得了你?”
電話還在響。老K按下通話鍵。
男孩拿起藥膏和棉球,沿著肚臍周圍層疊的粉色波紋涂。
電話里的人說:“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我是你的粉絲。”
這些歡天喜地的人究竟在說什么呢?老K隱約覺得,他們掌握著一個關于他的秘密——一個特別重大的秘密,可為什么,他們越是急于告訴他,他就越覺得糊涂了?他看著男孩肚子上的粉色波紋。波紋裂開了千萬張嘴。男孩做個深呼吸,千萬張嘴于是一齊張開,又一齊,像是被什么掐住了喉嚨,慢慢合上。
小姑娘說:“我真喜歡你,我男朋友要是能趕上你的一半我就知足了。”
嘴巴再張開,再合上。再合再張。
小伙子說:“等著瞧吧,你早晚會火,到時候你就發了。”
男孩的睫毛真是長得出奇,一根一根直勾勾地指著老K的褲兜。老K隔著褲子攥住薄荷糖,另一只手不停地摳著凳子上的螺絲釘。
他感覺雙腿又酸又軟,使不上勁。靠在兒童福利院的外墻上,老K撥通了老婆的號碼。他說:“我們不要孩子了,不要孩子了!弄出個小崽子干什么,他會要了我的命!”他摸到胳膊上大片大片的雞皮疙瘩。電話那頭先是一愣,接著傳來尖細的哭聲。哭聲就像她的小辮子。那天她舉著帽子站在他跟前,老K現在才想起,她往上一夠,腦后兩條小辮子撲棱起來,像對黑色的翅膀。也許他們會有個女孩。她會給女兒梳同樣的小辮子,軟軟地彎下來,拖到肩膀上。再系一根紅絲線,綰成蝴蝶結。他嘿嘿地笑了。
晚上老婆值夜班,老K跟哥們兒耗到十點多才回家。電話稀拉下來,好幾個小時沒有響動了。他伸伸懶腰。這真是個貴人多忘事的世界,老K想,唉,他還在指望什么呢?他拎出抽屜里最后一包方便面。紅紅的辣椒粉,碧綠的香菜,黃白相間的蛋黃和蛋清打著轉,咕咕直叫。他盯住一塊黃色,它似乎成心要甩掉他的目光,沒頭蒼蠅似的四處亂撞。這滋味讓老K想吐。他扣上鍋蓋,透明的,還能看到水在下面越滾越高。水撲出來,火被澆滅了,鍋蓋又狠狠地扣下去。他用雙手捧住腦袋。辣椒粉和香菜掛在鍋邊,像生日蛋糕上的彩色糖霜。他垂手站了一會兒。
半夜十一點二十四分,老K還在一根一根挑著他的面條,電話響了。他知道那是找誰的。
“你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男人用挑釁的語氣嚷道。背景里有機器運轉的聲音,緊接著是“咕咚,咕咚”,酒精的味道熏得老K暈頭轉向。
“對,是我。”老K說。
“他媽的!”醉漢的聲音又提高八度,“這他媽的世界,還真有快樂的人?!”
“有啊,”老K說,“我。”
“嘿,他媽的!”電話那頭的聲音像是一巴掌拍在大腿上,“那你倒是給我說說,快樂的人,長什么樣?也是他媽的兩只眼睛一張嘴?”
從來沒人提過這樣的問題。更確切地說,從來沒人向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提過什么問題。所有打來電話的人都看過一部名叫《世界上最快樂的人》的電影,他們告訴老K,在電影里,世界上最快樂的人親口報出了這個電話。他們撥通它,對接電話的人說:“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我是你的粉絲。”——這是沾了人家的光,老K心里發虛。但人們不是非要他相信嗎,他就是那個最快樂的人。當然,關于這個人,他們沒什么可問老K的。老K壓根就不知道有這么一部電影,他覺得這個名字傻里傻氣的。他旁敲側擊地向哥們兒打聽,果不其然,被奚落了一通。兄弟們說:“老K啊老K,看不出來,你還是個老清新啊!”后來老K就不想找這部電影了。他從始至終都沒問過老婆,他覺得她最近不怎么快樂。
“快樂的人嘛,”老K盯著碗里紅艷艷的方便面湯,“沒錯,也是兩只眼睛一張嘴。”
“說仔細點。”醉漢命令道。
“他的兩只眼睛,一只那么大,是單眼皮,另一只小的,倒是雙眼皮。你說怪吧?”
醉漢沒吭聲。
“他的嘴——對了,你打牌嗎?嗯,撲克牌——他的嘴是一顆黑桃。”
醉漢還是沒吭聲。老K伸長胳膊,夠到桌角的鏡子。黑桃國王在他身后謙卑地微笑,豎起大拇指。他也豎起大拇指。他覺得自己的鼻子長得真不錯。高高的鼻梁,薄薄的鼻翼,鼻頭稍向下彎,洋氣得很。整張臉,他最得意這個零部件。“快樂的人長著一只鷹鉤鼻。”他隨口說。
“呸!”醉漢突然大喝一聲,嚇得老K心臟都跟著哆嗦。“什么他媽的鷹鉤鼻!”醉漢說,“你給我聽好了,快樂的人是豬頭鼻子。”
“憑什么?”
“不憑什么,他就是!就是豬頭鼻子!”
“噢。”
又是“咕咚,咕咚”兩聲。
老K的鼻頭在鏡子里左歪一下,右歪一下,圓圓的鼻梁,圓圓的鼻翼,圓圓的鼻孔直往上拱。他的左眼長大了,是單眼皮,右眼小小的卻是雙眼皮,他的嘴就像黑桃。他抓了抓腦瓜頂。“快樂的人今年三十七歲,他有一頭黑亮濃密的頭發。還有胡子,直往上翹。那氣派……這么跟你說吧,”老K不出聲地樂了,“他的半張臉像小孩,另半張臉,像個老頭子。”
“老頭子?是那種老不正經嗎?”醉漢認真地問。
“對對,是那意思。”老K說。
“噢。”
“那么能不能再請你告訴我,”醉漢接著說,“快樂的人——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是怎么快樂起來的?”
“喝酒唄,”老K搖頭晃腦地說,“一醉解千愁,聽說過吧?”
“呸!”棕紅的大手從電話里伸出來,揪住老K的衣領,“你敢說快樂的人是酒鬼?!買醉誰不會啊,他媽的,你糊弄老子!”
“那他可能還……呃,唱唱歌跳跳舞什么的?”老K試探地說。
“呸!唱歌跳舞?那是白癡才干的事。你他媽敢說快樂的人是白癡?!”
衣領越卡越緊,老K臉憋得發燙。他覺得累了,可他逼迫自己使勁地想: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到底都干些什么來著?“他做夢。”老K幾乎是喊出來的。
他真的做過一個夢。他站在密封的木盒子里,四壁緊壓著他的身體。黑暗中有個聲音對他說:“在你的頭頂,有只鴿子。”他仰起頭,只看到黑暗。黑暗中的聲音說:“伸出你的手,你能摸到它。”他把右手食指頂在盒蓋上。食指穿透了盒蓋,外面的空氣很涼。接下來是第二根手指,第三根,還有第四根和第五根。十指,然后腦袋,胸膛。黑暗托起了他。整個后背鉆出盒子的時候,他生出翅膀。他在飛,像黑暗一般。夜空真大,風是清涼清涼的。
老K推開窗戶。黃澄澄的月牙兒掛在天邊,老K對著它,扭了兩下。影子在地板上忙活,手舞足蹈卻總是跟不上趟。真滑稽,他指著影子哈哈大笑。桌上吃剩的方便面結了一層紅油,他抬起頭向四周瞧了瞧。他想起客廳的柜門里還有兩塊桂花小點心。
抓住他的手松開了。老婆睡眼惺忪地走進門。
“我做夢。”老K又重復了一遍,“快樂的人應該做夢。”
“什么快樂的人?”老婆問,“你在跟誰說話?”
老K沒有回答她。他三口兩口就干掉了兩塊小點心,白色的碎渣從嘴角漏下來,他用手接住了,又抹進嘴里。他鼓著腮幫,沖老婆笑。
“是的,我知道你的夢,世界上最快樂的人,”醉漢說,“我看了你的故事。”
“那你給我講一個我的故事。”
“你向電線桿脫帽致意。”
“后來呢?”
“你在下水道遇見一只貓。”
“后來呢?”
“你為玩具鼓手吹喇叭。”
“后來呢?”
“你往臉上抹口水假裝眼淚然后陰錯陽差撞進馬戲團。”
“后來呢?”
“你死了。”
老K覺得腦袋里像放鞭炮,噼里啪啦響。他問:“我是怎么死的?”
“吃糖死的。”醉漢說,“你在哄孩子,你把糖豆拋起來,張嘴去接。糖豆正巧掉進氣管里。你的臉發紫,孩子笑了。你也笑了一下。”
“什么,什么孩子?”老K身子軟綿綿的,他問,“哪兒來的孩子?”他看了看老婆。她坐在床上愣愣地望著他,眼睛又紅又圓。
“看馬戲的孩子唄。”
“噢。”老K想起了兒童福利院里那個大肚子的男孩,反正他吃糖是不會死的,老K扭過頭對老婆眨眨眼睛,“瞧吧,糖豆就是給小孩吃的。大人連吃糖豆的本事都沒了。”他把手探進褲兜,慢悠悠地吐了口氣。可問題是,他——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死了,他該怎么辦呢?他實在太困了。
他掛斷了電話。閉上眼,他忽然又笑起來,吹了聲口哨。現在世界上真的只剩下他一個最快樂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