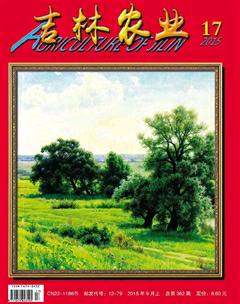喜鵲將村莊從夜里撈出
胡興法
喳喳、喳喳。
有一只鳥在房后,這么近地叫了兩聲。冒冒失失的。像一個人喊錯了一兩句話,又馬上用手捂住了嘴,噤若寒蟬。
我從床上翻了個身,眼晴瞪得大大的。可是什么也看不到。我這次回村子,客居在親戚家,瓦房頂蓋得嚴實。連一塊亮瓦也沒有。其實有亮瓦也沒用,看不到一星兒光。黑夜是一頭大獸,我們被它銜在嘴里,還沒吐出來。
瞪多大眼也沒用。盡管我們自詡目光遠大。這只鳥反倒看清了一切,興許包括床上翻身的我。它冒冒失失地把看到的叫了出來。幸好只兩聲,被誰喝住了。
接著我又睡過去了。直到天大亮。我睡得連親戚家的雞鳴聲都沒聽見。
天亮后,我把這種喳喳、喳喳的鳥叫聲說給親戚聽。親戚是近七十的老人了。他平靜地說,這是鴉雀子。也就是你們說的喜鵲啊。
好吧,就叫它喜鵲吧。
第二個晚上,我再次聽到了喳喳、喳喳的兩聲鳥叫。一定還是它。似乎與昨晚是同一時間。我抬眼,除了兩聲鳥鳴,什么都看不見。接著,我又睡了過去。不知睡了好大會兒,親戚家的公雞叫了一小陣。甕聲甕氣的。太早了,它們還被關在雞柵里。聲音給頂回了一部分,叫得不利索。像有人捏著鼻子唱歌。
雞叫了,天就快亮了。這常識我有。
但我不知道,原來有比雞起得更早的。它是喜鵲。一只喜鵲起得這么早,一定是個先覺者。鳥一般也是一個村莊的常住民。別以為天高任鳥飛。它們有能力高飛,但它們從不放縱翅膀。常住鳥很少飛離村子。人類說不清楚,只能猜想:或是一只巢,一個家;一只母鳥,一只情人鳥;一個村莊,一座山;一片林子,一棵能筑巢的樹。這些都足以留住它們。
雞胡亂叫了一氣之后,喜鵲就開始正式喳喳地叫起來了。這回有很多只了。叫得理直氣壯的。這個小村莊的鳥兒們在開晨會了。喜鵲定是領班。他們在商量很多大事。如果我們認為它們的事不大,它們早就認為我們的事一定全是扯淡。人從未承認除人之外能有多大的事,鳥也從未認為除鳥之外能有多大的事兒。
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
這叫聲在人類耳朵聽來,粗糙得很。彎兒不繞一個,調兒不變一聲。不像其他鳥叫,脆生生的。鳥喉嚨里如灌著一包水。
喳喳,喳喳……這叫聲,像刀擦磨刀石。像對罵的兩個人都將嗓子眼兒吵破了,一點兒也不像家有喜事才登門的喜鵲打鳴。
這時,雞又甕聲甕氣地叫上了幾遍。喜鵲叫聲與雞鳴聲將小村莊從黑夜里撈了出來,抬了出來。這一夜村莊里發生了些什么,什么在此消彼長,人們自作聰明所說的時間又弄丟了多少,那一只最早叫的喜鵲一定知道。其次是雞。再其次是喜鵲們、鳥們。后來才是我、村莊的人。
天亮后,我做的事便是一直盯著它們的窩看。我仰了一天的頭,徘徊在村莊的每條路上。村莊的人都以為我很高傲。出門三天,忘了家。看我需要仰視。其實,我是在仰視更值得仰視的東西。
喜鵲窩村莊里比比皆是。它們與村民比鄰而居。它們壘窩選擇大樹。樹小了,它們嫌棄。不知它們是想顯身份,還是想表現高風亮節。高大的樹上舉一只鳥窩,那定是喜鵲窩。仰脖細看,窩也并不精致。一些壘窩的樹枝還冒出幾枝,橫七豎八地戳在空中。不收斂,不規范。像出頭的椽子。這群開晨會、發號施令的家伙,居然一屋不掃,自己小家搞得粗制濫造,是何以掃天下的呢。
這是深冬。樹葉都落光了。樹干樹枝光禿禿地直戳天空。喜鵲的窩一覽無余。
它們來來往往地向窩里飛。黑的頭,白的肚子。雙翅與尾閃著黑緞子樣的光。標準的一身禮服。起跳,飛行,降落,舉手投足,喜鵲是最具紳士風度的。燕子都只是它的仿版。叫聲這么難聽的鳥,卻長得風度翩翩,不可思議。
我就這樣追著它們,仰頭看了一天。我在親戚家是做客,本無所事事,卻不經意間干了一件大事。而且從黑夜中某個時刻就開始了。以后我走路,養成了仰脖的習慣。以前一直是點頭哈腰的。
下一次,我準備看村莊里的另一種鳥,或一只雞、一條狗也行。不方便仰脖看,我就選擇蹲下……這樣下去,我會知道好多只有我一個人知道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