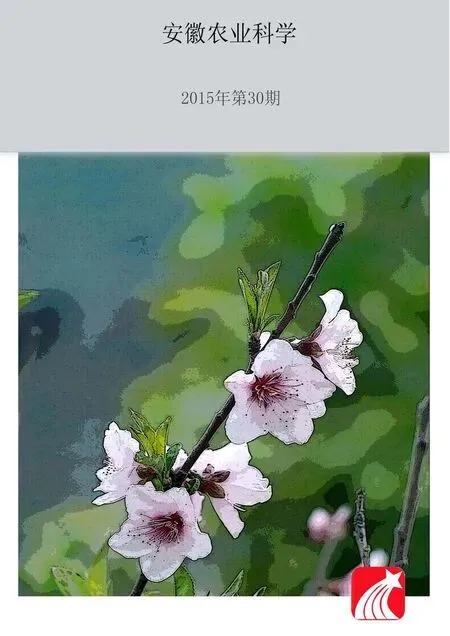大豆灰斑病發生特點及抗病遺傳育種研究進展
程 偉,常芳國,趙團結,孔杰杰
(南京農業大學大豆研究所/國家大豆改良中心/農業部大豆生物學與遺傳育種重點實驗室(綜合)/作物遺傳與種質創新國家重點實驗室,江蘇南京 210095)
大豆灰斑病發生特點及抗病遺傳育種研究進展
程 偉,常芳國,趙團結,孔杰杰*
(南京農業大學大豆研究所/國家大豆改良中心/農業部大豆生物學與遺傳育種重點實驗室(綜合)/作物遺傳與種質創新國家重點實驗室,江蘇南京 210095)
摘要從抗病育種角度出發,綜述了大豆灰斑病病原菌生物學特點、生理小種分化與鑒別、病害流行規律與防控、大豆對灰斑病抗性的鑒定方法與抗病種質(基因)發掘、抗病常規及分子育種等方面研究進展,并提出了大豆灰斑病抗性育種研究應加強病菌致病機理及生理小種劃分、抗病資源(基因)發掘、常規與分子育種相結合等對策。
關鍵詞大豆;大豆灰斑病;生理小種分化;抗病育種;分子標記
大豆灰斑病又稱褐斑病或蛙眼病,病原菌為(CercosporasojinaHara),稱大豆短胖胞,屬半知菌亞門真菌,其異名為Cercosporidiumsofinum(Hara)Liu & Guo,是世界性病害。1915年首次在日本報道,很多年后陸續在其他國家也有發現,如美國、中國、英國、德國等[1-3]。在我國黑龍江、吉林、遼寧、山東、河北等省灰斑病嚴重,少量在湖北、安徽、江蘇等也有發生。其中黑龍江省發病最嚴重。歷史上大豆灰斑病的發生與危害出現4次大流行。另外,大豆灰斑病的危害癥狀是侵染大豆的葉、莖、莢和子粒,使品質變劣,降低光合速率從而降低產量,造成輕者減產10%~30%,重者減產50%~100%,嚴重影響商品價值。筆者綜述了大豆灰斑病發生特點及抗病遺傳育種研究進展,提出了目前該方面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并展望了今后的研究方向,以期為大豆灰斑病防治提供參考。
1大豆灰斑病的生理小種與流行規律
1.1大豆灰斑病病原菌及其生理小種分化大豆灰斑病病原CercosporasojinaHara的分生孢子梗多為5~12根,不分枝,呈淡褐色。孢子有膝狀屈曲,孢痕可見,具1~9個隔,大小(24~108)×(3~9) μm,形狀、大小因培養條件不同略有差異。分生孢子萌發時從兩端細胞長出芽管,有時也從中部細胞長出[4]。黑暗條件下有利于病菌的生長與產孢萌發,陽光直射對孢子萌發有明顯抑制作用。在大豆葉葡萄糖培養基上該病菌生長最快,在小白菜瓊脂培養基和番茄瓊脂培養基上產孢量最大[5]。
大豆灰斑病菌具有明顯的生理分化,存在高度的遺傳變異。如Kim等[6]研究表明來自美國6個不同地區的132個大豆灰斑病原菌的標準化基因型多樣性值在26%~79%,還發現阿肯色州的灰斑病菌存在有性繁殖現象,可見,生理小種劃分工作重要。目前國內外多個國家和地區已對大豆灰斑病生理小種進行了劃分(表1)。國內多個研究應用鋼5151、九農1號、雙躍4號、合交69-231、Ogden、樺南綠大豆(現改用合豐 22)為鑒別寄主,對黑龍江省為主的灰斑病菌樣進行鑒定,分別鑒定出11~18個生理小種,其中1號小種是東北春大豆產區的優勢小種[7-10]。馬淑梅[11]對2006~2010年黑龍江省大豆灰斑病生理小種的監測結果表明,1號生理小種在各大豆產區出現頻率最高,為50.5%,平均為40.1%;其次是7號,出現頻率為35.9%,平均為26.2%。出現頻率較高的還有6、10和11號生理小種,平均出現頻率分別為18.8%、12.0%和9.6%。近期研究表明15號生理小種有增加的趨勢[10-12]。
國外研究中,巴西采用10個鑒別寄主鑒別出22個生理小種[13],美國早期用一套由16個品種組成的鑒別寄主鑒別出11個生理小種[12]。近期,Mian等[14]研究了來自美國、巴西、中國的93個灰斑病病原菌對 38個大豆品種的致病性差異,結果67個美國菌株可歸為13類,其中54%屬于第1、2類群,15個巴西菌株則屬于其中8個類群,中國的7個菌株分別屬于7個類群。最終篩選出Davis、Peking、Kent、CNS、Palmetto、Tracy、Hood、Lincoln、Lee、Richland、S100、Blackhawk共12個鑒別寄主,鑒定出5~15號共11個生理小種。Scandiani等[15]首次在阿根廷發現11和12號生理小種(表1)。
1.2病菌的分子鑒定利用分子標記能較好地反映出病原菌之間的遺傳關系。張俊華等[16]用引物對ITS1和ITS4PCR擴增我國東北大豆灰斑病菌16個生理小種的DNA,均得到600 bp片段,繼而用HinfI、RsaI和HaeIII 3種限制性內切酶將擴增產物消化,得到15個多態性片段,可將16個生理小種區分開來。孫洪利等[17]利用10對多態性高且穩定性好的AFLP引物組合,對黑龍江省121個菌株進行分析,共獲得148個多態性條帶,以遺傳距離小于0.81為界,將111個單元型劃分為6個類群。丁俊杰等[18]利用11對SSR引物對黑龍江省的24個灰斑病菌菌株進行EST-SSR基因型分析,結果共檢測出等位變異46.0個,平均每個位點為4.2個,相似系數范圍為0.091~0.956,平均相似性系數達到0.589;聚類分析結果與大豆灰斑病生理小種間呈現出較高的相關性。

表1 大豆灰斑病生理小種鑒定結果匯總
Bradley等[19]對來自美國(44個大豆灰斑病生理小種)、巴西(10個)、中國(7個)、尼日利亞(1個)等地共62個菌株進行AFLP標記分析,結果發現小種之間平均遺傳多樣性值高達0.56。聚類分析發現2個來自喬治亞州的生理小種被聚集到一起,2個來自中國的生理小種被聚集到一起。在美國QoI殺菌劑可以有效控制大豆灰斑病的發生與流行,近期發現抗該類殺菌劑的大豆灰斑病菌,研究發現QoI-抗病包含G143A突變的細胞色素b基因,導致一種氨基酸替代丙氨酸甘氨酸。其聚合酶鏈反應和TaqMan探針開發可以有效辨別QoI-抗病和QoI感病[20-21]。
1.3病害流行規律與防控一般在苗期和花期只能見到少數病斑,但是在大豆鼓粒期后病情發展迅速。氣象條件、感病品種布局及田間菌源量等條件都會影響大豆灰斑病的發生和流行。孢子萌發最適溫度為28~30 ℃,溫度范圍為10~40 ℃,生長最適溫度為25~28 ℃,萌發和侵染需要較高的濕度。pH為3~9時均可生長,最適溫度下分生孢子在水中1 h即可萌發,pH為5~6時最適宜。影響病害發生程度的主要氣象因子是濕度和降雨量,研究發現,東北地區大豆灰斑病發生與7月上旬、下旬降雨量呈顯著正相關;降雨量大、周期長,相對濕度較大,病害發生會較重[22-23]。
劉惕若等[24]認為大豆灰斑病是一個多循環病害,葉、莢病情田間流行曲線均呈“S”型。還根據病粒率與氣象因子的相關關系建立了早熟材料和中晚熟材料的灰斑病粒率預測多元回歸方程,預測病粒率與實際調查的病粒率十分接近。顧鑫等[25]利用2005~2013年黑龍江省東部地區大豆灰斑病發生情況和相應的氣象因子數據,采用逐步回歸方法建立包括的回歸預測方程,可對該地區大豆灰斑病發生情況進行中短期預測。
灰斑病流行與大豆耕種方式、病原菌、品種等因素有關。研究發現在美國大豆生產體系中,不施用殺菌劑條件下發病程度與耕作或免耕方式之間無顯著差異。殺菌劑的應用顯著減少了發病嚴重程度,產量漲幅為1%~17%。殺菌劑應用時,免耕耕作的大豆發病嚴重程度沒有顯著降低[26]。
2大豆抗灰斑病種質鑒定
2.1抗病鑒定方法與指標大豆灰斑病主要侵染幼苗、葉、莖、莢和種子[27]。帶菌種子長出幼苗,子葉上病斑明顯,多是半圓形、圓形、稍凹陷,深褐色。葉片發病,初為褪綠小圓斑,后逐漸擴展為邊緣褐色,中央灰褐色或灰色、直徑為1~5 mm的病斑,葉背中央有時密生灰色霉層,即為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嚴重時導致葉片枯死并脫落。莖部發病形成橢圓形病斑,褐色。病輕時僅產生褐色小點。豆粒上病斑與葉斑相似,多圓形蛙眼狀,也有的呈不規則形,邊緣暗褐色,中央灰白色。
目前田間鑒定大豆灰斑病等級多分為5級。曹越平等[28]先按病斑的大小和病斑的有無將病斑分為5種:B 斑、M 斑、N 斑、S 斑、O 斑(直徑> 3 mm、2~3 mm、1~2 mm、<1 mm、0 mm) ,并對上述5種病斑分別賦予 5、4、2、1、0 的權重系數;再按病斑數量的多少將病情分為5個級別:1、2、3、4、5 級。將病斑數量的級別數與病斑種類的權重系數相乘,其乘積即為病斑型級數。在進行病情調查時,以每個植株感染灰斑病較重的葉片為代表,表示該大豆植株的病情。而Sharma等[29]進行數量抗性鑒定時,根據整個植株葉片枯萎或壞死所占比例分0~9級(枯萎/壞死):枯萎、壞死均為0級;1級是 1%~10%/1%~5%;2級是10%~20%/6%~10%;3級是20%~40%/10%~20%;4級是40%~60%/20%~40%;5級是枯萎>60%,壞死>40%;6級為落葉達到33%;7級是落葉>66%; 8級是落葉>66%;9級為整個植株死亡。
2.2抗病種質篩選不同地區和來源的大豆材料對灰斑病菌的抗性存在差異,同一品種對不同的病原菌的抗性也有差異,所以選育抗病材料是抗病育種的基礎。國內外均進行了大量研究。我國從5 000余份國內外大豆資源中鑒定出一大批優異抗源(表2)。如陳慶山[30]從50個主栽品種中篩選出抗8個以上生理小種的品種系17份,其中抗10個生理小種的代表品種有1572、巴24、農大13699等。研究發現進化程度低的原始材料中抗源較多,對166份野生大豆鑒定發現表現免疫和高抗的分別有57和38份,占58.30%,表明野生大豆中抗源豐富[31-32]。而對東北地區的916份大豆品種進行抗性鑒定,其中來自黑龍江省、吉林省表現免疫的分別有0.31%、1.55%,表現高抗分別有9.09%和11.46%[33];對我國南北方大豆品種系進行抗灰斑病鑒定,結果發現不同地區和來源的品種、品系均有抗灰斑病的材料,北方高抗材料比例較高,育成品種的比例要高于品系[34]。
國外也開展類似抗源篩選工作,如美國對世界各地1 686份種質資源對灰斑病強致病菌株C-32抗性鑒定,發現有 660 份為抗性(0~3級)材料,韓國資源抗源較多[35]。Mengistu等[36]在2009~2010年通過田間接種大豆灰斑病11號生理小種鑒定發現,Davis、PI532465、PI567302、PI56748160、PI490766、PI567330、PI567333A、PI567432A、PI567432B、PI567438、PI532463A、PI567477、PI567478、PI567490、PI63945、PI538383、PI538386B、PI567291、PI567319B、PI567316A、PI567333B品種都表現出抗性。

表2 大豆種質對我國灰斑病小種抗性鑒定結果匯總
3抗病育種研究
3.1常規育種美國開展大豆抗灰斑病育種工作較早,早期選育出的抗病品種有Wabash、Clark等。1986年美國西北部受到灰斑病的嚴重危害,對P746、Shillageet、PK719、Bragg、VLsoya2、Himso507、Himso10 7個品種進行抗病鑒定,發現其病情指數達到了50%。其后育成一批抗病品種,如Doles、Maxcy、Holladay和VLsoya2等。近年來美國公共研究機構的育種家開展了較全面的新品種抗性鑒定工作,又選育出一大批抗病品種[45]。
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大豆抗灰斑病育種工作。劉忠堂[46]采用一次雜交,連續接種,定向選擇的方法培育了合豐28、合豐29、合豐33、合豐34號等抗灰斑病大豆品種。迄今已育成推廣合豐號抗病品種20多個。其他單位也育成一大批抗病品種(系),如東農42、東農43、1574、9674、593、墾農18、合輻93154-2、黑生101、建農1號、建豐2、北豆30、北豆35等。東農9674、合豐29和合豐34能抗黑龍江省8個以上生理小種[47-48]。由于東北地區大豆新品種審定要求對灰斑病的抗性達到中抗以上,目前大豆審定品種的抗性水平不斷提高。如通過雜交育種獲得的合農64和合農59均抗大豆灰斑病品種[49-50]。
3.2抗病基因發掘與分子標記輔助育種大豆對灰斑病生理小種的抗性是由單顯性基因控制,國內發現控制1號、7號和15號小種的Hrcs1、Hrcs7和Rcs15抗病基因[51]。利用東農9674(高抗)×東農87-104(高感)F2群體發現3個與抗病基因Rf1的連鎖的RAPD標記;為利于分子標記分析,還將抗病基因連鎖的RAPD標記轉化為共顯性的SCAR標記SCS3620&580[52]。張文慧等[53-54]用東農40566(抗)和東農410(感)雜交衍生群體接種1號生理小種,發現位于C1連鎖群上的3個SSR標記可能抗性基因連鎖。Dong等[55]用Gang 95144-1和Gongjiao 9723-6 2個親本雜交獲得的F2代,接種大豆灰斑病7號生理小種鑒定其抗病基因,并命名為Hrcs7,將抗病基因定位在E連鎖群(15號染色體),與Satt411的遺傳距離為7.9 cM。姜翠蘭等[56]研究發現,墾豐16對15號小種的抗性受1對顯性基因控制,定名為Rcs1,抗病基因位于J連鎖群Satt 529和Satt 547之間,遺傳距離分別為18.5和-6.7 cM。對108份大豆新品系進行標記檢測,Satt 547和Sat_224的檢測準確率達到85%以上,可用于分子標記輔助選擇育種和抗源篩選。丁俊杰等[18]以黑龍江省103份已鑒定抗大豆灰斑病3個生理小種的品種(系)為材料,同時利用7個標記(Satt565、Satt547、Satt431、Sct_186、SOYGPATR、Satt244、Sat_151)構建了供試品種(系)的分子身份證。
美國通過經典遺傳學方法已發現控制1號、2號和5號小種的Rcs1、Rcs2、Rcs3、Rcs5等抗病基因。利用Blackhawk(S)和 Davis(R)2個親本雜交獲得的F2群體以及F2∶3,Wright和Wright6-Rcs3的近等基因系接種3號生理小種,發現位于J連鎖群(16號染色體)2個標記Satt244、Satt547與Rcs3連鎖[57];進一步加密標記,在Rcs3周圍0.3 cM范圍內11個SNP,其中AZ573TA150和AZ573CA393可以直接應用于分子標記輔助育種[58]。近期又將PI 594891、PI 594774對灰斑病的顯性抗病基因精細定位在13染色體72.6 kb區間,包含5個注釋基因,其中3個基因(Glyma13g25320、Glyma13g25340、Glyma13g25350)的序列在抗感材料間有差異。已對Glyma13g25340、Glyma13g25350基因SNP變異開發出KASP標記用于標記輔助育種[13]。
Sharma等[29]利用Essex×Forrest RIL群體的94個家系接種灰斑病2號生理小種,分別在21和42 d調查家系抗病反應,結果定位到2個對灰斑病表現部分抗性的主效QTL,1個在6號染色體(C2連鎖群)Satt319標記附近,LOD=3.8,R2=52%,1個位于8號染色體Satt632附近,LOD=3.6,R2=15%。通過單標記分析,還在A1、B1、F、G、H、I、J、K、L、M 和O分子連鎖群上檢測到13個微效QTL。
4問題與展望
大豆灰斑病生理小種分化明顯,國內外對小種劃分都進行了許多研究,國內目前采用6個鑒別寄主材料,鑒別出多達18個小種[10];美國則提名了12個鑒別寄主材料,鑒別出11個小種[14]。由于二者沒有相同鑒別寄主,中美鑒定出的小種間還難以一一對應,其致病性等也難以比較,制約了進一步的研究工作。因此,建立一套標準鑒別寄主品種十分必要,有待有關研究者合作完成。此外,大豆對灰斑病抗性鑒定體系也需要統一和完善,包括小種選用(混合或單用)、處理時期、調查鑒定標準等。如我國大豆灰斑病病情分級一般按病斑數量分4~6級[27],國外有將灰斑病病情分為9級,還有數量抗性鑒定則更復雜[28]。
大豆對灰斑病抗性育種工作已取得很大進展。分子標記輔助選擇技術可彌補常規育種的不足,實現基因型的直接選擇。目前抗大豆灰斑病基因發掘工作相對落后,雖然已發現多個抗病基因,但只有Rcs3和位于13染色體的抗病基因被精細定位[13,58],可用于分子育種的分子標記很少。高通量測序技術不僅使對大豆轉錄組和基因組進行細致全貌的分析成為可能,更使挖掘高通量多態性 DNA分子標記成為現實,該方面工作需要加強。目前,分子輔助選擇育種只能對主基因控制性狀的選擇,對大量微效多基因控制的性狀的選擇方法與技術仍待進一步研發。另一方面,大豆灰斑病菌侵染大豆致病機理研究也有待加強,可發掘相關基因通過轉基因育種提高大豆抗病性。
化學防治大豆灰斑病的效果好,但對環境和土壤都可能產生一定的污染,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近期在美國還發現對防控灰斑病的QoI殺菌劑產生抗性的灰斑病菌[20]。因此,種植抗病品種是防治大豆灰斑病理想方法,并且依賴于抗病品種選育的速度和水平。由于灰斑病原菌小種構成復雜,優勢小種變化快,從大豆生產實踐看,仍需在考慮抗病品種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耕作栽培方式、化學防治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YORINORI J T,SINCLAIR J B.Cercosporasojina: A set of differentiated cultivars races for identification[J].Phytopathology,1982,72:173.
[2] 劉忠堂.解決我省東部地區大豆灰斑病的途徑[J].黑龍江農業科學,1985(1):20-30.
[3] 廖林.大豆灰斑病研究概況及展望[J].中國農學通報,1992,8(1):6-9.
[4] 曹越平,李海英,劉學敏,等.大豆灰斑病菌(CercosporasojinaHara)及其對寄主作用的研究[J].植物病理學報,2003,33(2):116-120.
[5] 鐘兆西,王偉,張桂榮.大豆灰斑病菌(Cercosporasojina)生物學特性的研究[J].大豆科學,1989,8(3):288-294.
[6] KIM H,NEWELL A D,COTA-SIECKMEYER R G,et al.Mating-type distribution and genetic diversity ofCercosporasojinapopulations on soybean from Arkansas:Evidence for potential sexual reproduction[J].Phytopathology,2013,103(10):1045-1051.
[7] 黃桂潮,霍虹,張再興,等.大豆灰斑病菌(CercosporasojinaHara)生理小種鑒定結果初報[J].大豆科學,1984(3):7.
[8] 霍虹,馬淑梅,盧官仲,等.黑龍江省大豆灰斑病菌(CercosporasojinaHara)生理小種的研究[J].大豆科學,1988,7(4):315-320.
[9] 馬淑梅,李寶英.東北春大豆灰斑病菌生理小種鑒定結果初報[J].植物病理學報,1997,27(2):180.
[10] 顧鑫,丁俊杰,楊曉賀,等.2008~2009年黑龍江省大豆灰斑病生理小種的監測[J].大豆科學,2010,29(3):540-542.
[11] 馬淑梅.2006~2010年黑龍江省大豆灰斑病菌生理小種監測及部分主栽品種抗性鑒定[J].大豆科學,2011,30(3):450-454.
[12] 丁俊杰,顧鑫,楊曉賀,等.黑龍江省大豆灰斑病菌生理小種及遺傳關系分析[J].中國農業科學,2012,45(21):4377-4387.
[13] PHAM A T,HARRIS D K,BUCK J,et al.Fine mapp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andidate genes that control resistance toCercosporasojinaK.Hara in two soybean germplasm accessions[J].PLoS ONE,2015,10(5):126753.
[14] MIAN M A R,MISSAOUI A M,WALKER D R,et al.Frogeye leaf spot of soybean:A review and proposed race designations for isolates ofCercosporasojinaHara[J].Crop science,2008,48(1):14-24.
[15] SCANDIANI M,FERRI M,FERRARI B,et al.First report of races 11 and 12 ofCercosporasojina, the causal agent of soybean frogeye leaf spot,in Argentina[J].Plant disease,2012,96(7):1067.
[16] 張俊華,張明,韓英鵬,等.大豆灰斑病菌生理小種PCR-RFLP分子檢測[J].中國油料作物學報,2010,32(1):128-131.
[17] 孫洪利,張俊華,韓英鵬,等.黑龍江省大豆灰斑病菌遺傳多樣性[J].中國油料作物學報,2011,33(1):57-61.
[18] 丁俊杰,姜翠蘭,顧鑫,等.利用與大豆灰斑病抗性基因連鎖的SSR標記構建大豆品種(系)的分子身份證[J].作物學報,2012,38(12):2206-2216.
[19] BRADLEY C A,WOOD A,ZHANG G R,et al.Genetic diversity ofCercosporasojinarevealed by 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markers[J].Canadian journal of plant pathology,2012,34(3):410-416.
[20] ZHANG G R,NEWMAN M A,BRADLEY C A.First report of the soybean frogeye leaf spot fungus (Cercosporasojina) resistant to quinone outside inhibitor fungicides in North America[J].Plant disease,2012,96(5):767-767.
[21] ZENG F,ARNAO E,ZHANG G,et al.Characterization of quinone outside inhibitor fungicide resistance inCercosporasojinaand development of diagnostic tools for its identification[J].Plant disease,2015,99(4):544-550.
[22] 劉學敏,李本寧.大豆灰斑病流行動態預測[J].大豆科學,1996,15(3):222-227.
[23] 丁俊杰.三江平原地區降水量變化與大豆灰斑病相關性分析[J].東北農業大學學報,2013,44(7):1-5.
[24] 劉惕若,李海燕,甄鴻杰.大豆灰斑病流行強度預測模型研究[J].中國油料作物學報,2006,27(3):54-57.
[25] 顧鑫,楊國珍,丁俊杰,等.黑龍江省東部地區大豆灰斑病短期預測模型的建立[J].黑龍江農業科學,2014(12):67-69.
[26] MENGISTU A,KELLY H M,BELLALOUI N,et al.Tillage,fungicide,and cultivar effects on frogeye leaf spot severity and yield in soybean[J].Plant disease,2014,98(11):1476-1484.
[27] 方中達.中國農業植物病害[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6.
[28] 曹越平,楊慶凱.大豆灰斑病抗感標準劃分的研究[J].大豆科學,2002,21(2):113-116.
[29] SHARMA H,LIGHTFOOT D A.Quantitative trait loci underlying partial resistance toCercosporasojinarace 2 detected in soybean seedlings in green-house assays[J].Atlas journal of biology,2014,3(1):175-182.
[30] 陳慶山.大豆灰斑病種質資源遺傳多樣性的RAPD和SSR分析[D].哈爾濱:東北農業大學,2001.
[31] 萬學臣.大豆灰斑病抗源篩選及其與若干性狀的關系[J].作物品種資源,1987(2):9.
[32] 姚振純,張玉華.野生大豆田間感染大豆灰斑病簡報[J].大豆科學,1986,5(4):349-350.
[33] 張文慧,杜吉到,陳慶山,等.抗大豆灰斑病育種研究進展[J].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學報,2006,18(1):22-26.
[34] 馬淑梅,韓新華,邵紅濤.大豆主要病害多抗性資源篩選鑒定[J].中國農學通報,2014(27):12.
[35] MENGISTU A,BOND J,MIAN R,et al.Resistance to frogeye leafspot in selected soybean accessions in MG I through MG VI[J].Plant health progress,2012,10.doi:10.1094/PHP-2012-0521-02-RS.
[36] YANG W,WEAVER D B.Resistance to frogeye leaf spot in maturity groups VI and VII of soybean germplasm[J].Crop science,2001,41(2):549-552.
[37] 朱希敏,王利財,鄒桂珍.大豆品種資源抗大豆花葉病 (SMV),灰斑病 (Cercosporasojina) 和霜霉病 (Peronosporamanschurica) 的鑒定和評價[J].大豆科學,1988(3):9.
[38] 張麗娟,楊慶凱.大豆抗灰斑病菌多個生理小種資源的篩選[J].大豆科學,1997,16(1):38-41.
[39] 吳秀紅.大豆抗灰斑病菌多個生理小種資源的篩選[J].植物遺傳資源學報,2003,4(4):341-344.
[40] 馬淑梅,李寶英.黑龍江省大豆品種和資源與本省大豆斑病菌相互作用的研究[J].大豆科學,1996,15(4):322-325.
[41] 馬淑梅.大豆種質資源對灰斑病抗性鑒定評價[J].植物遺傳資源學報,2011,12(5):820-824.
[42]馬淑梅,韓新華.大豆品種資源對灰斑病的抗性鑒定[J].大豆科學,2014(6):957-960.
[43]馬淑梅,韓新華,邵紅濤.大豆主要病害多抗性資源篩選鑒定[J].中國農學通報,2014,30(27):58-65.
[44]丁俊杰,顧鑫,楊曉賀,等.黑龍江省大豆新品系抗灰斑病鑒定[J].東北農業大學學報,2011,42(10):120-124.
[45]CHAWLAS,BOWENCR,SLAMINKOTL,etal.Apublicprogramtoevaluatecommercialsoybeancultivarsforpathogenandpestresistance[J].Plantdisease,2013,97(5):568-578.
[46]劉忠堂.抗灰斑病大豆育種技術的探討[J].大豆科學,1986,5(2):147-152.
[47]齊寧,郭泰,劉忠堂,等.高抗灰斑病高產大豆新品種合豐34號的選育[J].中國油料,1994,16(4):65-66.
[48]郭泰,劉忠堂,齊寧,等.大豆高抗灰斑病品種合豐29號的選育及利用[J].作物品種資源,1997(3):25-26.
[49]劉成貴,劉秀芝,鄭偉,等.抗灰斑病高油高產大豆新品種合農64選育與推廣[J].黑龍江農業科學,2015(3):1-4.
[50]劉秀芝,劉成貴,王志新,等.早熟高產優質抗病大豆新品種合農59選育與推廣[J].黑龍江農業科學,2015(2):1-5.
[51]顧鑫,丁俊杰.大豆灰斑病的研究現狀[J].中國農學通報,2010,26(9):303-306.
[52]鄒繼軍,楊慶凱.大豆灰斑病抗病基因RAPD標記的分子特征及抗,感種質的SCAR標記鑒定[J].科學通報,1999,44(23):2544-2550.
[53]張文慧,陳慶山,楊慶凱,等.大豆灰斑病1號生理小種抗性基因的SSR標記分析[J].大豆科學,2004,23(3):169-173.
[54]陳立君,郭強,劉迎雪,等.大豆灰斑病1號生理小種抗性基因的SSR標記[J].中國農學通報,2009,25(9):43-46.
[55]DONGZ,WANGS,LIUJ,etal.PreliminarymappingofsoybeandominantlocusHrcs7conferringresistancetoCercospora sojinarace7[J].Molecularplantbreeding,2011,2(6):37-40.
[56]姜翠蘭,丁俊杰,文景芝,等.大豆對灰斑病菌 15 號小種的抗病基因定位及標記檢測[J].植物保護學報,2011,38(2):116-120.
[57]MIANMA,WANGT,PHILLIPSDV.MolecularmappingoftheRcs3geneforresistancetofrogeyeleafspotinsoybean[J].Cropscience,1999,39(6):1687-1691.
[58]MISSAOUIAM,HABK,PHILLIPSDV,etal.SinglenucleotidepolymorphismdetectionoftheRcs3geneforresistancetofrogeyeleafspotinsoybean[J].Cropscience,2007,47(4):1681-1690.
中圖分類號S435.6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17-6611(2015)30-22-04
基金項目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項目(2012AA101106);長江學者和創新團隊發展計劃項目(PCSIRT13073);江蘇省現代作物生產協同創新中心項目(JCIC-MCP)。
作者簡介程偉(1988-),男,安徽亳州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大豆遺傳育種。*通訊作者,助教,碩士,從事大豆遺傳育種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10
Advance in the Disease Occurrence and Resistance Breeding of Frogeye Leaf Spot in Soybean
CHENG Wei, CHANG Fang-guo, ZHAO Tuan-jie,KONG Jie-jie*(Soybe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tional Center for Soybean Improvement/ Key Laboratory of Soybean Biology and Genetic Improvemen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National Key Laboratory for Crop Genetics and Germplasm Enhancement, Nanjing, Jiangsu 210095)
AbstractFrom the viewpoint of resistance breeding, some aspects including the pathogen’s characteristics, its physiological race differential and classification, the disease epidemiology and its control, identification methods for resistance and screening of elite resistant germplasm (genes), genetic improvement for resistance to frogeye leaf spot were reviewed. Some discussions involve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disease occurrence, race identification system, discovery of elite resistant lines (genes) and combination of convention and molecular breeding for resistance to frogeye leaf spot.
Key wordsSoybean; Frogeye leaf spot; Race differentiation; Resistance breeding; Molecular mar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