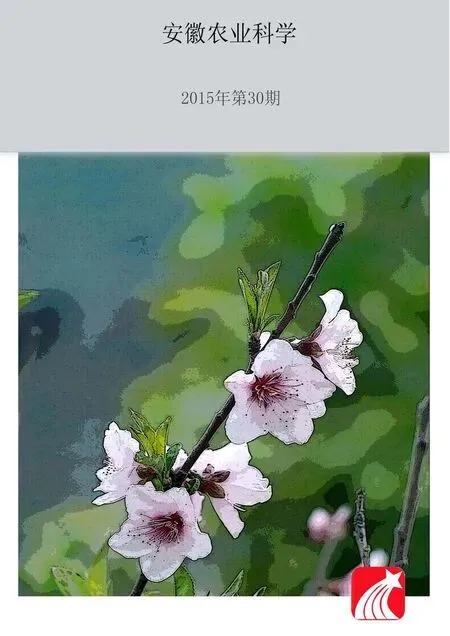園林植物應用的基本單位研究
——景觀單元
吳劉萍
(廣東海洋大學園林系,廣東湛江 524088)
園林植物應用的基本單位研究
——景觀單元
吳劉萍
(廣東海洋大學園林系,廣東湛江 524088)
摘要通過分析園林植物應用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理論與實踐需求等現實問題,依據學科的內在特征和客觀實踐需求,探尋園林植物應用的基本單位。筆者提出并深化景觀單元概念,基于“質-核假說”,構建以“植-境”為核,“生態-美學”為質的景觀單元理論框架,提出適地適樹、胞質干擾、邊界交流等內在機制和基于原型與變型、生長與組織等的模式語言、景觀圖譜等外形表達。
關鍵詞景觀單元;“質-核”模型;模式語言; 園林植物應用
2011年教育部學科調整后,風景園林學成為一級學科,和建筑學、城市規劃學一起共同組成完整的人居環境科學體系。然而,風景園林學的知識主體涉及植物、生態、社會文化、工程、藝術等各個方面,與生俱來的綜合性和邊緣性使其處于復雜的巨系統的各學科理論之中,自身學科處于削弱和離散狀態,各學科知識不能有機融合[1],理論體系落后于實踐需求。園林植物應用為風景園林學研究的六大內容之一,承繼風景園林學的交叉性學科本質,其理論體系也處于離散中,要想穩健地構建園林植物應用的系統理論和搭建其自身學科體系,首要在于探尋構建學科的基石,以及園林植物應用的基本單位。
1離散
發展中的園林植物應用學科以植物景觀營造為核心,包括植物多樣性保護與規劃、城市綠地植物規劃、園林植物配置、園林植物資源認識、栽培和養護等核心內容,各內容環環相扣、層級遞進,并以植物配置為紐帶,與風景園林學科相連接,融入規劃、設計、工程、美學、生態等各方面。然而,現狀缺少植物景觀營造理論[2];或以材料代替要素,主要以植物個體為研究對象,突出園林植物個體的形、色、姿、韻[3];或摒棄形狀和尺度,借鑒植物群落概念,采用大尺度林業的樣方研究方法。
1.1研究對象和方法的離散由于植物本身的綜合性、普適性和主體性,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特別是在以人文美學為主要功能的傳統園林階段,園林植物應用學科的主要研究對象以植物物種為基礎,細致到科、屬、種等分類特征、生態習性、栽培要點等,特別突出園林植物個體的形、色、姿、韻。無疑,園林植物是園林植物景觀的主體要素和材料:①因其自身固有的形態、色彩、姿態、質感,是最具表現力的景觀材料;②不同植物種類與其后期表現、養護管理密切相關;③植物分類學有著深厚的基礎,植物物種選擇脫胎其中,自然產生路徑依賴;④在自然人化的過程中,花語、花文化等植物象征意義也以物種的形式出現,且深入民心。然而,植物物種卻難以真正解答園林植物應用的關鍵核心,如小葉榕,可以是獨木成林,做街旁行道樹、辦公樓前剪形的柱狀體,也可以是一個盆景樹樁,雖為同一物種,就如同一個“字”,在不同的場(語)境中,其生態意義、美學意義差距甚遠,這個“字”不具有獨立的生態意義、美學意義,不足以于說明“人與自然”的關系。
隨著學科的發展,特別是城市生態需求的發展,承續植物生態學理論,借鑒自然植物群落概念,園林植物群落演變為研究的基本單位和研究熱點[4-5]。①園林植物群落以科學的方式整體呈現種類、結構、層次和外貌,與自然植物群落可形成對接;②依據群落層次劃分的“喬、灌、草”或“喬、灌”或“喬、草”等類型,較為直觀地反映了園林植物應用的模式類型及生態效益;③反映植物物種種間關系,一定意義上反映了人們的審美意識,體現了人工干擾強度。較之園林植物個體“字”而言,園林植物群落具有“詞”的意義,有了詞性、詞義,但同為3 m×3 m矩陣排列的9株“大王椰-臺灣草”群落,處于平坦的草地、緩緩的草坡、點陣式的水面、開闊的廣場,不同的“境”產生迥異的美學觀感和生態意象,僅關注植物組團及物種間的關系也難以表達完整的生態、美學意義,“境”與植物必須統一為“植-境”體,才可切入風景園林學科本體。楊銳在《論“境”與“境其地”》一文中指出,“境”為風景園林的核心范疇之一,擁有空間、時間和人的三重復合字義結構。此處的“境”更偏向于由物而起的“生境”的涵義,亦指棲息地,但又隱含有由心而得的畫境、情境、意境等“非物境”的涵義。
依然以上述“大王椰-臺灣草”群落為例,假設一:不再以矩陣的方式出現,而將與外界聯系的邊界轉化為折線、流暢的曲線或自然的曲折線,即使同處于廣場之境,表達的生態、美學意義亦不相同;假設二:同為矩陣形態,群落生長擴大,7株、9株、15株的大王椰,處于同一樹叢尺度級別,其生態、美學意義具有相似性;當其轉化為不同等級尺度的樹叢、樹群、樹林時,生態、美學意義便產生了質的區別,表現為尺度差異。邊界抽象為線形,承載了設計風格及手法,承載了人類的集體審美意識,也是如何發揮生態效益的主要思考途徑之一[6];尺度是園林植物應用的另一關鍵詞[7],園林植物應用存在尺度差異,這反映了“人與自然”交流的方式,也是生態過程、人文過程的景觀體現。大尺度自然植物群落以“樣方”法為植物層次結構的常規研究法,與其不同,園林植物應用更加關注植物景觀功能和規劃設計應用的對接,若去除尺度差異、形狀差異,忽視邊界形狀意義、群落尺度意義,也就偏離了學科的本質特征,以“樣方”法為基礎進行的園林植物景觀評價也就缺乏科學性。
1.2理論與實踐應用的離散園林植物是確保城市生態質量的主要對象,占據人居環境最大的數量和空間。城市是人居環境的主要載體,擁有獨特、混雜和受干擾的棲息地。面對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城市被稱為生物多樣性的熱點和熔點[8]。然而,當前城市綠化面臨著城市生物多樣性銳減[9]、綠地自我維持力不足[10]、風景地域性特色缺乏[11]等重大問題。一方面,忽視城市原自然植被,城市植物群落自然性、生態化不足[12-14],鄉土植物不足,地方風格缺乏[11],而觀賞型植物造景、裝飾性植栽背后可能是生態破壞性建設、養護費用高、植物景觀不可持續[15-16]等系列問題。另一方面,理論界倡導的“自然主義”風格的植物群落形成“雜亂的視覺”[17],“排外來樹種”與“唯鄉土植物”[18]等理論在實踐中也受到人們質疑。這反映了理論與實踐應用的離散,人們對城市綠化語言體系的認識不足,生態性詞匯缺失,“自然主義”詞匯應用不當等。正如一個人語言能力的高低在于是否掌握豐富的詞匯量,掌握其詞性、詞義,在一定的語境下能否巧妙得體地選詞造句,只有正確理解園林植物應用的詞量、詞性、詞義,掌握其構成和發展規律,才能寫出切題而精彩的城市綠化文章。
模擬自然一直是風景園林實踐的重要手段[19],熱帶園林植物群落就是運用園林植物模擬熱帶自然植被類型營造的人工群落[20]。然而,對自然的模擬是神似抑或形似,隱含著生態式設計、寫意式設計或規則式設計等手法差異。以熱帶雨林型植物景觀為例,在模擬自然的過程中,相同的修飾詞表達相似的目標,同一設計原型生長變化成多樣的變型。然而,如何模擬,形成的原型如何分類、生長、變型,這也是園林植物應用實踐中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2探尋
基本單位是客觀存在的,具有獨立結構和功能的單元體,是構建學科體系的基石,是有機融合學科內外關系的切入點和紐帶,是理論與實踐的共性需求。正如上文提到的“詞”一樣,其由語素構成,是最小的語法單位,能獨立充當句子成分,成為構筑語言系統的基石,是不同語言、不同文化轉譯交流的切入點。對于生物學而言,細胞為生物體的基本單位,細胞的認識發現使人們認識到各種生物之間存在共同的結構基礎,向上分類層進至組織、器官到生物體,并推進生物學研究以細胞為單位的更微觀的分子水平,成為生物學的基石。盡管形式、尺度、內容各異,“細胞、詞”均是客觀存在的、具有獨立結構和功能的單元體,具有基本單位的共性:客觀性、完整性和功能性。
在探尋園林植物應用學科的基本單位之路上,學者們提出了各自見解。李敏在研究園林植物配置與造景特色時提出景觀單元概念,指其為園林生態系統里具有一定穩定性和完整性的綜合體[21];李樹華提出種植設計單元是園林種植設計中的基本單位,是植物景觀營造過程中的最小組成部分,并按功能性劃分為7類植物景觀類型[22];嚴玲璋提出以植物群落為基本單位的設計思想[5],楊學軍進一步提出“群落單位”,指出可根據基質的性質、地形、土壤類型與土壤性質、功能分區、園路等自然與人工設計要素,進行空間單元的區劃,形成園林植物配置理論[4]。
在前人的基礎上,依據學科的內在特征和客觀實踐需求,筆者進行了園林植物應用學科基本單位的探尋。
2.1設計語匯與景觀意象世界園林的發展史也是園林植物應用基本語匯系統的發展史,具有顯著特征的模式語言成為園林風格和流派的主要標志。如“松石圖”、“牡丹臺”、“桃花澗”、“竹徑”、“梅溪”等,這種“植-境”相結合的景觀單元形式已成為中國傳統園林實踐中的模式語言,形成具寫意型圖式的語言原型,進而上升為一種具有集體審美意識的景觀意象,反映了中國傳統園林的營造規律和人文美學追求。風景園林不同時期、風格、流派的模式語言在美學維度和生態維度上不斷創新,形成了豐富多樣的設計語匯。如:從法國古典主義園林典型的林蔭道語匯到現代結構主義的雙排綠籬、林蔭道(丹·凱利,米勒莊園),到極簡主義的面包圈及植栽(瑪莎·施瓦茨,面包圈公園);從自然風景園中與起伏草地相隨出現的自然樹叢、孤植大樹等,到起伏花海、白樺樹叢演繹出的新托斯卡納風格;從布雷·馬克斯結合現代抽象藝術創新出的抽象流暢、色彩鮮艷的南美熱帶植物景觀語言,到“自然主義”風格引入野生花卉、鄉土植物的金斯伯瑞“新多年生植物景觀”等。上述設計語匯處于“美學-生態”維度的不同點位,為各自景觀意象的典型代表,是客觀的、完整的和具有功能性的園林植物應用的景觀單元。
2.2適地適樹與“植-境”單元論風景園林的實踐規律,“適地適樹”是植物在城市生境中健康成長的前提,“山以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發,以煙云為神彩”(郭熙《林泉高致》),唯地得草木而華、草木得地而發。“適地適樹”不僅是“樹與地”的關系,圍繞著“樹與地”的適宜性,潘劍彬進一步解析“適地適樹”的地區氣候條件、場地基址條件、人的功能需求的綜合、多目標協調和適宜[23]。“植-境”單元體不僅反映“植物與植物之間”、“植物與場地之間”的內在適宜關系,還包涵著人類的選擇。以河岸泥灘之境為例解析“植-境”單元體:①泥灘之境其植物景觀類型可以是美人蕉或是梭魚草,不同植物物種體現類似的美學情感,物種之間存在著可模擬性和可替換性;②當植物物種轉化為茳草、紅茅草、旱傘草或海芋之類,或黃槿、大葉榕時,同境營造出多樣的單元體,顯示為不同的景觀美感類型和生態類型,這是人類在“美學-生態”不同維度上的選擇;③倘若河岸泥灘之境的關鍵生態因素發生變化,如淡水轉化為咸淡水,則植物景觀類型定有顯著差異,或轉化為鹵蕨、草海桐,不同境,其“植-境”單元類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④以上述的海芋為例,又可適于泥灘之境,林下之境,或小區建筑角隅之境,同植物物種配置不同的境表現出不同的生態氣場。從而,真正發揮“生態-美學”效益的不是植物物種單方面,而是植物與境之間的協同性。“植-境”相互協調,才可能有良好的植物景觀。基于“適地適樹”,深入“植-境”單元綜合研究,并以此為核心,才可理解和發揮園林植物應用的“生態-美學”綜合機能。
2.3“質-核”模型與景觀單元在人居環境科學體系框架內,園林植物應用的價值標的處于純自然的生態和純人工的美學之間,其價值取向表達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美學”的綜合追求,城市綠化語言受“生態-美學”雙向維度的影響。H?GZüNER H采用開放式問卷調查方法,調查研究專業人員、政府管理人員、生態環保人員及普通市民等不同層次人員對待生態與美學的態度,并指出大部分人認可“生態型”語言和“美學型”語言在城市中協調共存[24-25]。Dunnet, N.借鑒Grime 的C-S-R三角模型[26],比較城市中自然植被、園藝植被和人工植被三者的關系,建立資源-美學-生態之間的三角模型,提出園林植物應用維度趨勢取決于管理資源方便可得性、公眾對野生植被的可接受態度、自然保護的相關重要性,進而提出創新的保護性景觀[13]。這些研究從城市綠化的層面指出“生態-美學”協調的重要性,城市綠化層面需要“生態-美學”共存的語言體系。“植-境”體既遵循自然規律,又融入人的意志,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內在機制,又有反映人類干擾強度的外型表達。當詞義基本明確后,“植-境”體的詞性定義標尺取決于人工干擾強度。當美學維度向量強勁時,視覺美、意韻美的機能放大,極端例子如剪型植景、造型盆景;當生態維度向量強勁時,人工干預弱化、自我維持力增強,生態機能放大、自我演替,轉化為純自然美,極端例子如自然保護區中的原生植物群落。
無論是視覺感受還是生態效應,邊界形狀、尺度差異反映了人的意志,體現了關于人文的設計風格及手法、空間的形態及組合、景觀異質及生態效益,“植-境”體與外界的交流具有邊緣效應。吳慶書從設計過程探討了邊界的意義[6],孫鳳云則以林緣面的形式評估了邊界對游賞體驗的影響[27]。當一個或多個“植-境”體組合構成植物空間時,邊界也就成為空間模式、空間形態的關鍵要素;另一方面,不同于建筑空間“實與虛”的絕對性,一定尺度和形狀的“植-境”體本身就有空間的意義。李雄在研究植物空間構成時,就提出過邊界的拓撲關系、圖底互鎖關系等模式[3];從而,邊界形狀抽象為林緣線,具有“格式塔”意義,形狀指數(是吳仁武、包志毅在研究杭州太子灣公園植物空間時提出的一指標值,形狀指數數值越大,空間形狀變化越豐富,并指出曲折的林緣線是豐富空間形態變化的途徑)反映了空間的豐富度及與外界交流時“自然-人文”的交流度。形狀、尺度是設計風格、生態交流等內在涵義的外在表達,整體或模糊性地表達了“植-境”體的語言詞性,是與風景園林規劃設計對接的關鍵要素。
綜合內在機制和外形表達,借鑒細胞學說,筆者提出“質-核”假說。以適地適樹為原則的“植-境”體為核,以反映人工干擾強度的“生態-美學”為質,以與外界進行“自然-人文”交流的圍合邊界為“細胞膜”,核為本,質為標,膜為表型要素,構成“核心-胞質-邊界”三層模式結構、具有獨立結構和功能的“質-核”模型。
由此,園林植物應用基本單位的探尋,從設計語匯、景觀意象、“植-境”單元到“質-核”模型,作為基本單位的“細胞”呼之欲出。基于風景園林學的本質和園林植物應用學的特征,筆者延續景觀單元稱謂園林植物應用的基本單位,并深化其概念內涵。景觀單元(Landscape Cell):是城市綠化中客觀存在的,由一定邊界圍合,受人文和自然影響,由“植-境”為核、“生態-美學”為質共同構成的具有獨立結構和功能、發揮景觀和生態效益的單元體。
3解析
3.1基本構成景觀單元“質-核”模型基本構成包括“核心-胞質-邊界”三層,三層整體不可分割,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達。①核心層:以“植-境”的適宜度為研究內容,重點解析適地適樹規律及植物層次構成規律;②胞質層:以“生態-美學”的干擾度為研究內容,研究干擾因素及干擾力,在“植-境”健康的前提下,解析設計過程是基于生態思維的美學設計,還是基于美學思維的生態性設計,語匯體系中是生態性詞匯還是美學性詞匯。③邊界層:以“形狀-尺度”的交流度為研究內容,研究邊緣的美學-生態意義,邊緣效應的形狀-尺度差異,線型的風格意義、形狀的空間意義、相鄰單元的組合關系(表1)。
3.2外形表達景觀單元“質-核”模型內在機制為適地適樹、胞質干擾、邊界交流,外形表達有賴于“植”、“境”兩大類物質要素:“喬-灌-草-藤”、“地形、水體、園道、園建”等。“植-境”體的物質性,以形、色、質反映其組織方式、構成規律,再抽象為點、線、面,細分為“邊緣-結構-裝飾”等功能,非物質性的審美情趣、文化意義等蘊涵于去物質特性的點、線、面之中。
3.2.1類別與原型。依據胞質干擾度,景觀單元劃分為生態、美學兩大類別,外形表達上也存在顯著差異,生態類別景觀單元重質輕形,美學類別景觀單元重形輕質,依質感、形態差異劃分出不同的景觀單元基本原型,構成其模式語言,通過不同色彩的點、線、面繪制成景觀單元二維形態圖譜及三維空間圖譜。

表1 景觀單元基本構成
3.2.2生長與變型。生長的含義一方面是指景觀單元設計過程中尺度的范圍性,基本原型在一定尺度范圍內,具體尺寸可變;另一方面是指設計后過程中構成要素植物本身的生長特性,表達為四維季相圖譜或年齡演化圖譜;變型相對于基本原型而言,一方面指園林植物應用時物種的彈性選擇,相似形態、色彩、質感的植物材料具可替換性,如水杉、落羽杉、池杉;另一方面對應生長的尺度范圍、年齡階段范圍,不同的變型構成基本模式語言的擴展集。
3.2.3組合與空間。基于植物材料的固有特性,單元體構成具有“虛-實”之別,如“喬-草”結構為“虛”、“喬-灌-草”結構為“實”。當其構成“實”時,景觀單元依據組合構成另一或“曠”或“奧”的空間,邊界邊緣外向效應明顯;當其構成“虛”時,單元體自身構成開敞空間、覆蓋空間、垂直空間等,邊界邊緣內向效應明顯,通過進一步的組合形成或“曠”或“奧”的空間,邊緣效應雙向交流。
4意義
景觀單元的提出對園林植物應用學科體系的構建具有理論與實踐意義,相對應于生物學、語言學的“細胞、詞”,是構建園林植物應用學科的穩健基石。
4.1學科體系的串聯與切入景觀單元串聯起植物材料、植物物種選擇、植物群落-生境組合、植物景觀空間營造、植物總體風貌及城市生物多樣性等園林植物應用核心內容,并以紐帶的形式與風景園林學科相連接,融入規劃、設計、工程、美學、生態等各方面。
4.2反映學科的本質特征園林植物應用的本質是研究“人與自然”關系的人居環境學科,通過適宜度、干擾度、交流度的量化可深入探討植物與植物之間、植物與生境之間、單元體與人之間、單元體與單元體之間的關系,反映了自然的客觀規律和人的主觀意識,有助于學科的發展。其類別的劃分、原型及變型、生長及組合的特性,為不同性質、不同功能、不同場境、不同景觀目標提供了適宜的語匯,利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4.3反映學科的典型特征“質-核”模型涉及生態適應性選擇、感官愉悅性選擇(特別是視覺性之色、香、形、姿)及社會文化性選擇(韻),將物質要素形態、線條、色彩、質感等材料特性轉化為點、線、面抽象形式,是設計者設計思維的著力點。景觀單元是最小的設計組合單元,也是工程施工組織單元、養護管理單元、游覽欣賞單元,從而是園林植物應用不同階段的研究基本單位,是發揮生態效益、美學效益、社會效益的基本單位。
參考文獻
[1] 張啟翔.關于風景園林一級學科建設的思考[J].中國園林,2011,27(5):16-17.
[2] 李樹華.基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植物景觀營造理論體系構建:基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風景園林設計論研究(二)[J].中國園林,2011,27(7):51-56.
[3] 李雄.園林植物景觀的空間意象與結構解析研究[D].北京:北京林業大學,2006.
[4] 楊學軍,唐東芹.園林植物群落及其設計有關問題探討[J].中國園林,2011,27(2):97-100.
[5] 嚴玲璋.略論21世紀上海城市綠化的可持續發展[J].中國園林,1998,14(2):44-46.
[6] 吳慶書.熱帶園林植物景觀設計[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9.
[7] 陳嵐. 城市公園植物景觀設計中的尺度探析[D].重慶:西南農業大學,2010.
[8] MULLER N.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biodiversity Curitiba. Cities and Biodiversity: Achieving the 2010 Biodiversity Target[Z]. 2007:26-28.
[9] 杰克·埃亨,周嘯.生物多樣性給風景園林師帶來的挑戰和機遇[J].風景園林,2011,27(3):140-145.
[10] 黃金玲.近自然思想與城市綠地系統規劃[J].城市問題,2009(9):11-14.
[11] 孫衛邦.鄉土植物與現代城市園林景觀建設[J].中國園林,2003,19(4):56-57.
[12] DUNNET N,CLAYDEN A.Resources: The raw materials of landscape[M]//BENSON J,ROE M.Landscape and sustainability. London:E & F.N. Spon,2000:179-201.
[13] DUNNET N,HITCHMOUGH J D.The dynamic landscape, design, ecology and management of naturalistic urban planting[M]. Spon, London,2004.
[14] ZERBE S,MAURER U,SCHMITZ S,et al.Biodiversity in Berlin and its potenti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3,62:139-148.
[15] 俞孔堅.大腳美學與低碳設計[J].園林,2011,27(10):18-21.
[16] MAURER U,PESCHEL T,SCHMITTZ S. The flora of selected urban land-use types in Berlin and Potsdam with regard to nature conservation in citi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0,46:209-215.
[17] NASSAUER J I.Messy ecosystems, orderly frames[J]. Landsc J,1995,14(2):161-170.
[18] HITCHMOUGH J.Exotic plants and plantings in the sustainable, designed urban landscap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1,100(4):380-382.
[19] 任斌斌,李樹華.模擬延安地區自然植物群落的植物景觀設計[J].中國園林,2010,26(5):87-90.
[20] 吳劉萍,李敏.論熱帶園林植物群落規劃及其在湛江的實踐[J].廣東園林,2005,29(3):6-10.
[21] 李敏,謝良生.深圳園林植物配置與造景特色[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7.
[22] 李樹華.園林植物種植單元的概念及其應用[C]//中國風景園林學會.中國風景園林學會2011年會論文集.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1:888-891.
[23] 潘劍彬,李樹華.基于風景園林植物景觀規劃設計的適地適樹理論新解[J].中國園林,2013,29(4):5-7.
[24]H?GZüNER H, KENDLE A D.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naturalistic versus designed landscapes in the city of Sheffield (UK)[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6,74:139-157.
[25] H?ZüNER H,KENDLE A D,BISGROVE R J. Attitudes of landscape professionals towards naturalistic versus formal urban landscapes in the UK[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7,81:34-45.
[26] WILSON J B,LEE W G.C-S-R triangle theory: Community-level predictions, tests, evaluation of criticisms, and relation to other theories[J]. OIKOS, 2000,91(1):77-96.
[27] 孫鳳云,李俊英,史萌,等.城市公園林緣景觀美學質量評價[J].沈陽農業大學學報,2010,41(6):736-739.
中圖分類號S68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17-6611(2015)30-145-04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51208118)。
作者簡介吳劉萍(1972- ),女,江西萍鄉人,在讀博士,副教授,高級工程師,從事園林植物應用、景觀設計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14
The Research on the Basic Unit of the Landscape Plants Application—Landscape Cell
WU Liu-ping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88 )
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research objects and methods, theory and practice demand of landscape plants application discipline, according to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objective practice demand of the discipline, the basic unit of the landscape plants application was explored. This paper put forward and deepen the concepts of the landscape cell, construct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landscape cell, based on the “cytoplasm- nuclear hypothesis”, as "plant-habitat" for nuclear and "ecological-aesthetics" for cytoplasm, then put forward to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s “Matching species with the site" (MSS), cytoplasm interference, border exchanges and the appearance expression as mode language and graphics mode, based on the prototype and variant, growth and organization etc of the landscape cell.
Key wordsLandscape cell; “cytoplasm-nuclear” model; Mode language; Landscape plants 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