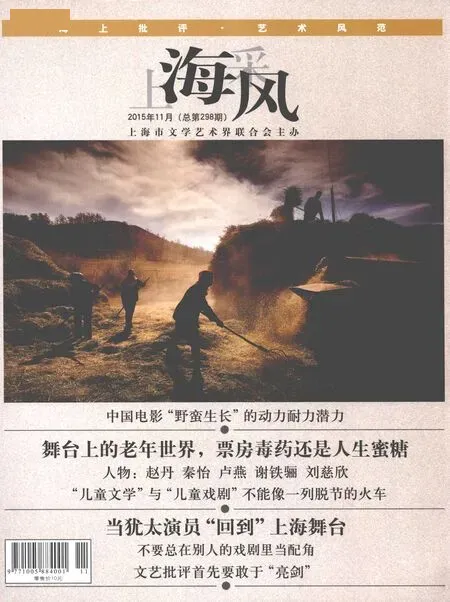“標準語”的口音
文/柯 玲
“標準語”的口音
文/柯 玲
什么是標準語?我們漢語的標準語即普通話,英語標準語是什么呢?國人比較認可的是英式和美式英語。現在出國求學的人越來越多,英語是第一道坎兒,不少人擔心自己的發音不夠標準,包括很多英語統考高分者出國后還是常常不愿多說或不敢多說。在我看來,牛津英語毫無疑問是標準語。《牛津英語詞典》被認為是全球最全面和最權威的英語詞典,被奉為英語世界的金科玉律。然而,在牛津大學老師們的眼中,牛津英語不過是一種“口音”而已。在語言中心的高級英語口語課上,喬治惟妙惟肖地給大家播放、對比了英國不同區域口音的區別,于是,我聽到了牛津口音、倫敦口音、威爾士口音、蘇格蘭口音等等。作為老牛津人,喬治只是客觀呈現,未表現出絲毫優越感。仔細想來,其實任何一種語言都不過是特定區域的特定口音。
我們的普通話作為標準語,是漢族間以及不同民族間進行溝通交流的通用語言,以北京語音為基礎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但普通話在牛津很少被稱為“Chinese”,大多數人更喜歡用“Mandarin”,據說這種譯法來自葡萄牙語。普通話多為官方用語,也是聯合國的六種官方工作語言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使用普通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進一步明確了“國家通用語言”的法定地位。所以,普通話對特定人群來說是必須掌握的語言,比如主持人、教師、官方發言人等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推普運動盛行之時,記得我還寫過一篇叫《鄉音的隱退》的電視散文去省里參賽,還獲了個二等獎。說真的,那時真心覺得師范生不講普通話就是犯法!
推普運動已歷經半個多世紀,中國經濟飛躍發展,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國人的語言使用習慣實際上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00年全國語言調查的結果:與家人交談時18%的人用普通話;到集貿市場買東西,23%的人用普通話;到醫院看病及到政府機關辦事,普通話使用率分別是26%和29%;使用普通話最多的場合是在單位談論工作,高達42%。此外,全國能用普通話進行交際的人口約為53%。2010年國家語委又進行了一次“普通話普及情況調查”,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能用普通話溝通的人大概在70%左右,與10年前相比增加了近20%,方言使用情況則沒有發生變化。可見,對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來說,普通話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掌握,但它也還不是一種普通國人人人掌握的標準語言。
我的小學老師上課基本都用方言,僅有一位黃老師可以講普通話(黃老師也是唯一一位畢業于師范學校的科班出身的老師)。黃老師講普通話常常被人們開玩笑為“山東驢子學馬叫”。不只是黃老師,連普通話也常常成為一些民間笑話的素材。記得那時公社廣播里的天氣預報最后都會說一下“天氣趨勢”,這個“天氣趨勢”當時竟然沒幾個能聽懂的。大人們說“天氣噓噓”,孩子們說是“天氣蛐蛐”。孩子們每天聽著天氣蛐蛐,模仿著廣播里的標準音說話,然后大家相互指著說“山東驢子學馬叫”,然后莫名其妙地傻笑半天,一直笑到肚子疼。比較滑稽的是我們竟然覺得“鹽城話已經是很標準的普通話”,我們模仿得已經很標準了。事實上,我的高考試卷上看拼音寫漢字(那是高考語文的必考題)8分才得了2分。直到我上了師大中文系,知道了鹽城話與普通話在調值、音位、音長等等方面存在著諸多差異,自此才開始有意識地學講普通話。不過,講普通話在家鄉依然還是一個會引來異樣關注的現象。記得有一次寒假回家,下車時不小心說了句普通話,馬上有位大爺問:“姑娘你不是本地人啊?你打哪里來的啊?”竟然鬧了個面紅耳赤,感到幾分慚愧。馬上改口相告我是師范生在練習說普通話。大爺通情達理:“哦,將來當老師是得講好標準語。當老師好啊!”
家鄉人之間講普通話會有種怪怪的感覺,因為對特定區域來說,當地方言才是真正的當地“標準語”。從文化淵源來考察,方言與文化之間有著與生俱來的水乳交融關系,而普通話則是后天新生的、人為綁定的一種關系。尤其在非北方方言區,普通話與當地文化之間似乎總是一種懸置或游離的關系。正因為普通話與各地文化之間缺少這種先天的聯系,要求每個人都發標準音就有了難度。
至于英語,乃是中華民族共同語體系之外的語種,與漢語之間聯系十分薄弱。兒時農村英語師資嚴重缺乏,擅長精神勝利的同胞,理直氣壯地嚷著“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照做中國人!”20世紀80年代之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英語人才日顯重要,普教系統的英語教育開始強化。英語水平考試除了全球性的托福和雅思之外,我國還專設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針對出國留學人員的外語培訓,我國也有相應的過關考試,如PETS5等等。實際上,即便各類英語考試都通過了,不少人到了國外還是覺得實際語境中聽和說的交流依然存在困惑。剛到牛津時,開口說話總忘不了先打招呼“請原諒!我的英語不標準!” 一般聽者都會善意地安慰我“不,挺好的”。只有直率的麥琪,聽了直接反對:“凱瑟琳,別這樣說,我們不知道什么是標準英語。誰的英語標準?所有語言都是一種口音,因為各地水土不同,口音一定會有差別。”喬治的觀點與麥琪完全一致。為了說明英語口音的存在,喬治課堂上播放了幾個不同地方牛叫的聲音,所有人都聽得忍俊不禁:原來,牛也有口音,動物界也同樣存在方言,你能想象狗吠、雞鳴、猿啼的“方言”嗎?太神奇了!
由此看來,所謂的標準語其實總是相對于特定區域而言,或許將標準音理解成一個政治或行政概念可能更為妥帖。所以,世上很難有標準語,即便如英語,包括一切英聯邦國家在內的說英語的國家似乎都沒有規定過標準音。在英國本土,以前曾把受過教育的極少數倫敦人的口音看作“標準音”,即所謂RP(Received Pronunciation)口音,現在不同了,以英國廣播公司BBC為例,近年的播音員明顯帶有不同的區域口音。美國英語一般認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正式場合說的話就是標準英語。或許因為我們是個比較鐘愛標準的國度,我們的基礎英語教育中,不僅有所謂“英式發音”和“美式發音”,我們甚至還會用所謂的標準音去衡量外國人的英語。記得十年前剛接觸來華留學生時,覺得不同國家的留學生英語發音大相徑庭。印度英語、日韓英語,甚至美國英語都幾乎聽不懂。稍許能聽懂的似乎還是英國人說的英語,這可能跟我所接受的英語教育有關。但有意思的是,這種互相聽不懂的情況在來自不同國家、操著不同口音的留學生之間似乎并不存在。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之間英語交流流暢自如,完全沒有我們想象的困惑,我常常在一旁饒有興味地欣賞這些南腔北調的英語,就像聽中國同胞操著的南腔北調的彩色普通話一樣,雖然口音濃重但相互交流無礙。所以,如果說英語是目前全球最為通用的語言的話,那么,它也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口音的一種語言。
罕見的一個特例是德語標準語。德國境內的方言也是各種各樣的,從南到北按照地形的高低大致分為高、中、低三大塊。所謂的“標準德語”(Standard German),歷史語言學上稱之為“新高地德語”,它在十四五世紀作為一種綜合若干方言特征的書面語出現,當時主要用于行政的管理。它隨著宗教、印刷品的傳播和城市化、工業化的進展而得到普及,但在19世紀之前它沒有口語形式,直到20世紀中才成為一部分人的第一語言。所以,有學者認為“標準德語”就是一個500年“沒有母語者的語言”,分析“標準德語”語料時應該將它與其他方言材料區別對待。語料分析是語言學家的事情,與民眾無關。我比較好奇的是與漢語普通話不同,“標準德語”的普及竟然是德國民眾的一種自發行為,政府沒有采取任何行政手段。德意志民族的邏輯、思辨傳統亦為世上罕見,莫非正因其民族超強的邏輯思維基因,使得在德國推行“標準”較為易行,甚至變成了一種內驅力?建立在德國“標準”文化根基上的標準德語較為便捷、自然地融入了德國文化之中。事實上,德國的“標準”文化遠不僅僅表現在語言方面,在生產、生活、技術等各方面都可以顯而易見地看到這種標準。
口音的存在源自方言的影響,方言是區域文化的表征。口音作為一種活態的文化化石會以各種形式從語言、發音中流露出來。標準語的口音其實正是特定區域文化在語言中保留的區域文化“我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