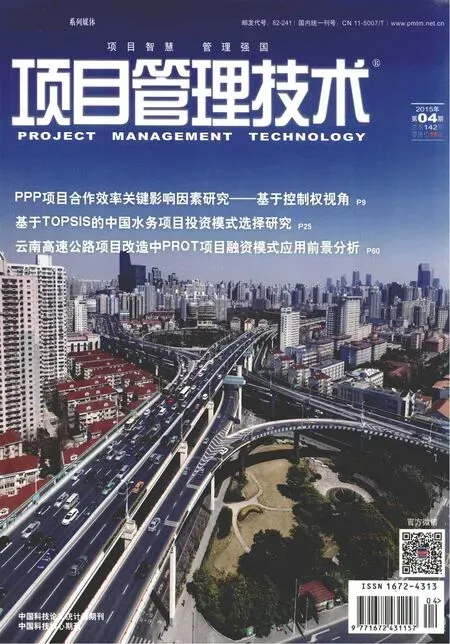基于監管主體與客體間博弈的流域水體污染治理項目研究*
張穎
(河海大學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0)
0 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及經濟結構調整的不斷深入,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在全球經濟危機和歐美主要國家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2013 年我國GDP總量實現7.7%的增長,達到58.8 萬億元,成功實現經濟的軟著陸[1]。但是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環境污染問題逐漸突出,水體污染尤為嚴重。同時環境治理成本逐漸增加,其占GDP 比重逐年上升。國家環保總局發布的全國環境統計公報顯示,2013 年,全國廢水排放總量695.4 億t;同時加大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達到9 037.2億元[2]。
1 文獻綜述
在流域水體污染治理項目的政府行政治理機制研究方面,學者們在吸收國外流域水體污染治理項目經驗的研究基礎之上,提出建立排污權交易市場、征收環境稅和科層級的治理模式。李曉峰針對污染的負外部性特征,提出通過稅收或產權交易使外部成本內部化,探討圍繞外部收益內部化制定環境經濟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實施排污權交易的建議[3]。毛顯強等在研究瑞典的環境問題時,從三個方面入手,指出瑞典環境稅制度對中國的借鑒意義[4];施祖麟等結合國外跨行政區水資源管理經驗,研究適合中國國情的跨行政區水污染治理管理機制研究,為我國解決跨行政區水污染治理提出可行的方法[5];黃德春等在介紹萊茵河、五大湖、多瑙河等跨國界河流以及美國田納西河、英國泰晤士河、意大利波河等跨省界河流的水污染治理機制的基礎之上,提出中國在跨界流域水污染治理方面可以采取五個方面的措施[6];陳燕等分析美國現行的環境經濟政策,討論我國環境經濟政策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改善政策[7];王勇分析澳大利亞墨累-達令流域治理中府際治理機制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提出我國流域污染治理應該引入科層型協調機制以及市場型協調機制[8];劉登娟等分析瑞典環境經濟手段作用機理,總結中國環境經濟手段的成績與不足,提出我國應該實行環境稅的建議[9]。
以上研究成果,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但上述文獻對政府查處策略的內在機理和對環保執法策略有效性的研究相對薄弱。因此,本文從流域水體污染治理項目監管主體與客體間的機會利益角度出發,結合流域水體污染治理的信息不對稱和公共物品特性,建立監管主體與客體間“查處-偷排”收入預期博弈模型,主要回答兩個問題:
(1)流域水體污染治理項目中環保等監管部門實施查處偷排行為策略的內在機理是什么?
(2)流域水利污染治理項目中環保等監管部門查處企業偷排行為的策略是否有效?以及如果存在策略失效,應該如何進行策略調整?
2 監管部門和排污企業的收入預期博弈模型及困境化解
在流域水體污染治理項目中,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和排污企業間的博弈同流域上下游企業間的博弈類似,都是客觀存在的,而且雙方都是博弈的參與人,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決定是否實施對企業的偷排行為進行查處的策略,而排污企業根據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是否對偷排行為進行查處和偷排收益與損失比這兩個指標來決定是否進行污水偷排行為。
2.1 模型有關變量的假定
假定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有效執行監管職能的正常收入為a,因查處偷排行為而得到的獎勵收入為b,因排污單位違規排放而未能有效查處而收到的懲罰損失為c,執法成本為d。排污企業的職責是在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之上進行商業活動,其正常收益水平為u,因偷排等行為而沒有受到監管部門查處所獲得的收益增加值為k,因被發現偷排等行為而受到的處罰損失為h,因在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的多次檢查過程中排污企業很好地執行國家的環保政策和法規而獲得的政府獎勵為g。
2.2 不對稱信息條件下博弈雙方支付設定
假設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和排污企業都存在自己的最優選擇,設定為e = (0,1)。對于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而言,e=0 是不采取對偷排行為進行查處的策略;e=1 是對偷排行為采取查處的策略。同樣的對于排污企業而言,e=0 是不采取偷排行為的策略;e =1 是采取偷排行為的策略。在排污企業施行偷排策略的情況下,監管部門查處的收益為a +b-d,監管部門不查處的收益為a-c;同時排污企業在監管部門查處的情況下的收益為u-h,偷排行為沒有被查處而獲得的收益是u+k。在排污企業不施行偷排策略的情況下,監管部門查處的收入為a-d,不查處的收入為a;同樣的在監管部門查處的情況下企業不偷排所產生的收入為u+g,監管部門不查處時企業的收益為u。通過對經典博弈模型的拓展,從而得出以下博弈雙方收益矩陣分析表(表1)。

表1 不對稱信息條件下博弈雙方收益矩陣分析表
2.3 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和排污企業最優行為選擇策略分析
如果排污企業偷排的概率為x (0≤x ≤1),則企業不偷排的概率為1-x。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查處的概率為y(0≤y ≤1),不查處的概率為1-y。假設排污企業偷排的概率x 的取值為某一特定概率值,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進行執法(e=1)和不進行執法(e=0)的期望收益為

令式(1)等于式(2),即E(1,x)= E(0,x),得出無論監管部門選擇執法(e =1)還是不執法(e =0)的策略,排污企業的最優偷排概率為x*=d/(b + c)。
同理可得,假定監管部門查處的概率y 的取值為某一個特定的概率值,排污企業選擇偷排(e=1)和不選擇偷排(e=0)的期望收益為

令式(3)等于式(4),即E(0,y)= E(1,y),得出無論排污企業選擇偷排還是不偷排的策略,監管部門的最優查處概率為y*= g/(h +k +g)。
通過對上述博弈雙方最優選擇概率的綜合,可以推出“查處-偷排”收入預期博弈模型的博弈雙方納什均衡解為[{d/(b + c),1-d/(b +c)},{g/(h + k + g),1-g/(h + k + g)}]。
2.4 結合流域水體污染治理項目外部性特征的模型結論分析
2.4.1 排污企業博弈行為分析
當預期收益k + g <h 時,即企業偷排所獲得的收益和政府補貼等遠遠小于偷排行為的處罰損失時,這時企業的最優偷排概率x*= d/(b +c)為零,企業的偷排行為幾乎不可能發生,因此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的最優查處概率y*= g/(h +k +g)為零,流域整體福利水平達到帕累托最優。
對于排污企業而言,如果因為偷排等行為而沒有受到環保部門等監管部門的查處所獲得的收益為k >h,即收益大于懲罰損失,在市場決定的均衡下,企業會不顧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的執法而繼續進行偷排,進而導致流域整體排污量增加,流域水體污染加重,污染的外部性致使社會整體福利水平受到損失。根據庇古的理論,外部性最直接的解決方法是對產生外部性的經濟體征稅。所有以激勵為基礎的外部性解決方案都來源于這個基本的直覺。因此針對污染的外部性特性,可以采用庇古稅等手段進行外部性糾正。假定一個環境稅稅率為γ,使得k × (1-γ)≤h,即企業偷排所產生的收益在征收了環境稅之后小于等于懲罰損失,在環保部門不斷加強監管力度的情況下企業偷排的概率x*= d/(b + c)接近于零,企業的偷排動機消失。同時,根據企業間“偷排-清潔生產”收入預期模型的結論,可以通過對企業采取清潔生產提供補貼和獎勵等外部性收入激勵來降低企業偷排的概率。因此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在加大執法力度的同時應該引入環境稅和清潔生產補貼等手段,消除排污企業的偷排動機和行為,推動流域福利水平向帕累托最優方向改進。
如果預期收益k 和處罰損失h 幾乎相等,則排污企業選擇排污與否不具有絕對性,但是在存在政府獎勵收入g 和污染排放權交易收入G1的情況下,企業存在外部收入的激勵因素,因此企業會選擇遵守國家的環保法律和法規進行清潔生產,企業的最優偷排概率為x*= d/(b +c),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的最優查處概率為y*= g/(h +k + g)。
2.4.2 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的行為分析
針對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而言,假設d <a +b-d <a-c,化簡為d-a <b-d <-c,即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查處企業偷排行為所產生的收益小于不查處時的收益并大于執法成本,在沒有任何外部激勵或者有效收入彌補的情況下,此時監管部門的最優查處概率y*= g/(h + k + g)為零,排污企業的最優違規偷排概率x*= d/(b +c)接近于1,企業明目張膽地進行污水排放而不受任何約束,流域水體污染狀況加重,流域區域福利水平下降,流域福利狀態存在帕累托改進的余地。因此,為了避免出現監管部門的職能缺失,政府部門可以考慮設立執法獎勵基金或者其他執法激勵的手段提高環保部門的查處積極性及概率。假設存在政府的執法獎勵β,使得β + b-d ≥- c,此時環保部門查處偷排所產生的收益大于不查處時的收益并且大于執法成本,環保部門存在執法的外部收入激勵因素,此時環保部門的最優查處概率y*= g/(h+k+g)接近于1,環保部門的執法力度和效率明顯提升。同樣的政府執法獎勵β 也適用于環保部門查處收益小于執法成本時的情況。
如果環保部門對企業偷排行為的查處收入a +b-d >a-c >d,化簡為b-d + c >a-c >d-a,即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對于排污企業的偷排行為進行查處所產生的收益大于不查處時的收益并且大于執法成本,監管部門存在查處的收入激勵因素,此時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的最優查處概率y*= g/(h+k+g)接近于1,監管部門的查處行為會時時發生,排污企業的最優違規偷排概率x*= d/(b + c)接近于零,企業的偷排動機得到有效遏制,流域污染水平下降,流域區域的整體福利水平提高,流域生態環境得到明顯的改善。
如果a + b-d ≈a-c 時,即環保部門查處和不查處排污企業的偷排行為所產生的收入相當時,則環保部門等監管主體會以y*= g/(h +k +g)的概率進行查處,此時排污企業的最優違規排放概率為x*= d/(b +c),博弈雙方達到納什均衡狀態。但是對整個社會而言存在福利帕累托改進余地,因此,如果政府部門采取多種激勵手段,比如單位榮譽或者豐厚的年終福利等方式對監管部門的查處行為進行激勵,致使環保部門加大監管執法的概率和強度,則企業的最優違規偷排概率會下降,進而推動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提升。
因此,針對流域污染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特性所造成的治理機制失靈,政府可以在適當的時候考慮引入環境資源稅和建立環保執法基金,在對企業的偷排行為進行收入約束的同時,加大對執法部門查處行為的外部收入激勵,進而消除排污企業的偷排動機和提高環保部門的執法積極性及執法效率,減少流域的整體排污量和改善流域的生態狀況,提高流域區域的整體福利水平。
3 結語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監管部門的執法措施沒有完全落到實處。為此,本文就流域水體污染治理項目提出幾點建議:
(1)完善相關排污治理法制法規,使得流域排污總量能夠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
(2)完善流域水體污染治理的行政架構體系建設,建立跨行政區跨職能部門垂直的綜合治理機構,引入科層制和市場化的運行機制,提高流域水體污染治理執法的直接性和效率,發揮市場調節的基礎性作用,彌補可能的政府職能缺失造成的執法真空。
(3)加快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的立法進程和加強流域水體污染執法的監察力度,杜絕地方政府執法和中央政府政策脫節現象的發生,從法律和行政機制上消除中央和地方存在的不對稱信息博弈困境,拓寬公眾參與流域環境治理的渠道,不斷增強民眾參與流域水體污染治理的廣度和深度。
[1] 國家統計局. 中國統計公報2013 [EB/OL] . http://data. stats. gov. cn/workspace/index?m=hgjd.
[2] 國家環保總局. 中國環境狀況公報2012 [EB/OL].http://zls. mep. gov. cn/hjtj/nb/.
[3] 李曉峰. 征稅還是補貼:對當前環境經濟政策的反思[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4 (2):25-30.
[4] 毛顯強,楊嵐. 瑞典環境稅:政策效果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 環境保護,2006 (2):90-95.
[5] 施祖麟,畢亮亮. 我國跨行政區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管理機制的研究:以江浙邊界水污染治理為例[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7 (3):3-9.
[6] 黃德春,陳思萌,張昊馳. 國外跨界水污染治理的經驗與啟示[J]. 水資源保護,2009 (4):78-81.
[7] 陳燕,藍楠. 美國環境經濟政策對我國的啟示[J].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0 (2):38-42.
[8] 王勇. 澳大利亞流域治理的政府間橫向協調機制探析:以墨累-達令流域為例[J]. 科學·經濟·社會,2010 (1):162-165.
[9] 劉登娟,黃勤. 瑞典環境經濟手段經驗借鑒及對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啟示[J] . 華東經濟管理,2013 (5):34-37. P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