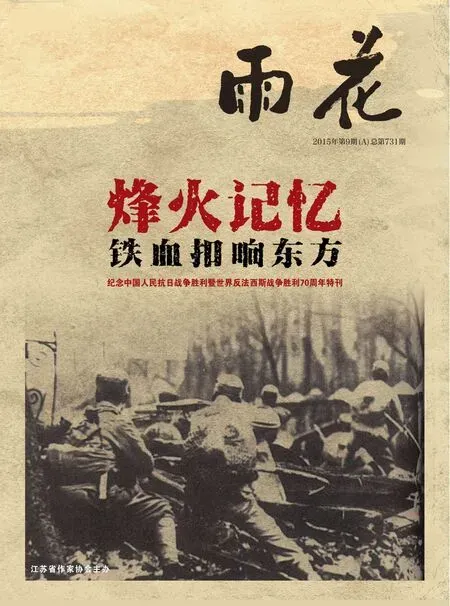中國(guó)勝利日:1945年9月9日
◎ 傅寧軍
中國(guó)勝利日:1945年9月9日
◎ 傅寧軍
1945年9月10日,重慶《大公報(bào)》頭版頭條,發(fā)表了記者自南京發(fā)回的重磅消息《日軍簽降一幕》:“1945年9月9日九時(shí)到九時(shí)二十分,是我們歷史上最光榮、最肅穆的二十分鐘。在這二十分鐘內(nèi),日將岡村寧次到我陸軍總司令部,簽訂了中國(guó)戰(zhàn)區(qū)及越南百萬(wàn)日軍的降書,何總司令應(yīng)欽把這個(gè)八年苦戰(zhàn)我千百萬(wàn)軍民血肉生命換得的榮譽(yù)結(jié)果,用廣播傳送給全世界……”
八年前,1937年12月,也就在南京,這個(gè)當(dāng)時(shí)的民國(guó)之都。中國(guó)守軍南京保衛(wèi)戰(zhàn)失利,被淞滬戰(zhàn)役阻滯的侵華日軍,以猛烈炮火攻破了古老城墻。當(dāng)日本舉國(guó)歡慶占領(lǐng)南京勝利的時(shí)候,30萬(wàn)無(wú)辜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被殘酷殺害。秦淮河漂浮著數(shù)不清的尸體,美麗的六朝勝地一時(shí)竟成人間地獄。日本軍人以最無(wú)恥、最殘忍、最瘋狂的獸性,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
1945年9月9日的南京受降,一雪國(guó)恥,無(wú)上榮光!
我不僅一次地,穿過(guò)南京熙熙攘攘的繁華城區(qū),走向一條兩旁長(zhǎng)滿梧桐樹(shù)的筆直大道,凝望當(dāng)年舉行侵華日軍南京受降儀式的大禮堂,它仍然保持著原有的姿勢(shì),尖頂、圓柱、長(zhǎng)廊、石階,默默地屹立在紫金山下。
我時(shí)常回想寫入了中國(guó)抗戰(zhàn)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zhēng)史冊(cè)的那一天,都說(shuō)時(shí)光易逝,而事關(guān)整個(gè)民族命運(yùn)的莊嚴(yán)時(shí)刻,永遠(yuǎn)將被牢牢銘記。
2015年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前夕,我想用后輩的敬重與虔誠(chéng),還原南京受降日的真實(shí)細(xì)節(jié)。我尋訪在世的抗戰(zhàn)老兵,他們雙鬢染霜,提及當(dāng)年在恥辱中奮起的艱辛歷程,依然充滿激情。他們說(shuō),鋼鐵一般的史實(shí),豈能被唾沫星子歪曲!中國(guó)人民是善良的,作為二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guó),沒(méi)在日本國(guó)土派駐一兵一卒。中國(guó)回顧抗戰(zhàn)的基調(diào)很明確,紀(jì)念勝利、緬懷先烈、追求和平。遺憾的是,卻有少數(shù)日本人否認(rèn)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無(wú)視日本侵華的歷史事實(shí),無(wú)視戰(zhàn)爭(zhēng)中逝去的萬(wàn)千無(wú)辜生命!
重溫抗戰(zhàn)受降日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抗戰(zhàn)老兵向我推薦了一幅紀(jì)實(shí)油畫,題目叫《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shí)·南京》。聽(tīng)這標(biāo)題就知道,這是一幅記述南京受降日的史實(shí)性畫作。它向世人展示了屢受列強(qiáng)欺凌的中華民族,在近代史上取得的第一個(gè)勝利,它的誕生與此后的命運(yùn),引發(fā)著人們的深切思考……
一
在93歲的抗戰(zhàn)老兵、國(guó)軍少校王楚英家的書房,書櫥里放著多年收集的抗戰(zhàn)史料書籍,墻上掛著油畫《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shí)·南京》的高仿復(fù)制件。王楚英告訴我,盡管油畫有藝術(shù)加工,但畫家忠于史實(shí),中日雙方代表有名有姓,動(dòng)作姿態(tài)都作了考證。畫家曾把王楚英請(qǐng)到工作室傾聽(tīng)了意見(jiàn)。
這幅迄今為止唯一的以南京日軍受降儀式為表現(xiàn)對(duì)象的大型油畫,作者陳堅(jiān)是以紀(jì)實(shí)風(fēng)格見(jiàn)長(zhǎng)的著名油畫家。上世紀(jì)七十年代,從士兵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陳堅(jiān)由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油畫系畢業(yè),調(diào)入南京軍區(qū)創(chuàng)作室,用畫筆追蹤軍人的戰(zhàn)爭(zhēng)與和平。他走進(jìn)的南京軍區(qū)機(jī)關(guān)大院,在紫金山下頗有傳奇色彩,曾是劉伯承元帥主掌的軍事學(xué)院所在地,再往前則是民國(guó)時(shí)期的中央軍校(前身黃埔軍校)所在地。
1987年,陳堅(jiān)又到王府井新華書店“淘書”。每次到北京他都有這樣的老習(xí)慣。他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紀(jì)實(shí)圖書特別感興趣,買了一本《中外記者筆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書中收錄的四十多年前重慶《大公報(bào)》的文章,是寫中國(guó)戰(zhàn)區(qū)受降大典的盛況的,這篇千余字的舊新聞《日軍簽降一幕》,他一連讀了好幾遍。舊新聞給他一種新視角,中國(guó)人艱苦抗戰(zhàn)后迎來(lái)勝利的無(wú)比激動(dòng),深深地觸動(dòng)了他。
也許是一種歷史的巧合吧,如今南京軍區(qū)大禮堂,正是中央軍校大禮堂,也就是1945年中國(guó)戰(zhàn)區(qū)舉行受降大典的舊址。陳堅(jiān)的畫室高大敞亮,位于大禮堂的側(cè)樓。當(dāng)他知道這座宏偉建筑曾經(jīng)擁有的榮光,每天再?gòu)拇蠖Y堂的圓柱長(zhǎng)廊走過(guò),心頭就涌起潮水般的感慨。他時(shí)常凝望這座西洋式的尖頂建筑,回味著大禮堂外民眾的歡呼聲和鼓樂(lè)聲,回味著《大公報(bào)》新聞稿傳達(dá)的民族自豪。
這是每個(gè)中國(guó)人都該銘記的時(shí)刻,是當(dāng)今的世界不該遺忘的時(shí)刻!填補(bǔ)中國(guó)繪畫史的這一空白,陳堅(jiān)提起畫筆又放下,激動(dòng)之余有些惶惑。民國(guó)檔案當(dāng)時(shí)屬于“禁區(qū)”,單憑道聽(tīng)途說(shuō),包括舊聞報(bào)道,還是粗線條的概念,無(wú)法描繪真實(shí)的受降詳情。陳堅(jiān)創(chuàng)作其他抗日題材油畫的時(shí)候,總會(huì)想到畫室所在的這座大禮堂的風(fēng)云際會(huì),這里奏響過(guò)抗日戰(zhàn)爭(zhēng)的最后樂(lè)章。他在思考,在醞釀,在等待。
直到上世紀(jì)九十年代初,撥亂反正、尊重歷史逐步成為共識(shí),國(guó)軍抗戰(zhàn)老兵的功績(jī)也得到了應(yīng)有的承認(rèn),陳堅(jiān)更感到責(zé)無(wú)旁貸。他像一個(gè)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者那樣,泡在中國(guó)第二歷史檔案館,翻閱一堆堆的民國(guó)檔案,尤其是一張張發(fā)黃了的老照片。他像一個(gè)盡職的記者那樣,拜訪健在的國(guó)軍抗戰(zhàn)老兵,核對(duì)受降儀式上的人與事,不放過(guò)任何一個(gè)細(xì)枝末節(jié),在浩瀚的史海中打撈著失落的記憶碎片。
陳堅(jiān)
要畫,就要對(duì)得起抗戰(zhàn)的前輩,要經(jīng)得起時(shí)間的檢驗(yàn)!1993年,陳堅(jiān)著手構(gòu)思油畫草圖。那些走進(jìn)歷史的人物又從封塵的歷史中走出,與他朝夕相伴。他不僅揣摩所有當(dāng)事人在那一瞬間的神情,還沿著他們的人生軌跡,觸摸著他們各自的精神脈絡(luò),直至中日之戰(zhàn)的遠(yuǎn)因與近果,詮釋一個(gè)個(gè)被歲月湮沒(méi)的重重謎團(tuán)。
昨天的輝煌一幕,在中國(guó)畫家的筆下,緩緩地拉開(kāi)……
二
1945年日本宣布無(wú)條件投降之時(shí),抗戰(zhàn)中內(nèi)遷后的國(guó)民黨政府尚在陪都重慶,為什么中國(guó)戰(zhàn)區(qū)受降典禮沒(méi)有選擇重慶,而是選擇在南京?
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diǎn):一是南京為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guó)時(shí)定的首都,也是抗戰(zhàn)前的首都,明確宣布勝利后將還都南京。二是1937年12月13日,日軍侵占南京后燒殺搶掠,30萬(wàn)中國(guó)人被殺的大屠殺慘劇震驚中外,南京是遭受日軍蹂躪最慘重的城市,時(shí)隔八年在這里舉行受降典禮,更具有象征意義。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在電臺(tái)播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詔書。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無(wú)條件投降。當(dāng)日,蔣介石急電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提出日軍六項(xiàng)投降原則,指派時(shí)在廣西南寧督戰(zhàn)的中國(guó)陸軍總司令何應(yīng)欽代表中國(guó)戰(zhàn)區(qū)最高統(tǒng)帥全權(quán)主持日軍受降事宜。21日,在湖南芷江舉行洽降儀式,日本中國(guó)派遣軍副總參謀長(zhǎng)今井武夫作為投降使節(jié),向中方呈送編制圖冊(cè),在投降備忘錄上簽字。今井武夫一行8人隨后飛返南京,向?qū)鍖幋螀R報(bào)南京投降儀式日程。
芷江洽降是序曲,南京受降是高潮。
史料記載:1945年9月9日,在日偽統(tǒng)治下8年的南京,滿城是新生的喜悅。街道兩旁披上節(jié)日的盛裝,到處喜氣洋洋,像過(guò)年一樣興高采烈。一些主干道均用松柏枝葉扎起彩色牌樓,牌樓上懸掛著中國(guó)國(guó)旗和國(guó)民黨黨旗,兩旗中間是紅色的“V”標(biāo)記,牌樓上鑲嵌著“勝利和平”四個(gè)金色大字。
黃埔路3號(hào)的中央軍校大門上方,懸掛著一塊藍(lán)底橫額,上寫楷書“中國(guó)陸軍總司令部”的白色大字。門前的牌坊懸掛紅布橫幅,貼有“中國(guó)戰(zhàn)區(qū)日本投降簽字典禮會(huì)場(chǎng)”的熠熠金字。大禮堂的廣場(chǎng)四周旗桿林立,聯(lián)合國(guó)五十二個(gè)國(guó)家的國(guó)旗迎風(fēng)飄揚(yáng),每個(gè)旗桿下面站著一名武裝士兵和一名憲兵。后來(lái),這五十二面聯(lián)合國(guó)國(guó)旗,作為日軍投降的見(jiàn)證,分別贈(zèng)送各國(guó)駐華使館留作紀(jì)念。
其實(shí),中國(guó)受降主官的何應(yīng)欽身為中國(guó)陸軍總司令、一級(jí)上將,前一天中午才乘坐“美齡號(hào)”專機(jī),在九架戰(zhàn)斗機(jī)的護(hù)衛(wèi)下,由芷江飛抵南京機(jī)場(chǎng)。這也是何應(yīng)欽隨南京國(guó)民政府遷都重慶八年后重回南京故地。
“中國(guó)陸軍總司令部”從何而來(lái)?原來(lái),侵華日軍代表赴云南芷江向中國(guó)陸軍總部洽降后,中國(guó)軍方就派人隨日方飛機(jī)赴南京,作為中方受降聯(lián)絡(luò)官。8月27日,中國(guó)陸軍副參謀長(zhǎng)冷欣受中國(guó)政府委派,率員從芷江飛至南京,設(shè)立“中國(guó)陸軍總司令部前進(jìn)指揮所”。參與南京受降的中國(guó)軍隊(duì),由名揚(yáng)滇緬抗日戰(zhàn)場(chǎng)的新六軍擔(dān)當(dāng),新六軍也奉命成立了前進(jìn)指揮部,所屬官兵分批空運(yùn)南京。
王楚英記得,8月27日下午二時(shí),從芷江機(jī)場(chǎng)起飛的七架飛機(jī),在南京大校場(chǎng)機(jī)場(chǎng)降落。“當(dāng)我乘坐的飛機(jī)在南京上空盤旋的時(shí)候,我憑窗俯瞰,山河雖然依舊,景物卻甚凋敝。在機(jī)場(chǎng)附近田間耕作的農(nóng)民和居民,一見(jiàn)到闊別八年的中國(guó)飛機(jī)與中國(guó)軍人,他們欣喜若狂,一起涌向機(jī)場(chǎng)的外壕外,揮舞草帽頭巾,向著剛下飛機(jī)的我們致意。一種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民族情感,從我的心頭升起。”
新六軍有此殊榮,緣于英勇抗日的赫赫戰(zhàn)功。
1944年8月5日,中國(guó)駐印軍攻克密支那后,部隊(duì)休整充實(shí),新二十二師、第十四師、第五十師合編為新六軍。廖耀湘升任新六軍軍長(zhǎng),以前他率部與日軍鏖戰(zhàn)于叢山密林,擊敗號(hào)稱“常勝軍”及“森林戰(zhàn)之王”的日軍精銳師團(tuán),所創(chuàng)造的叢林戰(zhàn)的典范,受到英美同盟軍指揮官史迪威將軍的贊揚(yáng)。廖耀湘獲青天白日勛章一枚,新二十二師及其六十五團(tuán)各獲虎旗一面,新六軍獲得了“叢林之虎”的美譽(yù)。曾參加過(guò)南京保衛(wèi)戰(zhàn)慘敗的廖耀湘,足以告慰血灑古都的將士。
1945年8月21日的芷江洽降時(shí),日本中國(guó)派遣軍副總參謀長(zhǎng)今井武夫向國(guó)民黨陸軍司令部洽降,中國(guó)陸軍總司令何應(yīng)欽指示在芷江機(jī)場(chǎng)設(shè)立受降臺(tái),接受日軍受降文件,時(shí)任軍長(zhǎng)的廖耀湘將軍率新六軍高級(jí)軍官登臺(tái)參加。隨后,新六軍又被中國(guó)戰(zhàn)區(qū)統(tǒng)帥部選為代表中國(guó)的受降部隊(duì),這是對(duì)新六軍的莫大肯定。
當(dāng)時(shí),南京還在侵華日軍的掌控之下。新六軍迅速在南京各地布防,嚴(yán)令日軍只能呆在營(yíng)區(qū)內(nèi),聽(tīng)從中國(guó)陸軍司令部的命令。剛到南京,新六軍警衛(wèi)營(yíng)所有官兵不敢懈怠,手不離槍,子彈上膛,擔(dān)心日軍在投降后孤注一擲。不過(guò),他們發(fā)現(xiàn),日軍雖已戰(zhàn)敗,并沒(méi)有潰不成軍,也沒(méi)有劍拔弩張,在營(yíng)區(qū)仍保持著整體的紀(jì)律。無(wú)論是官是兵,見(jiàn)到中國(guó)軍人都畢恭畢敬,向受降方立正敬禮。
定為中國(guó)戰(zhàn)區(qū)受降典禮主會(huì)場(chǎng)的大禮堂,一洗蒙羞的窘態(tài),恢復(fù)了莊嚴(yán)的氣派,戒備森嚴(yán),氣氛莊重。大禮堂的正面,是一塊用松柏枝扎的橫匾,上書金色大字“和平永奠”,還插有一面中國(guó)國(guó)旗。禮堂正門上,懸掛著中、美、英、蘇四國(guó)國(guó)旗。禮堂中央掛著孫中山像,兩旁是中國(guó)國(guó)旗和國(guó)民黨黨旗,下面點(diǎn)綴了紅色“V”符號(hào)與“勝利和平”四個(gè)金色大字。對(duì)面墻上懸掛著中、美、英、蘇四國(guó)元首的肖像。
日本投降代表簽字的桌子上方,懸掛著四盞巨型銀光燈,耀眼奪目。投降席對(duì)面為受降席。四周肅然挺立武裝士兵。簽字臺(tái)兩旁是參觀盛典的中外來(lái)賓和新聞?dòng)浾摺巧鲜侵型夤賳T的觀禮席,共計(jì)200余人,加上室內(nèi)外儀仗隊(duì)以及擔(dān)任現(xiàn)場(chǎng)警衛(wèi)的憲兵,有1000人左右。憲兵來(lái)自新六軍的警衛(wèi)營(yíng),頭戴鋼盔,腳穿皮鞋,身穿嗶嘰呢制服,手戴白手套,手持藍(lán)德半自助步槍,威風(fēng)凜凜。
當(dāng)年在受降現(xiàn)場(chǎng)的警衛(wèi)營(yíng)營(yíng)長(zhǎng)、少校趙振英,為能目睹南京日軍投降倍感自豪。美國(guó)記者拍下的受降儀式的視頻上,可見(jiàn)他頭戴鋼盔的勃勃英姿。他說(shuō),新六軍是國(guó)軍中的精銳之師,所有官兵身著美式軍裝,上衣扎在腰帶里,腿上是作戰(zhàn)皮鞋。畢竟從戰(zhàn)場(chǎng)上下來(lái),還覺(jué)得不夠精神,臨時(shí)制作了高腰馬靴。
重視軍人儀表,視之為軍人的榮譽(yù),這是中外軍隊(duì)共同的素質(zhì)要求。無(wú)庸諱言,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的艱難年代,中國(guó)軍隊(duì)的裝備之落后,中國(guó)軍人的服裝之粗糙,都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寧可舍近求遠(yuǎn),也要把美式裝備的新六軍運(yùn)來(lái)南京,讓一支威武之師出現(xiàn)在淪陷區(qū),無(wú)疑也有為中國(guó)抗日軍人爭(zhēng)光的意思。
那么,為什么正式受降時(shí)間選在9月9日上午九時(shí)?這個(gè)頗有講究的莊嚴(yán)時(shí)辰,并非隨便安排,而是蔣介石親自敲定的。
一至十的各個(gè)數(shù)字中,中國(guó)人向來(lái)最崇尚九,以為天地之?dāng)?shù),始于一而終于九,逢九即為大吉大利。蔣介石對(duì)風(fēng)水時(shí)辰向來(lái)篤信,因而將受降簽字儀式舉行之時(shí)定在三個(gè)“九”字相遇的時(shí)候,寓意“三九良辰”。
忠實(shí)于歷史的陳堅(jiān)精心構(gòu)思的畫面,不是古城的狂歡,也不是廣場(chǎng)的盛況,而是鎖定“三九良辰”。那個(gè)最寂靜的時(shí)刻,也最扣人心弦。陳堅(jiān)先給油畫起名《落日:1945年9月9日9時(shí)》,后來(lái)他感到,敘述史實(shí),應(yīng)該更公正、更客觀,去掉外在的評(píng)說(shuō),改名《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shí)·南京》。
三
雙手托舉起軍刀,曾經(jīng)指揮官兵屠殺中國(guó)人的軍刀,面向受降的中國(guó)將領(lǐng)深深鞠躬,該是日軍將領(lǐng)在受降儀式上的典型動(dòng)作。
陳堅(jiān)知道,繳械投降,是戰(zhàn)爭(zhēng)失敗一方的必然程序。兩軍對(duì)壘之后,軍人交出武裝,自然是一個(gè)投降的標(biāo)志性動(dòng)作。他看過(guò)南京受降儀式舉行之后,各地舉行的日軍投降儀式的照片,都有日軍指揮官交出軍刀的情節(jié)。尤其是北平太和殿前的甬道旁,日軍指揮官排著隊(duì)挨個(gè)上前,低著頭把軍刀放在桌上。
然而,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在隆重的南京日軍受降儀式上,侵華日軍的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卻沒(méi)有交出軍刀!因?yàn)樗揪蜎](méi)把軍刀帶來(lái)!
陳堅(jiān)查閱檔案,看到南京日軍受降簽字儀式舉行前,中國(guó)陸軍總司令部曾以“中字第17號(hào)備忘錄”致岡村寧次,其中有這樣的表述:“根據(jù)盟軍最高統(tǒng)帥麥克阿瑟將軍規(guī)定:1.日軍繳械時(shí),不舉行收繳副武器之儀式。2.日軍代表于正式投降時(shí),不得佩帶軍刀。3.凡日軍所有軍刀,均應(yīng)與其他武器一律收繳,一俟正式投降,日軍即不得再行佩帶軍刀。以上規(guī)定,在中國(guó)戰(zhàn)區(qū)一律適用。”
日本軍官所佩軍刀,從來(lái)是不離身的,收繳軍刀本來(lái)應(yīng)該不是問(wèn)題。此前,中國(guó)戰(zhàn)區(qū)指揮部已決定,在日軍投降簽字時(shí),解除日軍投降代表的軍刀,將岡村寧次、小林淺三郎、今井武夫的軍刀,分別獻(xiàn)給中國(guó)陸軍總司令何應(yīng)欽、陸軍參謀長(zhǎng)蕭毅肅、陸軍副參謀長(zhǎng)冷欣。岡村寧次接到備忘錄,違背日軍無(wú)條件投降的規(guī)定,一再請(qǐng)求中方提示簽字時(shí)出示證明文件載明的事項(xiàng),事先了解投降書內(nèi)容。
日軍投降書內(nèi)容及日軍投降簽字后,中國(guó)戰(zhàn)區(qū)最高統(tǒng)帥頒發(fā)“第1號(hào)命令”抄件, 經(jīng)請(qǐng)示中國(guó)陸軍總司令何應(yīng)欽同意,由副參謀長(zhǎng)冷欣派員,于9月8日晚秘密送岡村寧次閱。冷欣告知岡村寧次,何應(yīng)欽長(zhǎng)官有約在先:1.不許抄錄。2.不準(zhǔn)提修改意見(jiàn)。3.不得于簽字前宣揚(yáng),閱后隨即取回。
何應(yīng)欽奉命主持日軍受降儀式前,曾派他所信任的參謀王武上校到岡村寧次住處,向?qū)逋嘎叮瑓⒓油督祪x式可佩帶指揮刀,但必須在禮堂內(nèi)將指揮刀呈繳何應(yīng)欽;否則就不帶刀。帶與不帶,可由岡村自己選擇。岡村當(dāng)然不愿成為呈繳指揮刀的敗將,而寧肯當(dāng)“不帶刀的將軍”。這一說(shuō)法流傳甚廣。
何應(yīng)欽能主持中國(guó)戰(zhàn)區(qū)日軍受降,在中國(guó)抗戰(zhàn)史上留下一筆,實(shí)在是運(yùn)氣所致。何應(yīng)欽是貴州興義人,字敬之,曾任黃埔軍校總校官、國(guó)民革命軍第一軍長(zhǎng)、北伐軍東路總指揮、南京政府第一路軍總指揮要職。1930年起任軍政部長(zhǎng)至1944年。抗日時(shí)期歷任第四戰(zhàn)區(qū)司令長(zhǎng)官、軍委參謀總長(zhǎng)、國(guó)防委員會(huì)常委。蔣介石之所以選中何應(yīng)欽代表他主持受降,首先因?yàn)榇砣哲娡督档膶鍖幋问谴髮ⅲ⒎侨毡拒姺阶罡呤组L(zhǎng)。身為中國(guó)戰(zhàn)區(qū)最高統(tǒng)帥、特級(jí)上將的蔣介石,若主持受降有失尊嚴(yán)。而何應(yīng)欽兼陸軍總司令、一級(jí)上將,職務(wù)軍階與岡村寧次相等。
中方受降主官何應(yīng)欽,身為陸軍上將,又是蔣介石倚重的親信,位于民國(guó)政府中樞,對(duì)于日方投降主官的岡村寧次,為何如此寬大?原來(lái),他們?cè)侨毡娟戃娛抗賹W(xué)校的校友,按年齡說(shuō),岡村寧次是何應(yīng)欽的學(xué)長(zhǎng),而且私交頗深。“九·一八”事變后,何應(yīng)欽忠實(shí)執(zhí)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方針,代表蔣介石與日軍暗中商談妥協(xié)的可能,參與“何梅協(xié)定”的簽署,曾被民間嘲諷為“親日派”。有人說(shuō),蔣介石選擇何應(yīng)欽主持受降,有意替他在國(guó)人面前洗刷過(guò)去的污點(diǎn)。
何應(yīng)欽對(duì)岡村寧次的百般照顧,固然是老校友,是一貫的親日立場(chǎng),更主要是蔣介石“以德報(bào)怨”的有言在先,他能體恤蔣介石的用心。果然,岡村寧次日后逃過(guò)軍事審判,還曾為蔣介石的軍事戰(zhàn)略出謀劃策。
陳堅(jiān)并沒(méi)有把何應(yīng)欽臉譜化。歷史如此矛盾地選擇了他,但何應(yīng)欽代表的不是他個(gè)人,畢竟是一個(gè)浴血奮戰(zhàn)的民族。他是以怎樣的心態(tài)和神情來(lái)?yè)?dān)此重任的呢?陳堅(jiān)尋思良久,畫出的何應(yīng)欽一身戎裝,左手輕輕撥動(dòng)桌面,直立而挺拔的軍人姿態(tài),不失風(fēng)度地展現(xiàn)了勝利者的自豪和威嚴(yán)。至于他對(duì)面的岡村寧次,低下了不可一世的頭,他不是向他的老校友彎腰鞠躬,而是向中國(guó)人認(rèn)罪投降!
中方受降代表5人。中國(guó)陸軍總司令何應(yīng)欽一級(jí)上將位于正中,左側(cè)是海軍總司令、陳紹寬海軍上將、空軍第1路軍司令、張廷孟空軍上校。右側(cè)為陸軍第三戰(zhàn)區(qū)司令顧祝同陸軍二級(jí)上將、陸軍參謀長(zhǎng)蕭毅肅陸軍中將。中方受降席上,擺著一只時(shí)鐘,放了一套有文房四寶的漆盤。《降書》《中國(guó)戰(zhàn)區(qū)最高統(tǒng)帥第一號(hào)命令》順?lè)虐割^。給何應(yīng)欽當(dāng)日語(yǔ)翻譯的,是陸軍總司令部參謀王武上校。
日方投降代表7人。除了日本大本營(yíng)授權(quán)的簽字人、日本中國(guó)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陸軍大將,還有日本中國(guó)派遣軍總參謀長(zhǎng)小林淺三郎陸軍中將、副總參謀長(zhǎng)今井武夫陸軍少將、參謀小笠原清陸軍中佐,中國(guó)方面艦隊(duì)司令福田良三海軍中將,駐中國(guó)臺(tái)灣第10方面軍參謀長(zhǎng)諫山春樹(shù)陸軍中將,駐法屬印度支那第38軍參謀長(zhǎng)三澤昌雄陸軍大佐。日本翻譯木村辰男,恭立于岡村寧次身后。
南京受降過(guò)程并不復(fù)雜,卻聚焦了全體中國(guó)人的目光。在現(xiàn)場(chǎng)的王楚英說(shuō),9月9日8時(shí)52分,懸掛于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四盞水銀燈驟亮,何應(yīng)欽等中方代表步入會(huì)場(chǎng),全場(chǎng)來(lái)賓肅立,攝影記者頻頻按動(dòng)快門。8時(shí)58分,又一陣閃光燈嚓嚓作響,日軍簽降代表岡村寧次等自禮堂正門入場(chǎng)。他們成縱隊(duì)走到受降桌前變?yōu)闄M隊(duì),岡村寧次居中,脫帽向何應(yīng)欽等中國(guó)將領(lǐng)鞠躬致敬。
上午9時(shí)整,何應(yīng)欽主持中國(guó)戰(zhàn)區(qū)受降正式典禮。岡村寧次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侵華日軍128萬(wàn)余人向中國(guó)投降。
簽降過(guò)程中有一個(gè)細(xì)節(jié),讓王楚英難忘:岡村寧次提起毛筆的時(shí)候,小林淺三郎在旁邊磨墨,不可一世的囂張之氣全無(wú)。岡村寧次突然盯著毛筆發(fā)怔,手也微微顫抖。可能為了掩飾緊張,他捏了捏筆頭的羊毫,恭恭敬敬簽下自己的名字,伸手解上衣口袋的扣子,取出方章蘸了印泥,哆哆嗦嗦地蓋上。沒(méi)想到章蓋歪了,岡村寧次面露尷尬,站起身恭立。小林淺三郎呈遞投降書,他朝長(zhǎng)桌對(duì)面的何應(yīng)欽點(diǎn)頭。王楚英分析,岡村寧次一是表示致歉,二是表示日軍就此投降。
日軍受降儀式結(jié)束,何應(yīng)欽令日軍代表退場(chǎng)。何應(yīng)欽代表中國(guó)政府發(fā)表廣播講話:“中國(guó)戰(zhàn)區(qū)日軍投降簽字已于本日上午9時(shí)在南京順利完成。這是中國(guó)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gè)日子,這是八年抗戰(zhàn)艱苦奮斗的結(jié)果!”
潘庭槐,93歲,時(shí)任警衛(wèi)營(yíng)八連的少尉排長(zhǎng),作為守護(hù)受降典禮會(huì)場(chǎng)的國(guó)軍憲兵,參與了日軍投降簽字儀式的全過(guò)程。
呈遞《日本投降書》后,岡村寧次率日軍投降代表離場(chǎng),神色黯然地向大門走去,就從站在門框旁的潘庭槐身邊走過(guò)。潘庭槐說(shuō):“當(dāng)岡村寧次走近我身邊時(shí),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光頭低了下來(lái),都不敢正眼看我們。”
咔嚓。這一幕,恰好被一名在場(chǎng)的攝影記者拍下了。在黑白照片中,岡村寧次等日本投降代表提著軍帽,低著頭走過(guò),掩飾不住沮喪之氣。身著憲兵服的潘庭槐則在一旁,昂首挺胸,精神氣十足,筆直地持槍站立著。
失敗的將軍,勝利的士兵,就此在鏡頭中定格。
陳堅(jiān)告訴我說(shuō):“表現(xiàn)這7個(gè)侵華日軍簽降代表,我用的是真實(shí)的歷史情節(jié),通過(guò)行鞠躬禮刻畫他們的神態(tài)。他們的心情很復(fù)雜,天皇詔命不能不服從,一方面出于世界反法西斯正義力量的壓力,拱手遞上投降書。另一方面,日軍在中國(guó)還有相當(dāng)?shù)能娛聦?shí)力,一種不服輸不認(rèn)罪的心態(tài),止不住地流露在臉上。”
按事前擬定的南京受降儀式程序,規(guī)定日方投降代表,前后要向何應(yīng)欽行三次禮,到會(huì)場(chǎng)時(shí)、呈交投降書時(shí)與退場(chǎng)時(shí)。因此,油畫中表現(xiàn)的日軍將領(lǐng)的動(dòng)作特征,雖然高度濃縮,卻是有根有據(jù),準(zhǔn)確而又神似。
其實(shí),岡村寧次等日軍將領(lǐng)在中國(guó)戰(zhàn)區(qū)投降,內(nèi)心十分糾結(jié)。繼日本天皇發(fā)布投降詔書后,8月16日,日本大本營(yíng)電令岡村寧次“立即停止戰(zhàn)斗行動(dòng)”,岡村寧次當(dāng)夜下令“即時(shí)停止戰(zhàn)斗行動(dòng)”。然而,17日,岡村寧次雖然不敢違命,但向日本大本營(yíng)參謀總長(zhǎng)梅津發(fā)電請(qǐng)示,遺恨未消地直言不諱:“派遣軍擁有百萬(wàn)大軍,且連戰(zhàn)連勝。在國(guó)家間之戰(zhàn)爭(zhēng)上雖已失敗,但在作戰(zhàn)上仍居于壓倒性勝利之地位,以如此優(yōu)勢(shì)之軍隊(duì)而由軟弱之重慶軍解除武裝,實(shí)為不應(yīng)有之事……”
無(wú)可奈何花落去,失敗就是失敗,不服也不行。
自1895年,因中日甲午戰(zhàn)爭(zhēng)的失敗,清政府被迫簽定《馬關(guān)條約》,巨額賠款并割讓臺(tái)灣,此后的日本在軍國(guó)主義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直到發(fā)動(dòng)“九·一八事變”,搶占中國(guó)東三省,這還不滿足,又策劃“七七事變”,開(kāi)始全面侵華戰(zhàn)爭(zhēng)。日軍將領(lǐng)們?cè)袊蹋叭齻€(gè)月戰(zhàn)勝中國(guó)”,八年后卻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如果僅僅為了油畫的形式感,陳堅(jiān)可以在岡村寧次的手上添一把軍刀,但他尊重歷史,并不想漫畫似的隨意圖解,而如實(shí)畫出岡村寧次沒(méi)有帶刀,徒手向中國(guó)代表遞上簽署的日軍投降書。只不過(guò)陳堅(jiān)還是有些遺憾:那把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隨身攜帶的軍刀,本該是在這個(gè)神圣的儀式上收繳的啊!
四
太多歷史細(xì)節(jié)的碎片,在時(shí)光流逝中難以找尋了。這幅油畫對(duì)一個(gè)個(gè)細(xì)節(jié)的真實(shí)考證,幾乎到了嚴(yán)絲入縫的苛刻程度。受降會(huì)場(chǎng)上有聯(lián)合國(guó)五十二個(gè)國(guó)家的國(guó)旗,是按字母排列的,他求證這些國(guó)旗,并且是1945年時(shí)的國(guó)旗樣式,然后買來(lái)白布,畫出二十多面國(guó)旗,縮小排列成懸掛狀,成為繪畫取樣的實(shí)物標(biāo)本。
從許多黑白的老照片上,陳堅(jiān)有他的獨(dú)特發(fā)現(xiàn)。日軍將官的領(lǐng)章釘法與中方將官不同,將星不在領(lǐng)章正中,而是從邊沿釘起,即使一顆星也在一側(cè);日本軍官袖口都有軍銜標(biāo)志;日軍參謀到參謀長(zhǎng)佩有授帶,軍事主官卻沒(méi)有,而且不管多高的職務(wù)。日本陸軍皮靴有模糊的“馬刺”,包括高級(jí)將領(lǐng),這是為什么?陳堅(jiān)在海量資料中研究日軍皮靴的沿革,終于,在家中收藏的《愛(ài)新覺(jué)羅·溥儀畫傳》畫冊(cè)中得到佐證:日本雖屬軸心國(guó),但與德國(guó)相比,軍隊(duì)機(jī)械化程度并不高、封建軍國(guó)主義色彩甚濃,陸軍高級(jí)將領(lǐng)在戰(zhàn)場(chǎng)上普遍騎馬行軍,因此皮靴鑲有“馬刺”。
軍人在室內(nèi)是脫帽的,中日雙方將領(lǐng)均如此。陳堅(jiān)先在投降桌與受降桌上都畫了軍帽。后來(lái)他發(fā)現(xiàn),岡村寧次簽字蓋章后,旁邊的參謀長(zhǎng)小林淺三郎拿起,向何應(yīng)欽遞交投降書,照片上左側(cè)軍服皺褶不對(duì)勁,好像鼓出來(lái)一塊東西。他仔細(xì)研究,原來(lái)小林淺三郎雙手抬起時(shí),腋下夾著他的軍帽,而他坐著時(shí),軍帽是拿在手里的。陳堅(jiān)恍然大悟,難怪不少日本軍官坐在桌前的照片上,不見(jiàn)軍帽呢。陳堅(jiān)再畫軍帽,中方將領(lǐng)的軍帽在桌上,日方將領(lǐng)的軍帽只有一頂,是岡村寧次的,他要簽字蓋章,其他日將的軍帽都應(yīng)該在手上,這才符合歷史的真實(shí)。
中國(guó)軍人的服飾、領(lǐng)章、“中正劍”的佩掛、受降時(shí)特有的臂章標(biāo)記,陳堅(jiān)都做到有根有據(jù),絕不草率。他親手將它們制成道具,放在不同的光線中,供繪制時(shí)參照描摹。他的努力超出常人,他的表達(dá)也就超出了一般。
陳堅(jiān)感慨地告訴我:“我越研究,越發(fā)現(xiàn),有些反映那段時(shí)期的藝術(shù)作品,特別是影視作品,真實(shí)性的形象表述的誤差是那樣之大。有的甚至只憑想像,很不嚴(yán)謹(jǐn)!我鄙視唯利是圖、歪曲歷史的態(tài)度,太不負(fù)責(zé)任了!”
在史料記載和紀(jì)實(shí)文學(xué)中,受降儀式上的投降席和受降席是個(gè)十分簡(jiǎn)單的概念,而在陳堅(jiān)的眼中,它們的形狀和顏色,都不可以隨意涂抹,要給后人一個(gè)真實(shí)的記錄。他對(duì)照當(dāng)時(shí)的幾張照片,得出結(jié)論,投降席和受降席的大小是不同的。日軍將領(lǐng)面前的投降席,是三張長(zhǎng)條桌拼成的,桌面的寬度很窄。中國(guó)將領(lǐng)面前的受降席,則比投降席大一倍,是兩張辦公桌拼成的。日軍將領(lǐng)坐的是帆布?jí)|的高背木椅,中國(guó)將領(lǐng)坐的是帶扶手的太師椅,扶手上雕有回紋型的曲線花紋。
有專家考證,在研究南京受降會(huì)場(chǎng)的布置時(shí),何應(yīng)欽竟提出過(guò)“圓桌方案”,投降者和受降者圍在一個(gè)圓桌開(kāi)會(huì),叫盟軍將領(lǐng)大為驚嘆:太離譜了,這像什么話!美國(guó)顧問(wèn)反應(yīng)最強(qiáng)烈,如此則受降者與投降者豈不皆處于平等地位?現(xiàn)場(chǎng)才改為長(zhǎng)方形,受降者在上,投降者在下,對(duì)立而坐,不得造次。
聽(tīng)說(shuō)某博物院陳列有投降席和受降席的文物與復(fù)制品,包括桌子和椅子,陳堅(jiān)專門去看,畫了速寫。老照片上的投降席和受降席包有“三色布”,深淺不一,博物院復(fù)制時(shí)做成了藍(lán)色、白色、藍(lán)色。陳堅(jiān)認(rèn)為不對(duì),黑白照片的“三色布”有三種色差,不可能有兩種同樣的顏色。他參照會(huì)場(chǎng)立柱等處的色彩搭配,斷定“三色布”應(yīng)遵照中華民國(guó)的國(guó)旗色:藍(lán)色、白色、紅色,不能想當(dāng)然定顏色。他認(rèn)定,藍(lán)色、白色、紅色應(yīng)該是當(dāng)年受降儀式會(huì)場(chǎng)布置運(yùn)用的基本色。
后來(lái),陳堅(jiān)參觀某著名的紀(jì)念館,那里復(fù)制了日軍南京受降儀式的現(xiàn)場(chǎng)情景,受降席和投降席的桌布顏色,也存在同樣的錯(cuò)誤,陳堅(jiān)便對(duì)講解員提出了異議。那位講解員進(jìn)到辦公室,向一個(gè)領(lǐng)導(dǎo)模樣的人轉(zhuǎn)達(dá)。那人出來(lái)聽(tīng)完陳堅(jiān)的說(shuō)法,提出了疑問(wèn):“您真的研究過(guò)?國(guó)民黨怎么會(huì)有紅色?”在一個(gè)研究歷史的紀(jì)念館,本該專業(yè)的人士提出這樣一個(gè)非專業(yè)的問(wèn)題,令陳堅(jiān)哭笑不得。
在一次紀(jì)念抗戰(zhàn)的活動(dòng)中,陳堅(jiān)結(jié)識(shí)了親歷南京受降的南京政協(xié)委員、九旬高齡的王楚英老人。王楚英時(shí)為新六軍14師作戰(zhàn)科長(zhǎng),擔(dān)任史迪威將軍的英文翻譯官,是參與受降儀式的中方軍官。老人應(yīng)邀到南京軍區(qū)大禮堂側(cè)樓的陳堅(jiān)畫室,仔細(xì)觀看他的畫稿,肯定了陳堅(jiān)的創(chuàng)作構(gòu)思,只提出在會(huì)場(chǎng)守衛(wèi)的新六軍士兵的美式裝備,背囊上有一條卷起的軍毯。陳堅(jiān)找來(lái)一條軍毯,反復(fù)折疊,終于逼真地添畫上去。老人的意見(jiàn)加強(qiáng)了中國(guó)軍人的威武形象,陳堅(jiān)非常感激。
這幅全景式的史詩(shī)性畫作,融入了畫家的無(wú)數(shù)心血。陳堅(jiān)說(shuō),他的畫室就在他所表現(xiàn)的歷史場(chǎng)景的遺址,好像命運(yùn)選定了這個(gè)作者就是我!陳堅(jiān)以《拿破侖加冕》為例,法國(guó)著名畫家大衛(wèi)的名作,讓他在巴黎羅浮宮流連忘返。畫中人物真人那么大,在沒(méi)有照相機(jī)的年代留下了一個(gè)偉大的歷史瞬間。
“一位畫家朋友曾勸我,把人物畫到接近真人的比例。遺憾哪!我沒(méi)有那樣大的畫室作畫,要不然,就是中國(guó)的《拿破侖加冕》了!”
五
2005年,中國(guó)抗日戰(zhàn)爭(zhēng)勝利六十周年之際,這幅描寫侵華日軍投降儀式的油畫巨作《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shí)·南京》公開(kāi)展出,轟動(dòng)一時(shí)。中央電視臺(tái)《東方之子》欄目對(duì)作者專題訪問(wèn),北京各家全國(guó)媒體作了報(bào)道。在第十屆全國(guó)美術(shù)展覽上,它以高票榮獲本屆美展油畫金獎(jiǎng)。畫家以氣勢(shì)恢宏的整體構(gòu)架、細(xì)膩嫻熟的藝術(shù)技巧和令人驚嘆的真實(shí)筆觸,將歷史的瞬間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
在北京中國(guó)人民抗日戰(zhàn)爭(zhēng)紀(jì)念館,陳列著日軍的罪行與抗戰(zhàn)的壯舉,《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shí)·南京》作為壓軸之作懸掛在大廳。成千上萬(wàn)的中外觀眾,分享了彪炳于史冊(cè)的這一重要節(jié)點(diǎn)。許多抗戰(zhàn)老兵在油畫前流連忘返,激動(dòng)不已。經(jīng)歷抗戰(zhàn)的臺(tái)灣退役將軍流下激動(dòng)的淚水,托人表達(dá)對(duì)于作者的敬意。
陳堅(jiān)告訴我:“中國(guó)人民以三千五百萬(wàn)人的生命的代價(jià),換來(lái)了那一天的勝利。勝利來(lái)之不易,我感謝這一光輝瞬間給我心靈的極大震撼!”是的,每個(gè)看過(guò)畫作的人都會(huì)感到震撼,因?yàn)楫嫾业恼鸷硨儆谝粋€(gè)不屈的民族。
若干年來(lái),對(duì)于中國(guó)的突發(fā)事件,日本媒體記者總是頻頻追蹤,不愿意有任何的疏漏。然而,對(duì)于這樣一幅在中國(guó)廣為報(bào)道的油畫巨作,連同油畫所記錄的南京受降儀式,卻被日本某些人有意識(shí)地忽視甚至漠視了。
直到2009年,日本學(xué)者纐纈厚教授出版了專著《何謂中日戰(zhàn)爭(zhēng)》,封面印上了油畫《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shí)·南京》的照片。纐纈厚教授在書中發(fā)問(wèn):“陳堅(jiān)的油畫以及上傳到網(wǎng)上的有關(guān)照片,像這樣的歷史史料,迫使我們必須重新考慮和確認(rèn),日本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戰(zhàn)敗以至投降的呢?”
64歲的纐纈厚教授的發(fā)問(wèn)是尖銳的,直指日本的良知,纐纈厚教授是日本國(guó)立山口大學(xué)副校長(zhǎng),還擔(dān)任日本東亞歷史文化學(xu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日本和平學(xué)會(huì)理事等職。當(dāng)日本官方不愿意承認(rèn)侵略事實(shí),恢復(fù)軍國(guó)主義的勢(shì)力氣焰囂張的時(shí)候,他頂住壓力,孜孜不倦地對(duì)日本軍事政治的發(fā)展和演變深透研究。
纐纈厚教授在他的書中,專門列了一章:日本“戰(zhàn)敗”是敗給了誰(shuí)?他從這幅中國(guó)油畫說(shuō)起:“1945年9月9日在中國(guó)南京的投降儀式雖然是確鑿的歷史事實(shí),但是這張油畫所展示的向中國(guó)投降的簽字儀式的現(xiàn)場(chǎng)照片,很長(zhǎng)時(shí)間在日本人中間并沒(méi)有被公開(kāi)。這是出于何種意圖呢?還是資料遲緩?fù)涎幽兀俊?/p>
纐纈厚教授寫道:“有一點(diǎn)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戰(zhàn)后許多日本人并非想從正面來(lái)面對(duì)這幅畫所展現(xiàn)的事實(shí),即日本向中國(guó)軍隊(duì)投降的這一歷史事實(shí)。給日本人留下強(qiáng)烈印象的,只有在美國(guó)戰(zhàn)艦密蘇里號(hào)上的投降簽字儀式的場(chǎng)景,而在中國(guó)南京的投降儀式,在亞洲各地舉行的投降儀式的場(chǎng)景,被模糊淡化了。
“與此相對(duì),在中國(guó)的投降簽字儀式,從油畫中可以看出整體上籠罩在一種凜然的氣氛中,令人感到某種莊嚴(yán)。被迫遭受戰(zhàn)爭(zhēng)、蒙受巨大災(zāi)難的中國(guó)方面的要人,以及注視這一場(chǎng)面的中國(guó)民眾,表現(xiàn)出毅然決然的態(tài)度。
“戰(zhàn)后日本人不愿意承認(rèn)敗給中國(guó),其理由是多種多樣的。在此,通過(guò)對(duì)近代日本國(guó)家形成時(shí)期的中日關(guān)系史進(jìn)行分析,再次來(lái)確認(rèn)一下其中所表露的日本人對(duì)中國(guó)的觀念。我認(rèn)為,不承認(rèn)和不愿意承認(rèn)敗給中國(guó),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僅是信息量的多少及其質(zhì)量高低的問(wèn)題,更主要的是大多數(shù)的日本人所固有的對(duì)于中國(guó)的認(rèn)識(shí),或者是在近代中日關(guān)系史方面存在的錯(cuò)誤的認(rèn)識(shí)。”
不愿承認(rèn)敗給中國(guó),纐纈厚教授點(diǎn)出了問(wèn)題的實(shí)質(zhì)!
2010年,中國(guó)人民抗日戰(zhàn)爭(zhēng)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zhēng)勝利65周年。在中國(guó)各地日軍侵華舊址考察過(guò)的纐纈厚教授,將他的新作《我們的戰(zhàn)爭(zhēng)責(zé)任:歷史檢討與現(xiàn)實(shí)省思》一書,交中國(guó)學(xué)者翻譯成中文版推出。這本書在日本的原名是《我們的戰(zhàn)爭(zhēng)責(zé)任:昭和初期二十年和平成時(shí)期二十年的歷史考察》。
其實(shí),身為日本學(xué)者,纐纈厚教授是真愛(ài)日本的。在記者采訪他時(shí),他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我父親有三個(gè)哥哥,都是在對(duì)華戰(zhàn)爭(zhēng)中戰(zhàn)死的。父親臨終前對(duì)我說(shuō),如果戰(zhàn)前就有《和平憲法》第九條,我們就不會(huì)失去我們的親人了。”纐纈厚教授表示,自己失去親人十分悲傷,想到中國(guó)等亞洲受害國(guó)家的人民,在親人被殺害時(shí)會(huì)感到多么深切的悲痛啊!為了今后不再有家人因?yàn)閼?zhàn)爭(zhēng)而死,為了日本不再成為加害國(guó)或受害國(guó),我有責(zé)任站出來(lái)維護(hù)《和平憲法》第九條!
對(duì)于日本有人試圖突破《和平憲法》,纐纈厚教授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他說(shuō),《和平憲法》第九條明確規(guī)定,“放棄戰(zhàn)爭(zhēng),戰(zhàn)爭(zhēng)力量及交戰(zhàn)權(quán)的否認(rèn)”,顯示日本政府不再對(duì)中國(guó)等亞洲國(guó)家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zhēng)的決心,一旦被修改,日本就獲得了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zhēng)的權(quán)利。“戰(zhàn)爭(zhēng)責(zé)任是超越國(guó)境和時(shí)效的,這意味著只有向所有的受害國(guó)道歉,并且不限定時(shí)間的終止點(diǎn),這才算是日本真正地承擔(dān)了戰(zhàn)爭(zhēng)責(zé)任。”
纐纈厚教授富有正義感的聲音,在日本常常被屏蔽,他把油畫《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shí)·南京》推薦給日本民眾,就是告訴人們:這是一段無(wú)法回避的歷史真相,不愿承認(rèn)它,絕不等于它就不存在。
1945年9月9日,日軍投降日,中國(guó)勝利日。它仿佛世紀(jì)警鐘,將一個(gè)血與火的時(shí)代的思考化為永恒,久久回蕩在歲月的長(zhǎng)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