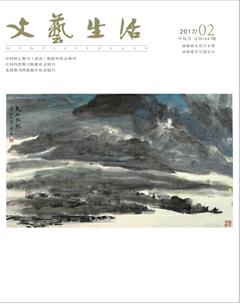淺析廣告營銷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及發展策略
黑霞
摘 要:企業和產品銷售方對廣告營銷這一方面的發展策略研究越來越重視,對產品廣告營銷的投入也越來越大,人們的生活中對產品各式各樣的廣告營銷手段也愈加普遍。本文就是針對這一社會現象,結合自己所學知識,從營銷策略角度入手,全面分析了廣告營銷對現在人們生活的具體影響,深入剖析產生影響的途徑和對產品消費者的思維
目前,我國經濟和科學水平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人們的消費觀念也在隨著經濟基礎的不斷增加在不停的發生著改變。現在,大多數消費者在消費時不僅僅關注產品的性價比,還追求產品的外觀設計和產品的文化底蘊,以及產品的綜合社會價值。這些都使得廣告營銷在企業整體營銷手段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廣告營銷是現在大多數企業擴大銷售規模,擴展營銷市場以及增加企業利潤的重要手段。廣告營銷在現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出現頻率,已經形成了一種常態化的生活現象。因此,廣告營銷對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同時隨著廣告營銷行業的不斷發展,廣告營銷的模式愈加多樣化,對人們的思維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影響。一個好的廣告營銷策略,能夠快速且顯著的提高對應產品的銷量。因此,要想從根源上改進產品的廣告營銷模式,就必須先從了解廣告營銷對人們生活的具體影響入手。
一、廣告營銷的相關概述
(一)廣告營銷的定義
廣告營銷的定義可以分開去解讀。首先是“廣告”二字,廣告顧名思義,就是把產品或品牌信息廣而告之,通過人為的多方面宣傳擴大產品信息的傳播范圍,提高產品信息的傳播速度,進而提高企業品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而“營銷”二字,可以理解為通過營造適合產品銷售的大環境來達到銷售產品的目的。結合起來考慮,廣告營銷就是通過人為活動,在多個渠道和環境中采用多樣化的宣傳手段擴大產品信息的傳播效率,提高企業品牌影響力。然后依此為主要手段,營造一種更加適合產品銷售的大環境,進而提高產品銷量,增加企業利潤。
(二)廣告營銷的作用
廣告營銷是各種營銷手段中提升產品知名度最顯著的營銷手段。而當下,我國伴隨著城鎮化速度的加快,很多鄉村的廣大消費群體也逐漸適應了城市化的快節奏生活方式,人們的消費觀念也在不斷的發生著變化。而這種快節奏的消費習慣就會使人們在挑選產品時更加關注產品的知名度,和宣傳出來的外在的文化底蘊和實用性。因此,廣告效果的好壞會快速的影響產品的整體營銷環境,進而影響產品的整體銷量。因此做好廣告營銷對企業產品銷售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二、廣告營銷對人們生活影響的理論支撐
(一)馬斯洛需求理論
馬洛斯需求理論認為,人們內心的種種需求可以按照需求原因和需求強烈層次分為五類:生理的需求、安全感的需求、情感和歸屬感的需求、人格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把這種需求理論用到廣告營銷中來,人們在購買產品時,也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某一項需求。而廣告要做的就是根據產品能夠滿足的需求點的不同,把這種心理和精神上的訴求更加直接的引導出來。依據馬斯洛需求理論分析,每種需求的表現方式都不一樣,人們對于五種需求的訴求強烈程度也不一樣,因此在實際的產品廣告營銷設計中也應該通過不同的方式體現,不同的產品滿足不同需求的功能。
(二)消費者群體意識
消費者群體是有若該共同消費意愿的消費者組成的消費意識共同體。具有共同消費意愿和消費需求以及心理或生理要求的消費者,在購買行為、消費習慣以及消費心理方面都有許多一樣的地方。群體意識是指有這種消費群體不斷進行共同的消費行為而確立的行為慣性和行為標準。這些行為標準對其后來的同類型的消費行為有這非常具體的影響。因此,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年齡、不同信仰等不同因素的消費者都可能對某一類產品形成不同的消費群體。因此,企業在進行產品廣告營銷設計時也應該充分考慮消費對象的其他群體因素,有針對性的設計廣告營銷策略。
(三)廣告鏡像理論
廣告能夠非常直白且具體的反應出產品的特征,同時也能間接反應出與廣告產品相關的周邊其他環境因素的特點。說真實化的大眾化的廣告是一個時期的社會記錄片也毫不夸張。而且廣告一般是通過圖像文學符號來達成傳播目的的,這些符號都相較于其他的時代符號更容易被人們說關注并記住。因此,大部分的廣告都有很強的潛在誘導力,同時大多數廣告都能讓人在虛擬化的印象中自然營造出一種理想化的生活狀態,能夠如鏡像一般表達出人們生活中多種多樣的潛在欲望和需求。因此,廣告也是一個時期大眾形象和生活方式的一種多層次體現。
三、廣告營銷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分析
(一)廣告營銷對人們生活影響的綜述
1.對行為習慣的影響
依據馬斯洛需求理論,大多數廣告形態的制定都是根據人們對產品的實際需求來量身訂制的。在對這些廣告進行大范圍宣傳時,能夠從心理訴求層面影響大多數消費者的行為習慣。其中對人們飲食和休閑的行為方式的影響最大,而對學習習慣的影響最小。這是因為人們對飲食的需求是最直接也最常出現的一種心理訴求,而對學習這種自我實現的需求的強烈程度相較于前者較弱。實際上,現在廣告已經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據人們對事物的自主需求,進行行為上引導,潛移默化的改變人們的行為習慣。
2.對不同年齡段人們的影響
依據消費者群體意識理論,企業在設計產品廣告時,對各個年齡段的消費群體所設計的廣告樣式也各不相同。整體而言,廣告營銷行為對年輕群體的生活習慣影響最為明顯,對年齡相對較大的消費群體的生活習慣影響則不是很顯著。這是因為,年輕的消費群體的消費觀念通常都比較多變,容易受到外來宣傳的影響,同時年輕人好奇心重,思維活躍,接受廣告營銷的機會也相對較多。而年齡較大的消費群體由于其影響消費觀念的因素過于復雜,形成的消費習慣也很難在發生改變,所以很難從影響消費行為為途徑去影響其生活習慣。
3.對不同區域人們的影響
就地區因素而言,不同地區的人們在生活習慣和消費觀念方面都有很大不同。總體來說,廣告營銷對城市居民的生活習慣影響更加顯著,而對鄉村居民的生活習慣影響相對較小。這是因為,城市居民在原有生活方式上習慣了快節奏的生活,同時見聞相對也較多一些,接觸廣告營銷的機會也較多,更加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影響,同時在消費時也更關注產品的廣告水平。而鄉村居民由于生活環境不同,在消費時更加關注產品的實用性和實際價格,對廣告內容的信任度本就不高,再加上大多數鄉村居民對廣告營銷的接觸機會就沒有城市居民多,因此在生活習慣方面很少受到廣告營銷的影響。
(二)廣告營銷對人們深入思維的影響
1.對價值觀的影響
價值觀是一種人們對各種事物包括自身的價值定位的一種簡稱,它是建立在人們對世界、社會人與人和人與事物的關系的內在認知的基礎上的。價值觀能夠直接影響人們對某人或某事的態度和心理傾向,同樣人們對某一事物的心理傾向和實際態度,也能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整體價值觀的形成和改變。特別是如今在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下,廣告展現出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消費者的價值觀念和生活習慣也存在廣告的影響下不斷發生變化:由“節儉觀”走向“享受觀”、由“權利觀”走向“財富觀”,由“大眾觀”走向“個性觀”。現如今,人們生活受廣告營銷的影響越來越顯著,人們的很多行為習慣都在因為廣告宣傳的鏡像效應而發生著潛移默化的改變,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人們原有價值觀的改變。
2.對審美觀的影響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人們接觸外來產品廣告營銷的機會越來越多,這些承載著西方文化的廣告營銷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人們對西方或其他國家文化內涵的好奇和向往。而這些人們心中的心理暗示又逐漸的影響人們去了解西方或其他國家的文化及其審美標準,然后再直接的這些外來文化的審美元素與我國原有的審美結合起來,形成新的審美標準。以前消費者的審美追求都是單一化、簡單化的,傳統的審美趣味也具有一定的規范性,消費者對于美只是一種自發追求。而如今,隨著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轉型,廣告對于消費者生活觀念的影響越來越大,單一的審美觀漸漸被多元化的審美觀所取代,消費者在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都印上了時尚、個性、自我的標記。
3.對生活意義的影響
以前在我國,制約廣告營銷產業發展的是媒體科技的發展,而現在隨著我國科學技術和媒體宣傳事業的不斷發展,廣告營銷的宣傳渠道越來越多樣化,廣告的宣傳力度和廣告覆蓋度也在隨著宣傳手段的更加現代化而變的更加形象、更加感性。再加上現在大部分消費者的消費理念的變化,人們在選擇產品進行消費時,更加注重突出個性,展現風格。而現在的這些快節奏的網絡廣告和視頻創意廣告更能符合人們對生活意義的個性化體現。
4.對生活環境的影響
現在很多廣告在設計過程中為了達到需要的宣傳效果,大多都會結合宣傳地區的實際生活環境,進行一些更加契合當地人現實生活的廣告宣傳。這些廣告宣傳都能影響人們對周邊生活環境的感受,繼而引起人們整體生活環境的改變。同時,由于我國在廣告宣傳方面沒有明確的保護環境的相關規范,很多不法企業或廣告商為了達到自私的廣告宣傳目的,肆意的破壞環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環境污染。
5.對消費習慣的影響
現在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逐漸加快,大多數消費者都把廣告信息作為評價產品品質的主要信息來源。因此,廣告營銷內容對于人們的消費行為影響愈加顯著。同時由于消費群體特殊的消費行為影響,通過適當的廣告宣傳能夠很快的在一些消費群體中建立一定的品牌基礎,繼而影響整個消費群體的消費習慣。當代大多數消費者在進行品牌和產品的選擇時都會或多或少的受周邊人或事的影響,其中就包括媒體類廣告營銷的直接影響,以及消費群體里其他消費者的言行影響。這些都能看做是廣告營銷對消費者消費行為的直接或間接影響。
四、企業利用廣告營銷的相應策略
(一)認清廣告營銷與人們生活影響的關系
要想通過廣告營銷提高企業的產品銷量,提升企業的品牌競爭力。首先,要搞清楚企業產品自身的特征和功能,明確產品能夠滿足人們的哪方面的需求,找到消費者的需求點。其次,透過共有需求點來尋找合理的消費群體。再來,有針對性的根據產品主要面向的消費群體特點進行廣告營銷策略的具體規劃。最后,要根據所面向的消費群體現實生活的變化規律來時刻調整廣告宣傳策略。只有這樣搞清楚廣告營銷與人們生活的關系,及時的調整和優化廣告營銷策略,才能使企業的廣告營銷一直保持高效。
(二)提高廣告文化蘊含程度
企業在進行廣告設計時,應該在注重產品信息宣傳的基礎上同時兼顧企業文化的展示。讓消費者在接受廣告宣傳的產品信息的同時,也能對企業文化內涵有一個簡單的了解,間接的提高了廣告的宣傳力度和企業的知名度。同時,還可以通過一些有創意和有文化氣息的設計風格來進行廣告的設計,比如把廣告的環境背景和歷史背景設計的更加富有詩意或更加有歷史的厚重氣息。這些廣告設計不僅能提高消費者對廣告的記憶強度,同時還能直接提升人們對企業品牌形象的關注度。
(三)積極使用現代市場營銷策略
企業和消費者之間進行雙向溝通、互相交流是現代市場營銷活動的必備手段,通過相互之間的溝通和交流來使消費者大方的放手消費。因此,對于企業來說,應該重視對市場營銷模式的創新,以及重視對市場營銷人員整體素質的培養。積極的運用現代化的市場營銷手段,能夠更加有效的廣告營銷營造的品牌優勢積極的運用在市場營銷方面,提高企業的產品銷量,提升企業整體產品利潤。
(四)使用互聯網渠道來進行廣告推廣
對于廣告營銷策略的設計也應緊跟時代的步伐,對互聯網這一新興媒體平臺也應該充分的考慮在內。尤其是,現在人們對互聯網平臺購物應用的愈加普及,大多數年輕消費者都把網絡消費作為自己的主要消費渠道,同時也把互聯網作為獲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介于這種情況,筆者認為,大部分企業也應積極的擴展互聯網營銷渠道,同時重視與之相匹配的互聯網廣告宣傳。適當的加大對互聯網廣告營銷的資金投入,提高企業產品在互聯網銷售平臺的競爭力。
(五)保證廣告本身的品質
企業一般通過各種廣告來在消費者心里植入印象,從而推動消費者對其產品的購買欲。優秀的廣告能夠傳達信息、服務社會和人民。優秀的廣告必須清晰而又形象,與消費者的生活相關,符合消費者的生活環境,能夠使消費者感受到關懷,和企業的品牌理念相符。只有這樣的廣告能夠更容易的建立品牌形象,同時也更容易得到消費者的贊同和認可,從而推動企業的發展壯大。保持廣告的綜合品質,及時調整廣告的宣傳手段,提高廣告的品牌符合,對于一個企業來說必不可少。否則,很難得到消費者的認可,企業也就很難發展壯大。
五、結語
本文綜合分析了我國現行的廣告營銷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深入研究了廣告營銷過程中對消費者具體的思維影響。然后結合以上研究所得,根據我國近幾年廣告營銷的發展趨勢,提出了自己對產品廣告營銷發展策略的一些建議。筆者認為在未來的廣告營銷發展領域內,網絡廣告營銷的地位一定會越來越重要,同時消費者對于廣告本身的質量要求也會越來越高。因此,企業應該從積極擴展網絡營銷市場以及提供產品廣告本身的文化內涵為突破口,依次來提高產品的廣告營銷效果。希望本文的研究內容能為一些企業在設計產品廣告營銷策略時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
參考文獻:
[1]王家卓,劉奕群,馬少平,張敏.基于用戶行為的競價廣告效果分析[J].計算機研究與發展,2011(01).
[2]張潔瑩.新媒介時代廣告營銷模式的創新——以力士廣告片為例[J].新聞世界,2012(14).
[3]黃倩,蘇傲,任逸杰.微博營銷形式探究——以代表性行業為例[J]. 藝術科技,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