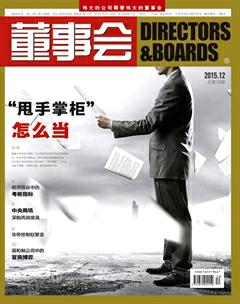給場外配資一條生路
梅慎實+王博
場外配資本身并不必然是違法的,它存在的問題可以通過制定、修改相關法律法規加以解決
今年上半年中國股市經歷了一次過山車般的行情,此間“股票場外配資”被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股市的跌幅。
股票場外配資是指個人投資者不通過證券公司進行、向配資公司借款用于股票投資的行為。其典型運作方式為:配資公司從銀行處取得借款,再將這些借款以1:3或1:5等比例借給股票投資者。但是投資者并不能直接在自己的賬戶中使用這筆資金,配資公司會將自己控制的賬戶交給投資者使用。這些賬戶或者是配資公司以他人名義開設,或者是使用電子系統劃分的若干子賬戶。配資公司的收入主要來自借入與借出資金的利差。為了保證自身資金的安全,配資公司通常會對賬戶設立預警線和強平線。當賬戶資金跌破強平線,則配資公司會將該賬戶強行平倉。在股市大跌的行情之下,很多從場外配資處融得資金的投資者都被配資公司強行平倉,血本無歸。
場外配資作為新生事物,我們應當如何區分其中的法律關系,其中蘊含著什么風險,我們應該如何對其監管?而在此之前,法院如何對場外配資糾紛進行審理?配資系統的提供者是否應受處罰?
多重法律風險
場外配資因其高杠桿率備受風險偏好型投資者的青睞。在股市上漲行情中,場外配資可以為投資者帶來可觀收益。不過一旦股市開始下跌,投資者為了防止被強平,會更快將股票拋售,從而加劇股市動蕩。這是場外配資可能造成的金融風險,同時它存在著相當的法律風險,包括配資公司可能因為客戶資金的損失而存在對銀行的違約風險,公司與投資者因共用賬戶而存在侵吞挪用投資者資金的風險。
此外,場外配資違反證券交易實名制。我國《證券法》第八十條規定: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賬戶從事證券交易;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證券賬戶。
事實上,自2015年6月以來證監會一直在進行場外配資的清理工作。7月12日證監會發布《關于清理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見》,要求證券公司和信息系統服務提供商嚴格落實賬戶實名制,并且要求信息系統服務提供商不得增加新客戶。截至11月6日,證券公司已基本完成相關清理工作,共清理5754個場外配資賬戶,其中12%的賬戶采用銷戶方式清理,其他賬戶均采用合法合規方式承接。目前,存量傘形信托的子賬戶的買入賣出功能均已關閉,投資者無法使用子賬戶進行股票買賣。
經過清理,場外配資基本已經成為了過去式,但場外配資是有客觀的市場需求的。現行融資融券業務的門檻較高,阻擋了許多風險偏好型的投資者,他們只能從場外市場尋求融資。因此,本輪清理結束之后我們要反思,如何構建場外配資的法律關系從而規避上述風險?目前法院應如何處理相應糾紛?提供系統的公司是否應受到行政處罰?
賬戶質押最適合
為了化解以上風險,我們需要關注的是配資公司自身的資質、賬戶資金安全以及證券實名制方面的制度。
為了防止配資公司對銀行違約,不妨在將來的立法中規定配資公司的資金與配資額之間的最高比例,保證配資公司有能力清償借款,控制違約風險。同時,配資公司應當按照不同客戶的風險承受能力合理安排杠桿比例。
對于客戶資金的安全問題,最好的處理方式是借鑒融資融券采用二級賬戶管理架構,將客戶資金證券劃入第三方專門賬戶進行管理并制定嚴格的使用規則,限制配資公司對于賬戶的控制權。在該架構下,客戶的資券存入自己開設的賬戶中。客戶也是以自己的證券賬戶進行交易,符合了證券實名制的規定。但同時,客戶的資券賬戶是證券公司的客戶資券擔保賬戶的二級賬戶。
實名制方面,可以賬戶質押方式構建場外配資的法律框架。所謂賬戶質押,是指“擔保人依據與債權人的約定,將自己在銀行開立的某些或全部賬戶及賬戶中的資金以浮動擔保的方式向債權人質押,在債務人不能按時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以以賬戶中的資金優先受償,并可以接管使用此賬戶的一種擔保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賬戶質押的標的依然是賬戶內的資券。因為賬戶本身并不具有交換價值,只有賬戶內的資金和有價證券才是賬戶質押的標的。與此同時,賬戶質押具有浮動性,賬戶內的資券是變動不居的,只有當強行平倉時才會特定化。賬戶質押的獨特性在于,“它可以在賦予質權人對賬戶的最終控制權(體現為當賬戶證券凈值低于事先規定的警戒線時,質權人有權強制平倉)的同時,保留出質人對賬戶本身的使用權(即出質人可以正常使用該賬戶進行交易活動)”。賬戶質押更好地兼顧了交易效率與當事人雙方利益的平衡,是最適合場外配資的一種法律模型。
但是,賬戶質押在實體法上的地位還有待確定。我國《物權法》和《擔保法》都沒有規定賬戶質押這種擔保方式。若采嚴格的物權法定主義,這些賬戶是不可以質押的。但是最高院《<擔保法>解釋》中規定了特戶這種擔保方式。不妨將出質的特定賬戶解釋為“特戶”,因為強平線的存在,賬戶內資券的價值其實是存在最低限額的,以此限額作為“特定化”的標志也是能夠被接受的。這并不違反法律解釋的基本原理。只要雙方在合同中明確約定了賬戶質押的權利義務,那這種約定就是可接受的。
合同并非無效
除了從立法論的角度探討如何對場外配配資進行監管,還需要將眼光投入當下。實踐中,法院面臨的最重要問題,就是場外配資合同的有效性問題。
場外配資合同違反了《證券法》關于證券實名制的強制性規定。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但是不能因此判斷配資合同無效。強制性規范又分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和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是法律行政法規明確規定違反其規定會導致合同無效的規定,而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并不導致合同無效,此類規范旨在管理和處罰違反規定的行為,但并不否認該行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朱慶育教授將這種規定稱作“純粹的秩序性規定”,其目的在于“為法律行為創造公平正義的秩序環境,違反之人將招致行政乃至刑事處罰,所涉具體法律行為之效力卻不受影響”,這種分類方式也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所肯定。因此,《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中的強制性規定應當被解釋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我國《證券法》規定了非法出借證券賬戶的行政責任,這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的特征相符。更為重要的是,雖然場外配資違反了《證券法》的強制性規定,但配資合同還是雙方真實的意思表示。《證券法》對實名制的規定是為了維護證券市場的基本秩序,重點不在于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為了達到此目的,《證券法》只需要利用管理性規范對市場主體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罰即可,不需要直接宣告當事人之間的合同無效。
重罰供應商不當
11月9日至11日,證監會對恒生、銘創、同花順三家場外配資軟件供應商進行行政處罰聽證。通過三家公司開發的系統,投資者不履行實名開戶程序即可進行證券交易。三家公司在明知客戶經營方式的情況下,仍向不具有經營證券業務資質的客戶銷售系統、提供相關服務,并獲取非法收益,嚴重擾亂證券市場秩序。擬依照《證券法》一百七十九條對三家公司處以總計4.5億人民幣的罰款。筆者認為,該決定值得商榷。
三家公司只是開發和銷售證券交易系統,該業務不屬于《證券法》一百二十五條規定的證券業務類型,也很難將單純地銷售系統解釋為“其他證券業務”,故以“非法經營證券業務”進行處罰顯屬不當。況且,這些投資系統本身具有多項功能,如何使用取決于客戶,不能認為這些功能是專門為違法行為設置,進而課以三家公司過重的行政責任。
場外配資本身并不必然是違法的,它存在的問題是可以通過制定、修改相關法律法規加以解決的。上半年場外配資的活躍也說明了其巨大的市場需求。因此,場外配資應當在將來的場外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是我們的監管制度要與時俱進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