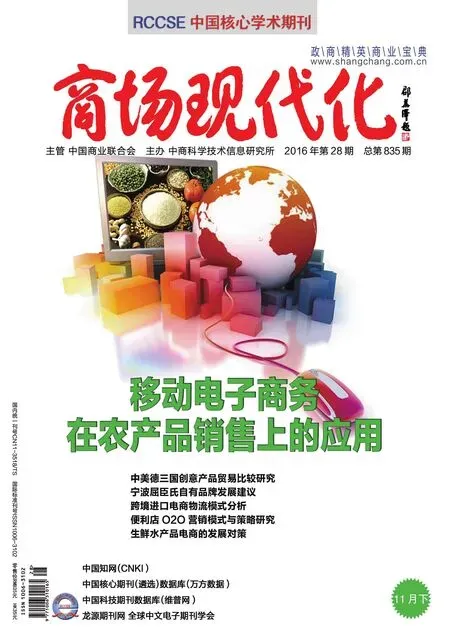商標授權中“先申請原則”與公共利益的價值博弈
葉建榮
摘 要:《商標法》規定了商標授權適用在先申請原則,然該制度的規定并非完美無缺,當先申請者申請注冊商標但未使用,而不知情的他人在審查期限內使用了該商標,同時也提出了注冊申請,并且后者對商標的使用涉及公共利益,這時就會存在先申請者的個人利益與后申請者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出現沖突,當兩種利益所體現的價值出現博弈時,需要運用價值比較的標準進行比較和權衡,即當商標的使用是涉及公共利益時,應該優先保護公共利益。除此之外,其他情形都應該適用《商標法》規定的“先申請原則”,優先保護個人利益。
關鍵詞:商標;先申請原則;公共利益
一、據以討論的案例和問題的提出
2010年11月12日創博亞太公司向商標局提出注冊“微信”商標申請,并通過初步審查。2011年1月21日騰訊公司推出微信平臺,并在同月24日向商標局提起“微信”商標注冊申請。此后,2011年11月21日第三人張新河以核準該“微信”商標注冊將對社會公共利益產生不良影響的名義對創博亞太的“微信”商標申請提出異議。2013年2月26日,商標局認為創博亞太的“微信”商標申請將產生不良社會影響,裁定不予核準注冊。創博亞太不服向商標評審委員會提出異議復審申請。商評委認定“微信”商標構成《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八)項規定的禁止情形,裁定不予核準注冊。創博亞太不服復審裁定,向法院提起訴訟。2015年3月11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維持“微信”商標異議復審裁定。本案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于對“公共利益和不良社會影響”的判定。因為法院是基于《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八)項的規定以維護公共利益為由判定創博亞太敗訴,避開了創博亞太的“先申請利益”。使得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價值出現了博弈,存在沖突時何者優先的問題。為此筆者撰寫本文通過對微信商標案的分析,探析公共利益在商標授權中應優先保護的正當性。
二、商標授權中應優先保護公共利益
《商標法》的制定不僅是為了維護特定民事主體的權益,也用于維護消費者這一群體所代表的社會公眾利益。“微信商標案”法院依照《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八)項的規定“有害于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響”來認定若核準創博亞太公司對微信商標的申請,將產生不良影響,進而損害公共利益,擾亂公序秩序,因此避開了對《商標法》中“申請在先原則”的援引。
1.商標授權中的“申請在先原則”及其例外規定
我國對商標注冊的核準采用“申請在先原則”,《商標法》第30條、第31條確立了商標保護的“在先申請制”。先申請制的確立可以防止商標權人“優先權”的受損,也在一定程度上敦促商標權人及時進行商標注冊申請。雖然《商標法》賦予商標權人申請在先的優先權,但“申請主義”不得對抗“使用主義”,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在先使用者的權益。《商標法》第32條規定了不能惡意搶先注冊他人已經使用并有一定影響的商標;第59條第3款規定了在先使用權人有權在原有范圍內繼續使用該注冊商標,都是對商標“申請主義”的突破。然而《商標法》32條、59條保護的情形是“在先使用”,即在商標申請注冊之前就使用了該商標,其并不涵蓋“在后使用”。而微信商標案中,騰訊公司是在創博亞太公司提出申請后才推廣使用微信并將微信發展成擁有全球影響力的通訊工具,因此本案并不符合“在先使用”的情形,無法適用《商標法》中對“在先申請原則”的突破規定。
2.公共利益在商標授權中的體現
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社會成員享有的利益。公共利益的范圍若界定不清,容易成為否定私權的工具,為此筆者將結合價值比較標準論述微信案存在的公共利益。
價值比較標準,是指通過對相沖突的利益所代表的價值進行比較,具有壓倒性的正義優勢的利益才能構成公共利益,對它應該優先進行保護。在微信商標案中,創博亞太公司作為單一的民事主體,受到《商標法》規定的“在先申請”權利的保護,而騰訊公司作為一個擁有幾億用戶群的平臺,而且用戶對“微信”的使用已經改造了全中國人的通訊交流方式,已經對公眾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兩者相比較,廣大微信用戶所代表的不特定主體的公共利益比創博亞太公司所代表的個人利益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因此該案中社會公共利益應該優先受到保護。但是不是在任何情況下公共利益都優先于個人利益受到保護,只有結合具體的案件情形比較才具有意義,而且在不同的案件中具有不同的情形,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之。
三、商標授權中濫用公共利益的影響
1.錯誤適用現有法律,致使權利架空
此次微信商標案,商標評審委員會是根據《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八)項禁止的情形,即有害于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響的,作出不予核準注冊的裁定。但筆者認為該條款的運用存在著錯誤。運用體系解釋的方法來解讀《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前七項內容,其主要針對的是商標的文字、圖形或者其他構成要素對我國政治、文化、宗教、民族等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產生消極的、負面的影響。為此商標評審委員會運用該條作出的復審裁定應當是認為“微信”商標的使用將產生不良的影響。因為騰訊公司與微信已經形成密不可分關系,如果將微信商標授予給創博亞太公司,會造成4億的用戶混淆,產生不利的社會影響。因此對“其他不良影響”做了廣義理解,不只局限于文字、圖形。
但是筆者認為如做這樣的廣義的解釋將會破壞現有的法律體系。因為《商標法》規定第十條第一款第(八)項的目的是旨在為前七項不能詳盡的標識內容做兜底性的規定,而此處卻將該條作為公共利益判定的依據實在有違法律的體系解釋。本案中,創博亞太作為在先申請人,本來可以依據《商標法》規定的“先申請原則”取得商標權的,如果錯誤適用法律,濫用公共利益,就會使得在先申請人的權利保護處于不確定狀態,容易使得權利人陷入恐慌,不利于維護法律的穩定性,而且錯誤適用法律則會損害司法權威。
2.對強勢主體的保護,致使市場競爭秩序紊亂
作為中國互聯網巨頭的騰訊,與創博亞太相比相當于大象之于螞蟻。因此即使將“微信”商標權賦予創博亞太,騰訊也可以斥資向創博亞太回購微信商標,因為打造一個具有同樣知名度和商業價值的品牌所花費的成本要遠遠高于對一個既有品牌的收購或維護,收購微信商標所付出的代價與微信背后潛藏的800多億的品牌價值相比實屬九牛一毛,而且這筆費用也是騰訊公司在為自己的過失買單,因為騰訊在推出微信前并未對該商標的權利負擔做盡職的調查,其欠缺風險防范意識造成的。無獨有偶,唯冠與蘋果的IPAD商標爭議,也正是蘋果為其過錯所付出的的天價贖金。但此次的“微信商標案”,商評委、法院都忽視了《商標法》第十條適用的應當之義,而擴張對該條的使用,使得該條成為維護公共利益而可以隨意適用的公序良俗條款,雖然適用的目的在于維護公眾利益,但如果隨意解釋適用不當,無疑會有對大公司、大企業的偏袒之嫌。為此筆者認為應當規范對公共利益條款的適用,而不能隨意濫用,否則會使得占據多數優勢資源、多數群體利益的大公司、企業處于支配控制地位,進而也降低了其履行義務的積極性,從而致使資源缺乏的小企業處于競爭的劣勢地位,使得其難以切實保護自己的利益,時刻處于權利落空的狀態,不利于市場自由競爭的有序進行。
四、結語
我國《商標法》中規定了商標注冊申請具有審查期限,在審查期內其他商標使用者就會存在商標使用盲點,不知曉該商標是否已經申請注冊,如果發生像本案的情形,即先申請者申請注冊商標但未使用,而不知情的他人在審查期限內使用了該商標,同時也提出了注冊申請,并且后者的影響范圍更廣,并涉及公共利益,這時就會存在先申請者的個人利益與后申請者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出現沖突,當兩種利益所體現的價值出現博弈時,需要運用一定的標準進行比較和權衡,何者應該優先予以保護。只有當商標的使用是涉及公眾的社會經濟、文化、甚至政治生活,是關于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時,才可以上升為公共利益,此時應該優先保護公共利益。除此之外,其他情形都應該是遵照《商標法》規定的“先申請原則”,優先保護個人利益。為此,為了防止類似微信案的糾紛再次出現,需要我國《商標法》盡快明確商標申請的及時公開,完善相應機構商標查詢系統,以免重蹈覆轍。
參考文獻:
[1]劉春田.《知識產權法》[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2]鄭永流.《中國法律中的公共利益》[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3]孔祥俊.《商標法適用的基本問題》[M].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4]劉太剛.公共利益法治論——基于需求溢出理論的分析[J].法學家,2011(2).
[5]芮松艷.商標行政案件審理情況綜合分析(中)[J].中華商標,2010(2)
[6]楊延超.“微信”商標究竟應該屬于誰[N].經濟參考報,2015年3月17日第8版.
[7]胡鴻高.論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從要素解釋的路徑.中國法學,2008(4).
[8]唐忠民,溫澤彬.關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現代法學,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