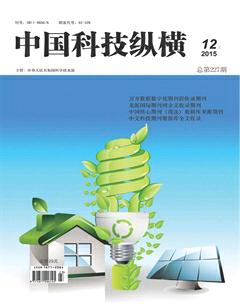關于中國畫學古和創新的思考
田麗
(鄭州師范學院,河南鄭州 450044)
關于中國畫學古和創新的思考
田麗
(鄭州師范學院,河南鄭州 450044)
在當下的商業化、媚俗化的社會背景下,對于國畫創作,如何繼承優秀傳統文化、推陳出新,形成個人風格的問題存在著一些爭議。本文立足于崇古派和革新派的分歧,主要闡述了在藝術觀念和工具材料上的傾向性的不同,以及由此引起的深層次的思考。而對學古和創新這個問題的梳理有利于對中國畫創作進一步明辨方向。
學古 創新 崇古派 革新派
中國畫有著延續千年的文脈,是中國視覺文化最精深、博大的部分。中國畫的繼承和發展始終是中國文化傳統討論的一個關鍵性命題。如何應對當下的商業化、媚俗化,又表現畫者的心性?如何傳承傳統呢?很多人為之困惑和爭論。學習國畫最終目的就是要推陳出新,要有自己的創新和個人風格。關于怎樣形成個人風格和創新的問題上,在崇古派和革新派兩類人群中存在著不小的分歧,主要體現在藝術觀念和工具材料上傾向性不同。
1 革新派
我們先說革新派。革新派認為只要文化觀念對了,隨時都可以創新,找一個與人不同的方向就能形成個人風格,我稱之為文化觀念至上論。
文化觀念至上論者認為,繪畫作為一種藝術門類,有一個共通的內在規律,這個規律就是在某個文化圈里生活的人們,被這種文化潛移默化影響所形成的一種共通的審美習慣。他們認為只要是生活在中國這個國度,受中國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就無形中繼承了中國文化的精神,而這種內在精神就會形成一種共通的文化觀念,且這個共通的文化觀念,放在國畫的范圍內,就形成一種共通的民族審美習慣,也即國畫的內在的規律。因此只要是中國人,從小接受中國文化熏陶,就相當于掌握了這種內在規律,所以無論他們怎么畫,都是中國畫,甚至用不用毛筆,都是次要的,無非是形式載體的不同罷了。這一派的代表人物當屬吳冠中,他甚至提出筆墨等于零的口號。
說到這里,這種所謂共通的文化觀念也需要單獨說明一下,所謂文化觀念,其實是一種很西化的說法,表達的范圍很寬泛,放在國畫的語境里,用純國畫的語言來講,應當稱之為格調,氣息,抑或氣質。這種觀點乍一看很正確,卻經不起仔細推敲,往深里推敲,就會發現有很多模棱兩可的地方。
一是生活在中國文化的氛圍內,也不一定就能繼承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因為這和個人的學習能力有關,這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必須主動的學習研究才有可能把握住這種文化精神的脈絡,而且個人的學習能力有高有低,也只是有可能罷了。所以說認為只要生活在中國文化圈子里,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就會主動降臨在頭上的說法是很站不住腳的,或許在每個國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打有中國文化的烙印,但那是散碎的、不自覺的、甚至是蒙昧的狀態。那種凌駕于所有人之上的、共通的民族審美習慣并不會天生存在于每個人的血液中,必須通過大量學習才能覺醒這種所謂的民族審美習慣。
二是繪畫作為一種藝術門類,還有一定的技術層面的要求,繪畫畢竟也算是一種技術活,它牽涉到材料、工具等方方面面的問題,每種民族藝術形式的形成,除了民族文化氣質外,還有相應獨特的文化載體來表達,才能形成獨特的藝術面貌。如果照革新派的理論,只要掌握了民族審美習慣就可以搞創作了,就可以不斷的創新了、形成個人風格了,那藝術家應該滿大街跑才對,藝術大師也該論筐裝,不至于幾百年才出一個,所以這種說法無疑是癡人說夢。
2 崇古派
崇古派認為只要不斷的臨摹古人作品,到了一定階段,創新、風格這些問題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我稱之為臨摹至上論。
臨摹至上論者認為,傳統很重要,國畫是一門傳承有序的藝術門類,所謂的傳承有序就是它有自己一套固定的內在規律,我們掌握了這套規律,就等于抓住了國畫的根本。而這個根本,大概就是遵循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的謝赫六法。所以對古代作品的學習是一個必經的階段,而且這個階段是長期的,必須把古人的東西完全吃透,才能談風格和創新。而且崇古派認為,一種文化氣質的表達,必須有一種最適合的文化載體,才能最大限度的表達這種文化氣質,而我們無數前輩的實踐證明,筆墨無疑是最適合的文化載體,甚至是獨一無二的文化載體,獨一無二到一旦離開了這種載體,所謂的文化氣質就成了空中樓閣,無從談起。文化觀念和文化載體恰如自行車的前后轱轆,你不能說那個轱轆更重要。所以筆墨功夫是學習國畫無法繞過的一道坎,也是學習國畫是否入門的一道分水嶺,如果筆墨功夫不到家,套用清人評論郎世寧作品的原話,就是雖工亦匠。
通過以上兩種觀點的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兩者的分歧一是創作順序的問題,二是工具材料的問題 。
3 兩者的對比和思考
關于創作順序的問題,我認為革新派那種看似高屋建瓴的做法很不切實際,完全是強行把西畫的理論移植到國畫系統里來,有點驢唇不對馬嘴,實際操作性比較差。就國畫而言,摹古派推崇的謝赫六法的操作性更實際一點,六法是一個由低到高的三個學習階段,其間順序整理如下,第一個階段即傳移模寫。也就是先臨摹前人優秀的作品,學習前人的優點,傳承流傳有序的精華部分。第二個階段即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這幾項的綜合。也就是通過學習前人作品,掌握用筆方法和用色技巧,解決造型和構圖問題。第三個階段即氣韻生動。通過臨摹,技法問題解決了,工具應用得心應手,如臂指使,到了隨心所欲的階段,所謂的氣韻生動自然而然就來了,什么風格創新之類的問題自然而然也解決了。
而說到文化載體的問題,我們不能不說一下國畫品評的一些基本常識,即大家品評一幅國畫作品時所遵循的一些基本的標準,比如我們常說的這幅作品是格調高雅還是格調低下,是氣質脫俗還是氣質渾濁,是富有文人氣還是市井氣,以及山林氣、江湖氣、工匠氣等不一足,也就是說這幅作品的整體氣質怎么樣。說到作品氣質,有一種說法是和個人氣質有關,我是不贊同這種說法地,我個人認為作品的氣質和個人的氣質關系不大,那種人品即是畫品的說法我也認為是荒謬的,他只和你的審美取向以及個人性格有關,其中你的審美取向占了一大部分。所以這個審美取向也是一個分水嶺,如果你的審美取向傾向于市井,傾向于所謂的俗氣,那你的筆墨就會不知不覺的為此服務。而審美取向的形成,和個人的生活環境,人生閱歷,以及讀書多寡等關系有關,比較錯綜復雜,這里就不多加探討。因此有時候我們大家會提到一個名師的問題,說有一個好老師會少走好多彎路。這個名師的作用,其實就是一個解決你審美取向的作用。有了老師給你強制解決審美取向的問題,就不會有你自己慢慢總結時出現的偏差的問題了。這反過來也印證了審美習慣并不是天生的,必須經過系統的后天學習才能形成,也再一次反正了革新派那種論調是鉆了牛角尖。而其對工具材料也即文化載體采取完全拋棄的態度,也是過猶不及。每種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氣質用合適的文化載體來承載這種文化氣質才是理智的決定,比如吃西餐用刀叉,中餐用筷子,你要非換著來也能吃到嘴里,但完全不倫不類。而說到學古,指的是學習古人的精神,學習古人的氣質。往白了說就是學習古人如何用適合的筆墨程式創造出屬于自己的氣質的方法,而想學習并掌握這種方法,那就必須在精神氣質方面與你所學習的古人做到一定程度的契合,這個很重要。但有些崇古派在學習的過程中犯了和革新派一樣的毛病---矯枉過正,除了臨摹古畫不敢越雷池一步,連工具材料都要做到和古人一模一樣才好,完全不管各個歷史時期不管是繪畫風格和工具材料都不盡相同的事實,僵化刻板,完全浮在外表,難免令人對這種一味崇古,不知變通的做法嗤之以鼻!
所以不管是學古還是創新,首先要弄明白自己學古或創新的目的是什么。學古并不是一味的鉆到故紙堆里不出來,而是要學習古人觀察世界以及進行創作的方法。創新也不是單純的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在前人基礎上的拔高。所謂的風格,并不是你畫的和別人不一樣就是風格,要符合基本的藝術規律,遵循一定的審美標準,對一樣東西先熟知在改造,這樣得出的結果才會最合理,漫談改造顯得太不嚴肅。
還有一種說法是國畫作品的創作具有一種不可復制性,就在于它關乎學養、功力、情緒、甚或當時的氣候環境的影響,不是你想畫好就能畫好的,它有許多的‘偶然性’在起作用。我認為這種創作過程中的偶然性是存在的,不過這個偶然性也是有前題的。這種偶然是在畫者繪畫技巧熟練的情況下發生的,在畫者的可控范圍內,不是純粹的為偶然而偶然!是可利用的偶然,甚至是有意識的偶然,比如不會畫畫的人,偶然更多,可惜都用不上,所以這個偶然有其必然性!也即是說那種所謂的不可重復性、所謂的天氣、心情、環境等都不是主要因素,不是一幅畫好壞評判以及創作好壞的主因,只是一種氣質的附加,比如王羲之蘭亭序寫的好,可能有外在因素的影響,但主要還是他本人寫的本來就好,外在因素不過是做了附加而已,他別的作品也不壞。
中國畫的創作要與時俱進,要在創作中把握它的精神內涵和外延形態。石濤的“無法之法,乃為至法”,“我自用我法”不失為現代人所效仿的精神。
[1]應一平.中國畫傳承與創新的思考[J].藝術教育,2014,10.
[2]顧丞峰.中國畫繼承和創新的可能性[J].文藝研究,2001.3.
[3]高阿影.關于國畫學習和創新[J].青年文學家,2006.5.
田麗(1980—),女,河南許昌人,單位:鄭州師范學院美術學院,職稱:講師,學歷:研究生,研究方向:美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