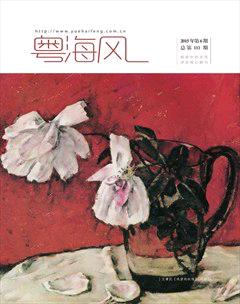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生產和傳統發明
易紅霞
“傳統不是古代流傳下來的不變的陳跡,而是當代人活生生的創造;那些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遠的傳統,其實只有很短的歷史;我們一直處于而且不得不處于發明傳統的狀態中,只不過在現代,這種發明變得更加快速而已。”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蘭格的著作《傳統的發明》
“傳統”與“現代”,“一體化”與“多元化”(或“多樣化”),是文化人類學“全球化”研究的兩對基本概念。似乎已經老掉牙了,但是,對于常常面對文化發展“傳承”與“創新”、“個性”與“共性”吵得不可開交的我們,依然有很多矛盾和糾結,翻來覆去地困擾和苦惱著我們。或許,我們應該換個角度來思考這個未解的話題了。
我們比較熟知的觀點,也是廣受學界追捧的觀點是,全球化就是一體化,甚至是西方化、美國化。全球化在破壞不同文化之間的邊界,在破壞文化的多樣性。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將會越來越趨同,與此同時,文化的差異性將越來越少。在不少人眼里,全球化就如同洪水猛獸,在全球化浪潮的強力沖擊下,傳統文化、異質文化將逐漸被淹沒以致最終消失。因此,傳統文化急需保護與搶救。我們常常為此而搖旗吶喊,不遺余力。
表面上看,這沒有任何問題。它所揭示的,是擺在我們眼前的一個個活生生的事實:君不見一個個現代化的城市在全球各地拔地而起,全然喪失了地域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君不見一種種民風民俗、一個個傳統節日、一樣樣傳統技藝瀕臨失傳,再找不到新的傳承人。因此,傳統文化急需保護與搶救。這些年來,各個國家和地區越來越重視對本土文化、傳統文化、特色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我國學界與政府也越來越重視告訴發展中傳統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和保護。問題在于,部分“搶救派”將“傳統”與“現代”、“一體化”與“多元化”完全對立,對傳統文化持一種靜態的、消極的保護觀,人為地制造一個個與世隔絕的文化孤島,進而反對任何發展與變革,便難免主觀臆斷、違背被保護者意愿,硬將傳統文化置于廢墟般的僵死狀態。這是一種靜態、消極的文化傳承觀。我長期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尤其是中國傳統戲曲藝術的保護與傳承問題,并深入田野調查多年,從我接觸的絕大多數被調查對象來看,這種靜態、消極的傳承方式,其實也違背傳統文化守護人的主觀意愿。他們希望傳統文化的精髓得以保存,更希望他們所從事的傳統文化工作不是一種博物館的“死”的藝術,而是一種能夠活在當下、受人歡迎、與時俱進的藝術。
和搶救派不同,“文化的生產”和“傳統的發明”的理論,卻從動態、積極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且讓我們簡單梳理一下有關學術思想。
馬克思在他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關于“傳統”和“歷史的創造”有一段經常被人引用的名言: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1]
在此,馬克思用詩意的語言,深刻地揭示出“傳統”和“創造”之間的“像夢魘一樣糾纏著”的辯證關系:歷史的創造者往往借助于傳統“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來“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和馬克思的觀念一脈相承。他在承認社會文化強大制約力的同時,強調社會文化是一個不斷被實踐改變、創造的動態發展過程。他所說的“再生產”既不是無中生有的創造,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重復。[2] 他在《教育、社會、文化的再生產》(1970)、《實踐論綱要》(1977) 、《雅趣:品位判斷的社會批判》(1979)、《知識精英》(1984)、《國家貴族》(1989)《藝術規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1996)一系列作品中,提出了“場域”、“習性”、“雅趣”、“象征暴力”等概念,極富創造性和解釋力,對當代學術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美國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進一步拓展了文化再生產的解釋空間。比較而言,馬克思和布迪厄主要是從政治、社會、階級的角度來闡釋文化再生產的,馬歇爾·薩林斯則更多地是從歷史與結構的角度,闡述了文化的“變”與“不變”的辨證關系,認為“過去就存在于我們中間”。[3]
馬歇爾·薩林斯在其對庫克船長之死的研究中發現,當土著文化和外來文化接觸后,新的文化產生了,舊的文化卻沒有消失,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文化+文化”的現象。在這一過程中,文化在不斷地被生產和再造,傳統也就在不斷地被發明。在《歷史之島》一書中,他有意識地“對那種迂腐學問中強求一致的二分法”進行了“某種批判性的反思”。[4] 他指出:
事物越是一成不變,變化就越大,因為范疇的每一次諸如此類的再生產都是不一樣的。就行為而言,文化的每一次再生產都是一種改變,使現實世界得以協調地存在的那些范疇在每一次變化中都增加了一些全新的經驗內容。[5]
在《何為人類學啟蒙——二十世紀的若干教誨》一文中,薩林斯借新幾內亞印加人(Enga)對西方力量的主動利用,闡述了他關于“文化的星球性重組”的觀點,提出了“世界文化體系”的概念。他說:
最近幾個世紀以來,與被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所統一的同時,世界也被土著社會對全球化的不可抗拒力量的適應重新分化了。在某種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質性與地方差異性是同步發展的,后者無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這樣的名義下做出的對前者的反應。因此,這種新的星球性組織才被我們描述為“一個由不同文化組成的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s),這是一種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組成的世界文化體系。正如烏爾夫·漢尼孜(Ulf Hannerz)所指出的:“現在存在有一種世界的文化,但是我們最好確證一下我們是否理解這一點意味著什么。這種文化的特征是一種差異性的組織,而并非同一性的復制。”因此,這種新全球化普適性的一種補充,就是近幾十年來是所謂文化主義(culturalism),這即是指對于他們的“文化”的自覺,是一種被生活和保護著的價值,這種觀點已經在第三和第四世界中蔓延開來。[6]
在此,薩林斯強調了全球化時代世界文化“同質性與地方差異性”的“同步發展”,富有遠見卓識地指出,這種“文化的星球性重新組織”正如烏爾夫·漢尼孜所說,“是一種差異性的組織,而并非同一性的復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將這種“文化的星球性重新組織”描述為“一個由不同文化組成的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s),認為它是“一種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組成的世界文化體系”。這種“新的星球性組織”和“世界文化體系”來自兩種既對立又統一的力量:一方面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一方面是“土著社會對全球化的不可抗拒力量的適應”,前者帶來全球性的“統一”,后者帶來的世界的“重新分化”。顯然,他的這種“世界文化體系”概念,遠比單從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出發所提出的“世界體系”(包括帝國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體系)來得更為平實、客觀,更符合當前世界既逐漸統一又多元化發展的實際。
薩林斯這種全球性的文化重組的觀點,和馬克思、布迪厄的文化生產的概念遙相呼應,我們可將它視為一種全球性的文化的生產和傳統的發明,一種全球性的“文化+文化”的現象。在這一全球性文化重組的過程中,傳統與現代、繼承與創新并不絕然對立。薩林斯尖銳地指出:
幾乎所有人類學家們所研究和描述的“傳統的”文化,實際上都是新傳統的(Neotraditional),都是已經受西方擴張影響而發生改變的文化。[7]
非西方民族為了創造自己的現代性文化而展開的斗爭,摧毀了西方人當中業已被廣為接受的傳統與變遷的對立、習俗與理性的對立的觀念,尤其明顯的是,摧毀了20世紀著名的傳統與發展對立的觀念。當哲學家們暗暗地想把腐朽的東西砸爛,想通過進步理性來摧毀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之時,這些對立觀早已顯得陳舊了。[8]
在這里,薩林斯已經把文化的生產和新傳統的發明緊密聯系在一起了。“傳統的發明”是一個與“文化的生產”密切相關的概念。
英國人類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對“傳統的發明”有著更為獨到的研究和深刻的見解。在他主編的《傳統的發明》一書中,通過蘇格蘭民族服裝的起源、威爾士的典籍再造、英國皇家儀式的變遷、英國統治下印度慶典禮儀的變化、非洲人對英國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間英法德三國民族節日和大眾文化的變化六個個案,揭示出“傳統是被當代人發明出來的”的道理。該書認為:
傳統不是古代流傳下來的不變的陳跡,而是當代人活生生的創造;那些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遠的傳統,其實只有很短的歷史;我們一直處于而且不得不處于發明傳統的狀態中,只不過在現代,這種發明變得更加快速而已。[9]
在有關“發明傳統”的研究中,霍布斯鮑姆還敏銳地發現:
更有意思的是,為了相當新近的目的而使用舊材料來建構一種新形式的被發明的傳統。這樣的材料在任何社會的歷史中都有大量積累,而且有關象征實踐和交流的一套復雜語言常常是現成可用的。[10]
這和馬克思的“穿著傳統的服裝、上演新的一幕”的觀點,如出一轍。
文化人類學認為,文化的傳承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無意識的傳承”,一種是“有意識的創造”。千百年來,文化一直在被無意識地傳承著,傳統社會里的傳統文化,尤其是文字、交通、信息不發達的原始社會和農業社會,外來文化沖擊小,先民口口相傳,模仿沿襲,文化更多地采用的是這種“無意識的傳承”的方式,傳統被一代代地繼承下來,結構穩定,不是沒有變化,但變化緩慢。到了文明社會,尤其是現代社會,交通信息發達,地球成了一個村,越來越小,太平洋東岸的蝴蝶扇動一下翅膀,就會激起太平洋西岸的一陣颶風。民族文化、區域文化、地方文化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無處躲藏。如果任其自然、聽之任之,終難逃被邊緣化和消滅的命運。這時候,人類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更多地是、或者說更需要一種“有意識的創造”。更客觀地說,沒有哪種傳統不是在不斷和外來文化的接觸中不斷地被生產和發明出來的,傳統在不斷地更新,沒有更新的傳統沒有生命力,沒有變異的傳統不會發展。反過來說也一樣,沒有傳統的創造是空中樓閣,離開了傳統的發明是無根之木。正如麻國慶在他的《全球化文化的生產與文化認同》一文中所說:
文化人類學的研究一直著眼于民族文化的研究,特別是側重于“無意識的文化傳承”的研究。而在今天,不同國家、地域和民族的文化其“無意識的傳承”傳統,常常為來自國家和民間的力量,進行著“有意識地創造”。這種創造的過程,正是一種“文化的生產”與“文化的再生產”的過程。這種“生產”的基礎,并沒有脫離固有的文化傳統。[11]
歷史是割不斷的,歷史也是無法割斷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文化的生產和傳統的發明,終究是在歷史、傳統、慣習的基礎上無意識和有意識地進行的。這一點,對于常常糾結于社會高速發展進程中“傳統”與“現代”、“保護”與“發展”、“傳承”與“創新”、“多元”與“單一”、“個性”與“共性”的現代中國,具有非同凡響的意義。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199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603頁。
[2]Richard Brown edited: 1971,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Tavistock, London.
[3]馬歇爾·薩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庫克船長為例》,張宏明、趙丙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39頁。
[4]馬歇爾·薩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庫克船長為例》,張宏明、趙丙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94頁。
[5]馬歇爾·薩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庫克船長為例》,張宏明、趙丙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86頁。
[6]馬歇爾·薩林斯:《何為人類學啟蒙——二十世紀的若干教誨》,見《甜蜜的悲哀》,王銘銘、胡宗澤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出版,第123頁。
[7]馬歇爾·薩林斯:《何為人類學啟蒙——二十世紀的若干教誨》,見《甜蜜的悲哀》,王銘銘、胡宗澤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出版,第123頁。
[8]馬歇爾·薩林斯:《何為人類學啟蒙——二十世紀的若干教誨》,見《甜蜜的悲哀》,王銘銘、胡宗澤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出版,第125頁。
[9]E·霍布斯鮑姆、T·蘭格:《傳統的發明》,顧杭、龐冠群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出版。
[10]E·霍布斯鮑姆、T·蘭格:《傳統的發明》,顧杭、龐冠群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6-7頁。
[11]麻國慶:《全球化文化的生產與文化認同》,見《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4期,第154-1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