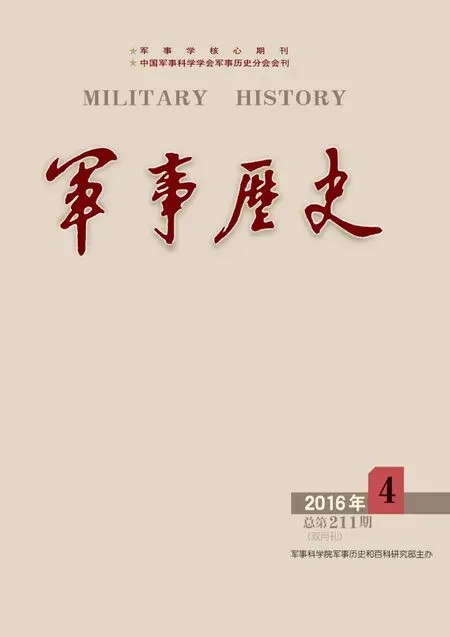“攻戰(zhàn)守”釋義考辨
★
一、問題的提起
受時下中國周邊安全環(huán)境影響,學界對閎廓深遠的古兵法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也對其解釋產(chǎn)生了某些歧義,其中對《司馬法》有關“攻戰(zhàn)守”的理解,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認為,“攻戰(zhàn)守”代表攻、守二種作戰(zhàn)樣式;另一種認為,“攻戰(zhàn)守”代表攻、戰(zhàn)、守三種作戰(zhàn)樣式,并由此產(chǎn)生了古代作戰(zhàn)是有二種基本作戰(zhàn)樣式還是有三種基本作戰(zhàn)樣式的爭論。為探其究竟,很有必要對其進行一番考證。
二、“攻戰(zhàn)守”釋義考
“攻戰(zhàn)守”一語出自《司馬法》“定爵”篇,其文如是:攻戰(zhàn)守進退止前后序車徒因是謂戰(zhàn)參。就其譯文,不同版本,有不同釋義。如李零所著《司馬法譯注》,將此句斷分為:攻戰(zhàn)守,進退止,前后序,車徒因,是謂戰(zhàn)參;其譯文是:進攻、作戰(zhàn)、防守,前進、后退、停止,前后位置排列有序,車兵和徒兵相互配合,這叫作戰(zhàn)必須檢驗的東西*李零譯:《司馬法譯注》,35、36、38 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田旭東所著《司馬法淺說》,將此句斷分為:攻戰(zhàn)、守進、退止、前后序,車徒因,是謂戰(zhàn)參;其譯文是:攻擊敵人,與敵決戰(zhàn),對敵防守,作戰(zhàn)目的必先明確。見可進則進取,不可進即后退,適可而止。前后有序,戰(zhàn)車、步兵相互為用,協(xié)同作戰(zhàn),這是臨戰(zhàn)參酌詳審不可忽略的*田旭東:《司馬法淺說》,60、63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和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主編的《司馬法今注今譯》,將此句斷分為:攻,戰(zhàn),守,進,退,止,前后序,車徒因,是謂戰(zhàn)參;其譯文是:攻擊敵人,與敵決戰(zhàn),對敵防守,是作戰(zhàn)目的先要確定。見可進就進取,見不可進就后退,見可停止就停止,是作戰(zhàn)對象先要確定。然后才可以安排作戰(zhàn)軍的前后次序和兵種的協(xié)同。這是臨戰(zhàn)參詳不可忽略的*劉仲平注譯:《司馬法今注今譯》,58、74~7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以上三個版本的譯著,盡管斷句不同,但對“攻戰(zhàn)守”的解釋基本相同,即將“攻”解釋為進攻、攻擊,將“戰(zhàn)”解釋為作戰(zhàn)、與敵決戰(zhàn),將“守”解釋為防守、對敵防守。如此斷句釋義代表了當今學界的一種學術(shù)觀點,而且是主流觀點,如著名的《司馬法箋證附韻讀》《司馬法直解》《司馬法(張輯)》《司馬法(錢輯)》等譯著,均持這一觀點。筆者姑且將這一觀點稱之為甲種觀點。不過,還有另外一種觀點,出自毛元佑、黃樸民注譯的《武經(jīng)七書》,其斷句為:攻戰(zhàn)守,進退止,前后序,車徒因,是謂戰(zhàn)參;其譯文是:掌握攻戰(zhàn)守的不同要領,把握進、退、止的時機,注意前后左右的配合和戰(zhàn)車步兵間的協(xié)同,這些都是臨戰(zhàn)前應該考慮好的事情。而具體到“攻戰(zhàn)守”的注釋,卻解釋為:“攻戰(zhàn)守:它們是三種基本的作戰(zhàn)樣式,一般而言,攻城稱為‘攻’;野戰(zhàn)稱為‘戰(zhàn)’;城市防御作戰(zhàn)稱為‘守’”*毛元佑、黃樸民注譯:《武經(jīng)七書》, 125、135、130頁,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筆者姑且將這一觀點稱之為乙種觀點。
三、“攻戰(zhàn)守”釋義辨
上述兩種觀點,究竟哪一種更接近或更符合作者本人司馬穰苴之意呢?這要從字源和古漢語字典的解釋中去尋找答案。從字源上講,攻是形聲字,在金文、篆書中以“攴”為形,“工”為聲,在楷書中以“攵”為形,“工”為聲。其本義是指攻打、進攻。在《古代漢語字典》中,攻的釋義是攻打,進攻。*《古代漢語字典》,24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左傳·僖公四年》: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墨子·公輸》: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史記·項羽本紀》: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等等均是此義。戰(zhàn),從字源上講,是形聲字,“戈”為形,“占”為聲;在金文中,戰(zhàn)亦是會意字,由“戈”和“獸”組成。其本義是指作戰(zhàn)、交戰(zhàn)。在《古代漢語字典》中,戰(zhàn)的釋義是作戰(zhàn),打仗。*《古代漢語字典》,1031頁。《左傳·莊公十年》:公與之乘,戰(zhàn)于長勺;《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zhàn)之大功;《石壕吏》: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zhàn)死,等等均是此義。守,從字源上講,是會意字,由“宀”和“寸”兩部分上下組合而成。“宀”在這里指衙門,“寸”表法度。其本義是官吏職責。在《古代漢語字典》中,守的釋義是防守,守衛(wèi),與“攻”相對。*《古代漢語字典》,729頁。如《周易·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墨子·公輸》:殺臣,宋莫能守;《過秦論》: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等等均是此義。
我們將甲乙兩種觀點與字源釋讀和古漢語字典的解釋相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甲種觀點與字源和古漢語字典的釋義完全相同,而乙種觀點則在字源釋讀和古漢語字典的解釋中難尋依據(jù)。其實,通讀《司馬法》或其他古兵法,也可以從中尋到答案。如《司馬法》仁本篇:“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zhàn)止戰(zhàn),雖戰(zhàn)可也”,“內(nèi)得愛焉,所以守也”;用眾篇:“攻則屯而伺之”;嚴位篇:“凡戰(zhàn),以力久,以氣勝”;天子之義篇:“短兵以守”。《孫子兵法》:“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戰(zhàn)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孫子兵法·軍形篇》。。《吳子》應變篇:“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論將篇:“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治兵篇:“一人學戰(zhàn),教成十人”等等,對攻、戰(zhàn)、守的解釋,均與字源和古漢語字典的釋義相同。
通過上述對攻、戰(zhàn)、守釋義的辨析,可以確定,攻即是進攻、攻擊、攻打,其意既包括野戰(zhàn)中的進攻,也包括城市作戰(zhàn)中的進攻,但絕非專指攻城;守,即是防守、守御,其意既包括野戰(zhàn)中的防御,也包括城市作戰(zhàn)中的防御,但絕非專指守城;戰(zhàn),即是作戰(zhàn)、交戰(zhàn),其意既包括城市攻防作戰(zhàn),也包括野戰(zhàn)攻防作戰(zhàn),但絕非專指野戰(zhàn)攻防作戰(zhàn)。由此可推知,“攻戰(zhàn)守”應斷分為“攻戰(zhàn)、守(戰(zhàn))”,對此,大體成書與《司馬法》同處一個歷史時期的《商君書》有比較恰當?shù)尼屛模骸八膽?zhàn)之國貴守戰(zhàn),負海之國貴攻戰(zhàn)”*《商君書·兵守篇》。。據(jù)此可知,“攻戰(zhàn)守”即是攻戰(zhàn)和守戰(zhàn)之意,只是“守”后的“戰(zhàn)”字或省略或在相傳中遺失罷了。而“戰(zhàn)”并非是一種作戰(zhàn)樣式,是指作戰(zhàn)、交戰(zhàn),它包含了進攻和防御兩種作戰(zhàn)樣式。自此可以明晰:古代作戰(zhàn)和現(xiàn)今一樣,也只有進攻和防御兩種基本作戰(zhàn)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