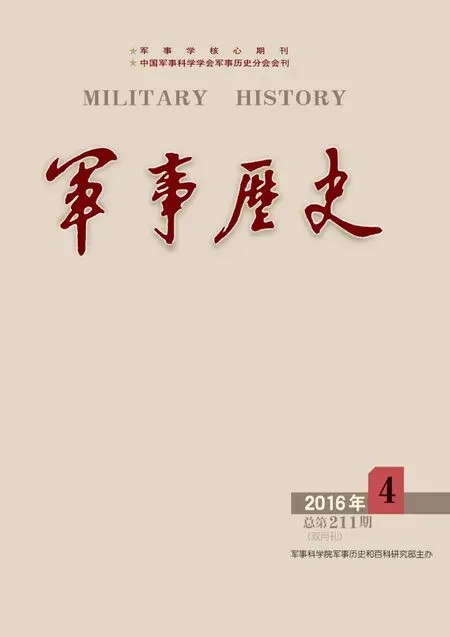試論諸葛亮《八陣圖》
★
一
方陣作戰是冷兵器時代戰爭的基本方式。所謂“方陣”,就是密集厚實的整齊戰斗隊形,大多呈方形或長方形,故稱方陣。“方陣”一詞,狹義指方形戰斗隊形;廣義泛指密集厚實的整齊戰斗隊形,多數是方形,也有非方形者。“方陣作戰”概念就是用其廣義。
方陣作戰的基本要求是厚集兵力,統一步調,形成強大的集團沖擊力或堅強的整體防御。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基本是方陣對決,以整勝亂、以整勝散是基本規律——哪一方的陣形先亂,哪一方的陣形先散,哪一方就必然歸于失敗。因為保持整齊隊形的集團方陣,其強大沖擊力或堅強防御力是任何散兵游勇所難以對抗的。所以古代實戰陣法的基本原則就是厚集兵力,整齊統一,即以訓練有素的士兵組成密集厚實的整齊集團隊形,步調一致、行動統一,其方法并不復雜,其特點就是厚集兵力,簡單實用,統一整齊。越復雜的陣法,必然越難以統一一致,往往不足以勝敵,反而自亂陣腳,自取其敗。
然而,與實戰陣法的簡單實用相背離,中國古代陣法理論發展卻走上了神秘化、復雜化的玄虛道路。其中有兩個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兵陰陽理論的盛行。戰國秦漢時期,陰陽五行學說趨于成熟,逐漸成為中國人看待宇宙萬物世界萬象的基本方法論。受此影響,在軍事領域也產生了兵陰陽學派,運用陰陽五行學說來預測、分析、闡發戰爭和軍事問題,形成了系統的兵陰陽理論*漢代將兵家總分為四派: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漢書·藝文志·兵家》述兵陰陽理論:“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斗擊,北斗所指,泛指星象;五勝,五行相勝。。這一派人多為占星望氣的方術之士,排兵布陣之法是其熱衷探討的重要問題,他們沒有實戰經驗,卻有基于陰陽五行理論的成套推演方法,其陣法理論,遂越來越脫離實際,而趨向神秘化。
二是文人論兵風氣的盛行。文人論兵,發端于戰國時期,漸成風氣,其流弊便是“披甲者少而言兵者眾”,“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益弱”。何也?蓋紙上談兵,不切實用,夸夸其談成風,反而敗壞了社會風氣,誤國誤民。中國歷史上文人論兵的風氣在宋、明兩代達于極盛,這兩朝因而也是紙上談兵風氣的高峰。眾多文人學士,熱衷于談兵論戰,他們沒有實戰經驗,又受陰陽五行學說的強烈影響*這時,陰陽五行學說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基本思想方法。,更進一步加重了軍事理論特別是陣法研究的神秘化和復雜化,于是,在陣法研究中形成了文人論兵和兵陰陽理論的合流之勢,大量的兵書,純粹從兵陰陽的理論模式——諸如陰陽五行、太極兩儀、八卦九宮,等等,推演出了五花八門的復雜陣法,在實戰中則完全難以運用,其末流,甚至墮落為奇門遁甲的法術。宋、明兩朝,兵書撰著之豐創造了“世界之最”,而在實際戰場上則疲弱不振,屢戰屢敗,與此不無關系。
了解了中國古代實戰陣法與陣法理論之間存在的悖反現象,有助于我們對諸葛亮《八陣圖》研究采取正確的態度,這就是必須以實戰為依歸,力求把握其實戰性特點,切忌墮入傳統陣法理論神秘化、復雜化的誤區。
二
諸葛亮《八陣圖》歷代眾說紛紜,后世演繹紛繁,但從當時和接近的時代留下來的可靠史料并不多,從這些較為可靠的史料,筆者認為可以得出如下基本認識。
(一)《八陣圖》是一部陣法著作。《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記:“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這是史籍中關于諸葛亮作《八陣圖》的最早而明確的記載。所謂“推演兵法作《八陣圖》”,也就是對用兵布陣之法進行研究演練,由此而形成確定的作戰陣法,著為《八陣圖》。《晉書·職官志》記載,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魏滅蜀漢后不久,司馬昭專門派陳勰去學習諸葛亮的“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可見諸葛亮的作戰陣法有其獨到之處,是對陣法的創新發展,在當時就受到兵家推崇。所以晉·李興所撰《諸葛丞相故宅謁表》云:“推子八陣,不在孫吳。”*見《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蜀記》。《八陣圖》既然名為“圖”,應當是以圖為主干,輔以文字說明的著作。無圖不明,無文不詳。圖文結合也是古代陣法著作的基本特點。
(二)《八陣圖》是指導蜀軍訓練作戰的一部陣法手冊。諸葛亮存世的有關兵法的文字大多簡略*后世托名諸葛亮的一些兵書,如《將苑》,篇幅較大,本文不將之作為依據資料。,具有很強的實用性,與實戰緊密相關,甚至直接指導實戰。這些遺文中常有關于布陣的訓令、教諭,如《軍令》:“敵已來,進持鹿角,兵悉卻在連沖后”*《太平御覽》卷三一七引。;“帳下及右陣各持彭排”*《太平御覽》卷三三七引。。又如《賊騎來教》:“若賊騎左右來至,徒從行以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蒙陣而待之。地狹者,宜以鋸齒而待之”*《北堂書鈔》卷一一七引。。這反映了諸葛亮的兵法著述具有高度的現實針對性和實踐指導意義。因此,其所作《八陣圖》應當是對實戰經驗的總結之作,具有指導蜀軍訓練作戰的實際作用,可以視之為由蜀軍實戰使用的一部“陣法手冊”,類似于今天軍隊必然要有的《作戰手冊》。
(三)《八陣圖》中的陣法可以運用于不同戰場環境,《八陣圖》對蜀軍作戰有全面指導作用。從西晉到南北朝,史書中留下了幾條材料,反映出諸葛亮《八陣圖》中的陣法可以運用于不同的戰場環境。《晉書·馬隆傳》記載,西晉咸寧五年(279年),馬隆率軍平定涼州(治今甘肅武威)羌人之亂:“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眾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后。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這是諸葛亮《八陣圖》中的陣法被運用于西北山地作戰的例子*參見《李衛公問對》卷上,唐太宗與李靖討論諸葛亮《八陣圖》,稱馬隆便是依此“作偏箱車”。。《晉書·桓溫傳》記載,東晉永和二年(346年),桓溫伐蜀,在白帝城附近的江灘上見到了當年諸葛亮軍陣的遺跡:“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為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于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這反映了諸葛亮《八陣圖》之陣法曾被運用于峽江地區的攻防作戰。《魏書·高閭傳》記載,北魏孝文帝時,大臣高閭上書建策:“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修立戰場,十日一習。采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御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御寇。”《通典》卷一九六《北狄·蠕蠕》又記,北魏皇興年間柔然犯塞,大臣刁雍也建議“采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御寇之方”。這說明諸葛亮《八陣圖》之陣法可以運用于平原廣野作戰。
蜀軍作戰,有三個主要的戰略方向,一是北方逾秦嶺趨向關中,一是東南出三峽趨向荊襄,一是西南跨大渡河趨向云貴。上述史料反映出,諸葛亮《八陣圖》陣法在這幾個方向的戰場應都可以運用,因此它對蜀軍作戰具有全面的指導作用。
(四)諸葛亮《八陣圖》應包含多種陣法,可以根據不同戰場和敵情,選擇運用,而不是一套陣法廣泛適用,也不是單一陣法只用于某種戰場環境或某種類型的作戰。從上引史料可見,諸葛亮《八陣圖》不是只運用于某一種戰場環境或某一種類型的作戰,因此,它必然包含多種陣法,可以根據不同的戰場環境和所面臨的敵情,具體、靈活地選擇運用。設想它只是一套陣法,而能廣泛適用于各種不同的戰場,是完全不切實際的。
(五)諸葛亮《八陣圖》陣法的突出特點是組織嚴整,而非靈動變化。“諸葛一生唯謹慎”。陳壽在《三國志》中評價諸葛亮的才能,“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也就是說,諸葛亮最突出的才能是治國理政,而非帶兵打仗,其軍事才能,又以治軍(即管理部隊)為長,作戰用兵的出奇制勝是其短處。關于諸葛亮的軍事才能,《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袁子》也說:“亮,持本者也,其于應變,則非所長也。”諸葛亮軍事才能的這個特點,在其指揮的戰爭中有突出的表現,特別是“六出祁山”攻魏,每次都穩扎穩打,不敢出奇冒險,結果始終不能突破魏軍防線,師勞功微。然而,諸葛亮的治軍才能,連魏將也深為佩服。其最后一次出祁山攻魏,據五丈原,與司馬懿統領的魏軍相持百余日,發病卒于軍中。蜀軍退走后,司馬懿查看蜀軍駐軍布防的“營壘處所”,禁不住贊嘆諸葛亮“天下奇才也”*《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司馬懿所嘆服的,自然是諸葛亮駐軍布防的嚴整有序。從諸葛亮的軍事才能特點,可以推知其所設計的陣法,必然以組織嚴整為突出特點,而不是以靈動變化為特征。傳諸葛亮自己曾說:“八陣既成,至今行師,庶不覆敗。”*《水經·江水注》。諸葛亮正是靠其創設的陣法,訓練蜀軍以嚴整的組織進行各種攻防戰斗,確保了蜀軍作戰的有序性和穩固性,因而不至于輕易覆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