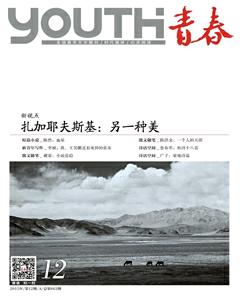小說范穩
姚霏
四川男人是不是都綿里藏針,這我沒做過考證。但范穩屬于此列。
30年前的1985年,我是和范穩夫婦一起大學畢業后從外省分到昆明來的。我和他夫人張維是回家鄉,他則是入贅云南。那時候他白凈得與高原的紫外線格格不入,因此寡言少語。我甚至不知道那時候在云南省地礦局工作的他,是否已經開始了文學創作。張維在云南人民出版社文藝處做編輯,與寫作者的交往是很頻繁的,作家們聚會的時候,范穩總是默默喝酒,不多與人搭訕,像個加繆筆下的局外人——藏在綿里,針不外露。
大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晚些時候,有一天詩人于堅對我說,云南寫小說的人,有個叫范穩的值得期待。可惜那時沒有互聯網,想關注也無從著眼。直到1989年,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從云南師大辭職,側身江湖,寫了長篇武俠小說《一劍平江湖》之后,才算是真正了解了范穩。原因很簡單,那時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領導,讓張維做了我署名“滄浪客”的《一劍平江湖》及其以后所有武俠小說的責任編輯,我得經常去她和范穩在昆明書林街那個當時出版社分配的窄小的家里,商討某些細節。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看了范穩不少的早期作品,應該就是后來被收入他的中短篇小說集《回歸溫柔》和《男人辛苦》的大部分篇什吧。說實話,文筆細膩,情感真摯,是那些中短篇小說的最大特色,我不知道當時的文學批評家們是怎么評價的,但在我看來,氣象確實還不夠大。只不過,在與他的閑談中,其偶爾不露聲色的鋒芒,會使你惕然而驚:這家伙一旦接了地氣,讓“針”穿出了“綿”,前途將無可限量。
1990年,我離開云南去上海、北京和深圳,雖說與云南文壇基本上失聯,但對云南作家的作品,還是念茲在茲。范穩的長篇小說《騷莊》《冬日言情》《山城教父》《清官海瑞》一部接一部出版,可惜影響似乎都不太大。那時我就在想,如果把作家分類的話,一類像隱居“城堡”的卡夫卡、塞林格,一類像貼著大地行走的杜甫、塞萬提斯,范穩為什么不選擇后者呢?即便他于2003年度獲得了“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我也覺得,對于范穩來說,炮制于書齋的作品,仍遠未達到他理應達到的文學高度。
但很顯然,沒有任何一個外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2002年我回昆明工作定居,在一家報社主編文學副刊,再見到范穩時,他已經不是早年的那個白面書生了。問題他近些年在干些什么,他還是綿里藏針,只淡淡地說“混跡”于藏區。當時我就在想,這黑黝黝的家伙,下一部作品必將驚世駭俗。果然,2004年初,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長篇小說《水乳大地》,并入圍第七屆茅盾文學獎,雖未最終折桂,但正像外界所評論的那樣,因為書中“有藏傳佛教的活佛,納西東巴教的代表,基督教的傳教士;有紅漢人的干部還有不懼天地鬼神的康巴漢子,以及西藏土著宗教苯教鼻祖的魂靈,小說就是在這種宗教和現實交錯、多種民族混居、多種文化相互沖撞與融合的氛圍里,打造出了一系列慘烈而有光彩的故事和性格突出、生動可見的人物形象。”此書因此轟動文壇。兩年之后,2006年6月,人文社緊接著出版了他的《悲憫大地》,責編推薦說:這是繼《水乳大地》之后推出的第二部描寫藏區宗教、歷史及民族文化的長篇小說,“該書依然血性、剛烈、傳奇、莊嚴;依然堅韌、虔誠、魔幻、空靈。這是一部在我們的想象力以外的作品,也是一部超出我們日常生活經驗的作品。”然后到2010年6月,十月文藝出版社再出版了范穩的《大地雅歌》,他的“藏地三部曲”正式宣告完成。用他在《大地雅歌》后記里的話說:“我為自己感到慶幸,十年來我做了一樁有意義的工作,把三本書奉獻給我的讀者,供奉給那片神奇的土地。不是我書寫了這片大地,而是這片大地召喚了我。我服從了召喚,就像服從黎明的第一縷陽光,把我從黑暗中喚醒。”是的,在那布滿神靈的大地上,范穩書寫的沖動,可能永遠也不會不枯竭。以至于讀完“藏地三部曲”之后,我在報上寫了這樣一段話:“那片神奇的土地,始終暗藏至今仍難破譯的密碼,且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自由敘述與想象的巨大空間,成為當代文學史上一個不容忽視的題材高地——我說的是當然是藏地。關于西藏的書寫,盡管早已汗牛充棟,但客觀地說,或許只有范穩的“藏地三部曲”,才達到了長篇小說與那片神奇大地匹配的深度、廣度與厚度……歷經10年,范穩像個苦行的智者,執著而堅韌,以上個世紀上半葉外國傳教士在藏區傳教的經歷為切入點,孜孜探尋不同宗教的交鋒與對話,試圖以文學的形式還原那一段隱秘的歷史。”
“藏地三部曲”的完成,從某種意義上說,作為小說家,范穩已經完成了自身的蛻變與涅槃。我以為他會停留一段日子,靜享屬于自己的尊榮。但沒想到,2009年,當時的紅河州委為了給哈尼梯田申報世界自然文化遺產,聘請他、我、海男與北京的樂艷艷分別到紅河縣、元陽縣、金平縣與綠春縣各寫一本書時,他竟欣然應允。在紅河州的那些日子,聚首喝酒自不再在話下,但范穩給我所留下最深的印象,無疑就是:只要貼著大地行走,這家伙就活力無邊。
最直觀的例子是,今年,在中國人民抗戰勝利69周年之際,范穩又出版了長篇小說以西南聯大時期一代知識分子投筆從戎御敵救亡,并在不同歷史時期起落沉浮的長篇小說《吾血吾土》,既是史實,又是史詩,除了大量的案頭工作,更有八千里路云和月探訪,創作這部書的艱辛可想而知——為創作《吾血吾土》他蟄伏四年,查閱各種史籍,深入滇西地區,還采訪了多位抗戰老兵,并遠赴臺灣、日本等地進行創作采風——故而在對他與該書做專訪時,我寫了這樣的開頭:盡管深知,中華民族,歷來不缺“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脊梁,更不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的決絕與悲壯。但在范穩新出版的長篇小說《吾血吾土》中,讀到當年學子們從軍時曾經吟頌誦過的這首詩,我還是很難掩飾血管即將炸裂的沖動:“沒有足夠的兵器,且拿我們的鮮血去。沒有熱情的安慰,且拿我們的熱血去。熱血,是我們唯一的剩余。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你,我,誰都不曾忘記。”
漫說范穩,寫一本書也足夠厚重,打我必須收筆了。畢竟“小說”不是“大說”。作為30年的朋友,作為文學道路上的兄弟,我相信只要范穩繼續貼著大地行走,他的良知與情懷,必將還會給中國文學增輝,給同道兄弟們帶來溫暖。因為他還年輕。
責任編輯:韓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