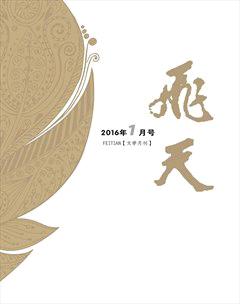異鄉記
1.風琴上的灰塵
十月的皖北已經微有寒意,天氣預報說,氣溫驟降,最低溫度為攝氏九度,風力3—4級。已是深秋,滿院子的楊樹葉在風里翻飛,我明顯感到了清寒,緊了緊衣衫,跟著豆老師進教室,開始我的支教歷程。
上課前,豆老師作了簡短介紹,從杭州過來,會在學校住半個月。下課時,同學們一下圍在我身邊,他們當中有幾個便顯得特別親熱,問我杭州的天氣是不是很熱,有沒有五十多度;杭州是不是有個西湖,水很清澈,像鏡子一樣;杭州的馬路是不是很干凈——這些大約是父母從杭州回來后跟他們說起的西湖見聞。我注意到班里有個男生,長得清秀,長長的睫毛撲閃著,總是遠遠地站在課桌旁邊,欲言又止的樣子。
再上課時,我便有意識地關注那個男生,從他的本子上知道了他的名字,郭小龍,他的眼里充滿了好奇,時不時有疑惑的神情。外面又起風了,教師里坐了五十個學生,比較暖和。等一下課,教室門一開,風從門外進來,我看到郭小龍不自覺地抱了抱肩膀。
走廊上,我拉住郭小龍:怎么不多穿件衣服?
郭小龍顯得很羞澀:不冷。
看你發抖,還說不冷,下午可得加一件衣服了。
郭小龍點點頭,我再想跟他說點什么,見旁邊一個女生,站在一邊,好奇地打量我。她穿著一雙拖鞋,一件白色的短袖T恤,胸前印著一只浣熊,一條褲子剛及小腿處,整個是盛夏的裝束。我問女孩怎么不多穿件衣服?女孩低下頭,悄悄地跑開去。
穿過走廊,剛想進辦公室,李老師從教室出來,跟我點頭打了招呼,一邊嘆氣搖頭,一邊往辦公室走。李老師五十多歲,從鄉村小學建立開始他便在這里任教,從學前班的拼音“啊波次得”到五年級的地理,他都教過。我夸贊說,你是全能將軍!“沒有辦法,我們農村小學老師少。”李老師感嘆一句。
進了辦公室,李老師告訴我,他班里的郭燕燕上課一直在哭,她爸爸不要她媽媽了。李老師是本村人,對村里每戶人家的情況了如指掌。他告訴我,郭燕燕的爸爸外出打工十多年,媽媽留在家里,家里五姐妹。男人外出打工之后,這個家就沒有團圓過。李老師感嘆:“在我們這個地方,要像你們那邊一樣,一家幾口團團圓圓地過日子,真是比什么都難!”
我們交談沒幾分鐘,郭燕燕就進來,一見我便哭開了,也不管我是陌生人,她就那樣一直哭訴著告訴我,她爸爸不要這個家了。
2011年,我開始采訪留守家庭。很多時候,留守者的訴說總是讓我酸楚難擋,好多次,睡在家里溫暖的床上,睡里夢里都是那些哭泣的聲音,醒來后久久無法入睡。
記得整理行李的時候,同學給我短信,她擔心我的這次出行又會給我帶來心靈創傷。短信說:其實我們都無法給予別人能量,即便貌似的力量,也都是虛弱的,因為那個時候,對方還不具備消化的能力,我們的所謂給予,或許反而是另外一種逼迫。不要讓自己太進入情景,任何時候我們都是旁觀者。
此刻,辦公室靜悄悄的,郭燕燕在抽泣,我看著瘦弱的她肩膀一聳一聳的,不是哭喊,是嗚咽。她的臉被淚水模糊,手上沾著鉛筆灰,一擦,臉更模糊不清。我把她拉過來,坐在旁邊的椅子上。
實在找不出恰當的語言來安撫她,但我不想讓她一直那樣悲傷。尋思中,瞥見左側椅子邊有一架風琴,沒有蓋子,布滿灰塵,黑白琴鍵因為天長日久,色澤有些模糊。我摸摸郭燕燕后背,拉過她的一只手,按了幾個琴鍵,想以此來平復她的情緒。幾個音符響起來,聽著有些哀怨。郭燕燕順勢一把抱住我的手臂,哭出聲來。我附在她耳邊說,大人的事,他們自己會解決的……摸著她瘦弱的后背,單薄的衣衫下一顆稚嫩的心。
李老師見此情景,站起來,摸摸郭燕燕的頭,扶著她的肩,慢慢地往辦公室外面走。才走了三四步,郭燕燕卻又回轉身來,站在我面前。
“老師,我爸讓我和弟弟跟他,我不想跟他,我要跟我媽媽。我媽媽窮,可是我不會離開我媽媽。我就算死了,也不會跟爸爸走,我會守著我媽媽。”仿佛是一段告白,又似乎是最后的傾訴。
李老師告訴我,郭燕燕常年不回家的爸爸有一次忽然回來了,背著老人跟妻子來到學校,來接兩個孩子。郭燕燕跟弟弟欣喜不已,長久不見的爸爸回家了,沒曾想卻把姐弟倆接到了朱集法庭,讓姐弟倆表態,跟爸爸還是跟媽媽,爸爸媽媽要離婚了,讓他們自己想好了……郭燕燕跟弟弟哭著抱在一起,跑出了朱集法庭,邊跑邊哭喊:“媽媽,我們死也不會跟他……”
郭燕燕的媽媽長年留守在鄉村,除了土地,一無所有。郭燕燕說:“寧愿跟著媽媽去要飯……”我費力克制著的情緒,不可遏制地被郭燕燕轟炸出一個缺口。在深秋的皖北校園,我看到淚水滴落在老舊的風琴上。
2.自行車上的童年
我跟豆老師說想去郭小龍家看看。豆老師猶豫了一下說,他爸媽都不在家——哦,他爸已經死了。我看著站在操場邊的郭小龍,跟他笑了笑,算是打招呼。郭小龍羞澀地走開去。豆老師又說,剛才在辦公室跟你哭鼻子的是他堂妹。說話間,一個女孩跑過,七八歲的樣子,腦后的馬尾巴歡快地跳動,而她身后,一個五六歲大的女孩,哭喊著姐姐跟在后面跑,撲通一下摔倒在地。我趕緊扶她起來,誰知女孩用力甩脫我的手,拿眼睛瞪我一下,又往前追了去。
豆老師嘆氣說,瞧瞧,這也是郭小龍的堂妹,郭小龍爸爸有九姐妹,叔叔伯伯家的孩子一大串……
走出校園,沿著一條灰塵撲撲亂飛的村道,我跟郭小龍并肩走著,郭小龍步子很快,我背著一個大包,跟著有點吃力。身后跑上來的郭燕燕氣喘吁吁,得知我要到郭小龍家去,顯得很開心,跟我絮叨著她跟郭小龍的關系。
“是俺哥,俺二伯的兒子。”
前面在修橋,我們從一側泥地里走,泥路凹凸不平,雖是晴天,依舊有些泥濘。郭燕燕停下來,后面跟上來一個小男孩,五六歲的模樣,是郭燕燕的弟弟郭春弟。我們幾個人混雜在放學回家的同學中,擠擠挨挨地過了那塊泥濘的道路,眼前便是一條筆直的村道。
郭小龍小跑著往前。我喊住他,讓他慢慢走。他停下來等我,見我到眼前了,便又很快地走起來。這個鄉村少年有著一雙深邃的眼睛,皮膚黝黑,臉上隱約有幾塊蟲斑,穿一件長袖T恤,一條青色運動褲,白色運動鞋在他腳底翻飛。這是一個陰天,看不見云層,天空是灰黃色的,不遠處的田野,農戶正在焚燒玉米稈子,大蓬青黃色的濃煙翻滾著往空中升騰,跟半空里厚厚的灰塵銜接在一起。
我跟郭小龍的話題從天空開始。郭小龍說,他想發明一個機器,像一張網,晴天的時候,把天空中的灰塵煙霧全部都收進去,這樣,“我們抬起頭來,就能看到藍天白云了”。等到夏天,很熱,爺爺奶奶去地里干活的時候,機器自動把網里的灰塵和煙霧都凈化,變成一朵一朵的云,飄浮在種田人的頭頂,“這樣,他們就不會感到熱了”。
走著走著,只剩下我們幾個。我這才知道,郭小龍家不在這個縣,是緊挨著的阜南縣。從學校到郭小龍家六七里路。我問郭小龍怎么不騎自行車,郭小龍笑笑沒有說話。一邊的燕燕搶著說:“老師,俺哥為了跟你一起走路,把自行車留在學校了。”
內心一陣感動。路過一個村莊時,郭小龍的臉色變得沉重起來,步子比剛才快了一些。在我的追問之下,郭小龍才道出了實情:緊走慢走地趕路是想早點回家去地里喊爺爺奶奶回來做飯,因為“家里來了客人,是我們老師,爺爺奶奶一定很高興”。而此刻的步子更快是因為,“俺媽在這個莊上”。
在郭小龍斷斷續續的敘述中,我得知郭家一段往事:郭小龍五歲那年,爺爺生了一場大病,為給爺爺治病,家里負債累累,連那頭耕田耙地的黃牛都牽去賣了。“俺奶奶一直哭那黃牛,舍不得。”郭小龍說到這里,神色黯淡下來。
郭小龍父親外出打工賺錢,不到三年,忽然得病去世了。“俺還記得俺爸走的時候跟俺說,等爸在杭州找到工作賺到錢了,給爺爺治好病,俺家有余錢了,就帶你去杭州看西湖,去西湖劃船。”郭小龍說,他爸也不知犯了什么病,沒等他媽趕去杭州,人就沒了,在杭州給燒了。
父親去世不久,母親改嫁到鄰近一個莊上,“俺爺說俺媽還懷著弟弟”。
我們行走的這條村道,左側是一條河流,只是已經干涸,河床上長滿了荒草,還有村人丟棄的垃圾。村道右側是白楊樹林,村子就在這個樹林里。皖北農村的住戶大都分散在這些高大的楊樹之間。依稀是草垛、休憩的黃牛,三兩只小雞在踱步。
我不由自主停下腳步,看河對岸的村子,一樣的白楊樹,一樣堆得高高的草垛,偶爾一只雄雞高昂地啼鳴,從一個外人的眼里看來,安逸、寧靜。我問郭小龍,哪個房子是你媽媽家的?郭小龍徑直往前走,頭也不回:“我不會踏進她家一步……我恨她!”
一定能夠找得到很多理由來給郭小龍母親合理的解釋,為何忍心拋下五歲的兒子,帶著身孕另嫁?而少年郭小龍顯然還無法理解成人世界的復雜。一個年輕的女子,留守三年,含辛茹苦侍奉老人、哺養小孩,盼不到夫妻團聚、豐衣足食,卻在一夜之間成為寡婦。家里有一個病倒在床的老人,破敗的泥坯房子,看不清的天空……這一切或許都是她易主的理由。后來我從側面了解到,郭小龍母親給出的說辭是:她的肩膀已經垮了,再也挑不動擔子。她現在跟丈夫在一起,又生了兩個孩子,夫妻倆在田間地頭刨食,“不覺得苦,只要一家人在一個窠里”。又說,當初郭小龍父親外出時,她就竭力反對,因為她不想獨自一人留在家里,“像葬在樹林里,永世不得翻身”。只要“一家人在一個窠里”。——最低的生存要求,也不見得能夠達到。
我還沒有從郭小龍家的情景中回過神來,卻聽前面傳來哭聲。“是俺妹。”郭小龍說著往前奔去。我們幾個也跟了過去,卻見兩個女孩摔倒在地,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壓住了她們的腿。郭小龍把自行車扶起來,我這才想起,剛才在校園看到過這兩個女孩,一個在前面跑,一個在后面追,摔倒后我扶她起來,她瞪了我一眼——八歲的姐姐郭豆豆,上二年級,五歲的妹妹郭愛愛,學前班。每天,姐姐用自行車載著妹妹去學校。剛才,妹妹在自行車后面鬧脾氣,不小心把腳夾進輪胎的鋼絲圈里了。
也是郭小龍的堂妹,郭小龍小叔的兩個女兒,“家里還有一個弟弟,一歲半”。
安撫好郭豆豆姐妹,我們繼續往前。知道我要到郭小龍家去,郭豆豆特別高興,他們幾家住一個莊,離得不遠。郭豆豆不愿再騎自行車,她希望跟我們一起步行回家,妹妹郭愛愛卻不干了,她坐在后座,兩腳亂蹬,非得姐姐趕緊帶她回家。郭豆豆推著自行車,不時地看我,那樣的眼神——過去大半年,我依然能夠回想起來,卻依然無法準確說出那眼神透露的信息。歡喜?驚訝?信賴?惶恐?似乎都不是。
我本想替換郭豆豆推自行車,減輕郭豆豆的負擔,這樣也可以加快前行的速度,誰知郭愛愛更加狂亂地折騰起來,非要姐姐騎上去,她要回家。無奈,我只得把自行車把手交還給郭豆豆。見妹妹吵鬧得厲害,郭豆豆摸摸妹妹的臉,又幫她擦眼淚——郭豆豆像母親一樣,把妹妹的頭摟過來。妹妹坐在車上,姐姐個子又不高,妹妹想在姐姐懷里窩一下的舉動沒完成。郭豆豆又摸摸妹妹的臉,緊走幾步,跨上了自行車,慢慢的,身影變小了。我看到妹妹把頭靠在姐姐后背,緊緊地抱住姐姐的腰。妹妹的兩腳晃動,自行車也跟著左右晃動起來。
郭燕燕快嘴道:俺嬸子又得打豆豆了。
我問為什么,燕燕搖搖頭說不知道,反正嬸子就愛打豆豆,打愛愛更兇。
正說著,一直默默跟在后面的弟弟插嘴:“嬸子抓俺妹的頭發,都這一把。”燕燕弟弟在路邊抓了一把枯草,晃動著說。
再細問,幾個孩子嘰嘰喳喳地說起嬸子的事來,說嬸子總是無緣無故地打豆豆跟愛愛,白天打,有時半夜打,“打愛愛最兇,有一次,俺嬸子都打暈死過去了,俺奶就給掐手腕、掐人中、掐腦門,才回過氣來”。
八歲的小女孩,自己都還不知道冷暖,卻要帶著五歲的妹妹去學校,在我看來,已經夠乖巧的了。郭小龍又告訴我,郭豆豆六歲就開始學會騎自行車,那時父母都不在家,跟著爺爺奶奶過,白天她獨自在家照料妹妹,晚上還得料理妹妹睡覺。郭豆豆上學前班時就帶著妹妹去學校,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那逐漸遠去的自行車,自行車上兩個年幼的孩子,她們的童年的背影……
3.掌心里的驚喜
從大路拐進一條田埂似的小道,再過一座低矮的橋,便進了村子。高大的白楊樹下零散著幾戶人家,典型的皖北鄉村風貌一展眼前,一條同樣干涸的村中小河把村子分割成了兩半。還沒進村,聽得身后汽車響,我們幾個閃開去,一輛面包車從我們身邊駛過,在前方五十米處停下,接著便聽到鞭炮炸響。還沒回過神來,卻見郭小龍第一個飛奔向前,郭燕燕姐弟倆也跟著飛奔而去。村子里呼啦啦出來七八個男女,齊刷刷地往面包車方向跑,定睛看去,見面包車上下來一個人,正往人群里撒東西。在這個安靜的鄉村,“哄搶”的熱鬧場景有些突兀,我拿眼尋找郭小龍和郭燕燕姐弟,卻見幾個人正橫沖直撞在撿拾,郭小龍還跟一個胖胖的中年婦女爭奪什么。我大聲喊郭小龍,郭小龍從中年婦女胳膊肘底下伸出頭來,看我一眼,羞怯在他臉上蕩然無存,有的是興奮、激動,夾雜著莫名的狂喜。
面包車噴出一蓬烏黑的尾氣開走,人群慢慢地散開來,陌生的言語在這個村子里散開去。郭小龍飛快地跑過來。我發現他的鼻孔流出血來,趕緊拿出紙巾要幫他擦,他卻一扭頭,用手背擦了下。
“你們在搶什么?”
郭小龍笑了笑,羞怯又回到他的臉上,他慢慢地伸出手來,在我眼前攤開手掌,是滿滿的一手掌糖果,紅的綠的金黃的糖紙泛著亮光。
“老師,給你。”
原來那輛面包車是來定親的,鞭炮,包括在路上撒的糖果,都是鄉村的習俗。我從郭小龍手掌心拿過一顆糖,他的手指粘糊糊的,有新鮮的血漬。
我用紙巾幫他擦了擦手指,“被三嬸踩到手指了,她胖,重得很,我手指抽不出來……老師,你嘗嘗,甜不?”
我看著郭小龍,他剛擦過鼻血的地方依舊有血漬,因為搶奪時的奮力,使得他的臉紅紅的。我剝了一顆糖,想塞進他嘴里。
郭小龍別開頭,“老師,我搶來就是給你吃的,你一定要吃!”
郭燕燕和她弟弟也各自把糖遞過來。
“老師,吃。”
“老師,吃糖吧。”
鼻子酸酸的,我終于抑制不住落了淚。幾個孩子定定地看著我,他們不明白,老師吃著糖卻為什么哭了。
我們先進了郭小龍爺爺家。爺爺跟五叔同住,郭小龍事實上是寄養在五叔家的。
進門,是一個小院子,院子地上散落著玉米棒、紅薯等,一只深咖啡色的狗在披屋里蹦跳,也不癲吠,只是蹦跳。郭小龍說,是他爸爸從杭州帶回來的,前段時間生病,差點死了,剛緩過勁來。郭小龍把手伸過去,狗狗親熱地舔起來。一個胖墩墩的小孩搖晃著走出來,額頭鼻尖顴骨處烏青斑斑,嘴唇上還有一塊血漬,還沒結痂。見到陌生人進來,孩子哇一聲哭了。郭小龍趕緊過去安撫。屋里出來一個年輕女子,肚子凸出來,見孩子在哭,擺動身子過來。見到我,嘴角牽了牽,算是打招呼。
郭小龍稱呼她“五嬸”。我欠欠身子,也跟著郭小龍稱呼一聲,五嬸。
五嬸大約二十八九歲光景,臉色顯得有些蒼白,鼻子上有著懷孕女人特有的紅,點點滴滴的紅色痘子。我問五嬸預產期幾月份,五嬸的手放到腰上,走了幾步,顯得有些費勁。
“就這個月了。”原來就要生孩子了。
我們站在院子里說話,郭小龍跑著出了門,說去找爺爺奶奶回來。我說不用了,我這就回學校去。郭小龍哪里肯依,一溜煙就出去了,丟下一句話:“老師,你等我!”
郭小龍一走,我站著便覺得有些尷尬,因為事先沒有準備來拜訪,兩手空空地來到人家屋里,總覺得很唐突。
“看我,什么都沒給孩子帶。”我發自內心地不安。
五嬸笑笑說,不用帶什么的。又問我從哪來,是干什么的。
我們站著在院子里聊開了。這中間五嬸始終沒有邀請我進屋子,薄薄的涼意。在我跟五嬸站著的半個多小時里,我了解到五嬸原來也是留守婦女,今年二十八歲。小胖墩是她兒子,今年三歲。丈夫在外打工,“他說趕得及就回來,趕不及就不回來了”。
我說,你一個人生孩子,沒人照顧,真不方便。
五嬸想了想,說,俺農村人,不都這么過的么?
我問五嬸孩子他爸出去幾年了,五嬸說:“結了婚就出去了。”
想起那首新民謠:“月兒彎彎照新房,十家新房九家荒。新郎打工去城市,留下新娘守空床。新娘新娘在家忙,家里家外挑大梁……”
我問五嬸,生完孩子之后打算怎么辦?五嬸不假思索地告訴我,等孩子能走路了,就交給他爺爺奶奶帶,她也要出去打工,“這那的開支,他爸一個人太累了”。
我問五嬸,已經生了一個兒子,怎么想到再生一個?誰知我的話一出口,便被五嬸打斷:“這飯不讓人吃飽,錢不讓掙,生孩子是我們自家的事,總得讓生吧?”不知怎么會有這樣的想法?我見情勢不妙,跟郭燕燕對視一眼。這小女孩很機靈,趁勢說,“五嬸,俺帶老師去豆豆家看看。”五嬸愣了愣,瞥一眼郭燕燕,忽然又對我說:“俺還生,三個五個的,憑什么人家能生,俺就不能生?”
我倉皇離開五嬸的院子,五嬸牽了胖墩兒子的手,進屋。
4.“從來沒有記者來我們村”
剛過了橋,便見到了她——很多次,我希望自己能夠用飽滿的熱情,為這位留守在家的女人寫一篇樸素的文章,她是我筆下的主人公。可是,當我鋪開資料打算完成有關留守婦女的紀實作品時,很多場景次第來到我眼前,校園、村莊、孩子,一一跳進我的腦海。豆豆媽媽留守在家近七年。在我的走訪經歷中,七年的留守時間并不算長,可是,這個女人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以至于我回家之后好幾次都夢見她,夢見那兩個夜晚,我跟她隔墻而臥、各自翻身、各自心懷感嘆的不眠之夜。
說話間,我們來到豆豆家門前的道地,地上全是樹葉,細碎的麥桔稈,還有干枯的楊樹枝,看起來不像是住戶人家的道地,倒像是閑置不用的村中空地。聽到聲音,郭豆豆從屋里走出來,怯怯地看著我。
我注意到郭豆豆的眼睛紅紅的,剛哭過的樣子,不知道豆豆回家后發生了什么。我看到她媽媽拿眼睛瞟了豆豆一眼,豆豆怯生生地往門里縮了去。
我夸豆豆乖巧懂事,人還沒自行車高,卻每天要帶妹妹去上學,又說豆豆很疼妹妹,云云。誰知她媽媽嘆息一句:“生在我家里,是她沒福氣,我家這幾個孩子,都是沒福氣。”
屋子里凌亂不堪,地上除了已經干燥的泥土沫子,還有很多樹葉麥桔稈碎末,鞋子東一只西一只,沾滿了灰白的泥土。一張小矮桌上散落著幾個塑料玩具,已經破碎的鴨子、水槍、襪子、梳子——這間屋子多久沒有清理過了呢?豆豆媽拖一把椅子招呼我坐下。我這才知道她剛才打了女兒幾個巴掌——她的輕描淡寫讓我吃驚,仿佛是習以為常的事。想象不出,她干多了粗活重活的手掌是如何砸在豆豆稚嫩的臉上的。我有些氣惱地說了一句,帶著明顯的責備,我說,這么小的孩子,已經這么乖了,你也真下得了手!
她愣了愣沒有說話,走進里屋,片刻便出來,忽然換了話題,說本來兒子睡了她也可以去田里,但是怕陌生人進村看到大人不在家,把孩子抱走。
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接上她的話題。等她出門拿掃把時,我悄悄問豆豆怎么回事,豆豆猶豫著看了看門外,羞怯地笑了笑,搖搖頭。郭燕燕插嘴說,豆豆從來不說——從來不說,是不想說?不愿說?還是不敢說?我摸了摸豆豆的臉,站起來想離開,去田里看看郭小龍,誰知一頭蓬亂頭發的妹妹郭愛愛在旁邊抓住我的背包帶子,“老師,你不走嘛,老師,你不走嘛……”她顯然也剛哭過。想起包里有個蘋果,掏出蘋果時,發現自己犯了個錯,幾雙眼睛齊刷刷地看著我手里的蘋果——就在剛才,陸續進來了幾個孩子,是郭燕燕的同學,她們看著蘋果,欲言又止。我讓郭燕燕拿了一把刀,把蘋果剖開,一片一片分給大家。吃著蘋果,我們都笑了。豆豆媽忽然進來。豆豆跟愛愛趕緊把手往身后藏,她媽媽壓低聲音說:“敢吃涼的,肚子痛別跟我說!”
走出門外,后面跟著這些孩子,不遠處的樹林間,一個身影朝這邊走來,是郭小龍爺爺。他衣服上粘了一些稻草衣、草屑、泥土,見我站著等他,急急地走上來。我喊了聲爺爺。爺爺很熱情地對我笑笑,說怠慢了怠慢了,沒得空做飯給我吃,他得拉個電瓶三輪車去田里。
這當口,孩子醒了。豆豆媽進屋把孩子抱出來,一雙眼睛葡萄一樣,水靈靈的。因為剛睡醒,似乎還在夢里的樣子,看著我陌生的面孔,想哭又忍住了。我打算離開,豆豆媽竭力挽留我在她家吃中飯。其實我已經很餓了,嘴里卻推辭著說不餓。往前走兩步,郭愛愛追在后面跑來,“老師,你咋走了呢?老師,你咋走了呢?老師,你還來嘛,老師,你不走了嘛……”一直追在我后面,我返身抱起這個五歲的孩子。
我說:“就在你家吃中飯了。”
豆豆媽笑了笑,“我這二妮子,平時見了生人很兇,不理睬人,你看她喜歡你呢。”
中飯是面粉南瓜糊糊,一大碗,一大筐子饃饃,都是豆豆媽自己做的。郭小龍已經從田里回來。一張低矮的小桌上擺滿了碗筷,郭小龍、郭燕燕姐弟、郭豆豆三姐弟,加上五嬸那個胖墩墩的男孩,七個孩子,嗷嗷待哺的情形。喝光一碗再去盛一碗,很快就見了鍋底。豆豆媽告訴我,平時郭小龍郭燕燕姐弟也常在她這里吃飯,“他們幾個家里沒人做飯,有時就不吃了,我看不過去,就招呼著一起吃一點。”
席間,這個的碗碰到了那個的筷子,那個的筷子戳到了這個的眼睛,小矮桌上吵吵鬧鬧的,盡管跟我這個陌生人坐在一起,他們還是忍不住地計較起來。
“你說這一大家子的人,誰見了心里不煩悶?”豆豆媽收拾完桌子洗碗,一大水盆碗。燕燕在一邊幫襯著,一不小心打破了一個碗。豆豆媽站起來,嘆口氣,“不知道這日子什么時候是個頭……”
離開的時候,我想偷偷放一點錢在豆豆家柜子上,不知怎么的被發現了。豆豆媽很生氣,說我看不起他們,他們家是窮,也不至于讓人掏吃飯錢——這倒叫我生出尷尬來。我反復解釋老家的習俗,第一次不能空手去別人家吃飯。“你那是什么規定喲!我們這要是人家上門,不留吃飯,那得多傷人嘛。”各說各的理,一來二去,兩人反而熱乎了起來。我說你就收了吧,你看,你在北方,我在南方,我們兩個人,要不是有緣,怎么會走到一起,在同一張桌上吃飯呢?再說了,我也不一定以后常常會來這里,我們以后也許永遠不見面了,你在這里老,我在杭州老——忽然,豆豆媽抓著我的手,眼睛紅起來。她說她快要撐不住了,這日子真是沒法過了。“我想走,我想離開這里,可是,你看看這些孩子……哪是孩子,都是一根根繩子,把我給捆住了……我哪里都去不了。你是記者,我就跟你說說,心里好受一點。我們這個地方,荒著呢,從來沒有記者來問過我們的事。”
5.誰在廣場上嘭嚓嚓?
傍晚,我風塵仆仆地回到住地。王依跟劉小云都加班,鄉政府大院里,一臺播放機正唱著刀郎的歌:“2002年的第一場雪,比以往時候來得更晚一些……”隱約看去,一些人在跳排舞。我對中國的排舞常常心生茫然。在這個小小的院子里,我忽然想看看到底誰在開心地跳舞。
露天舞場上,分成三排,每一排有五個人在扭著身子,她們動作輕柔、剛柔并濟的意味,把中國近幾年推廣的排舞演繹得十分到位。而我卻想起了豆豆和她的妹妹他的媽媽,這個時候,她們在干什么呢?想起吃中飯時,豆豆媽告訴我,這兩個女兒都惹她生氣,中午郭豆豆帶妹妹回家時,妹妹身子扭動得厲害,自行車歪進了水溝。雖然水溝沒有水,但是泥土還潮濕,兩姐妹身上還是粘了一些黑灰的土,她就著水龍頭把她們的衣袖后背都洗了——是直接穿在身上洗的。難怪吃飯時,愛愛伸出手臂,拉扯了一下衣袖,嘟囔了一句:“媽,涼……”媽媽拿眼神剜二妞一眼,二妞馬上噤了聲。
這一刻,小小的鄉政府廣場,從加班的劉小云跟王依她們辦公室透出來的亮光,燈光灰暗,可是足以撐得起一場中國式的廣場舞。左腳往前,右腳跟上,身子往左偏,雙手跟上,腰部配合臀部節奏,后背挺起來,眼睛看前方。這種種,讓人頓生凄楚。什么時候,我們的廣場舞成了廣譜抗菌式的精神撫慰?來,來,來,音樂開始,跟著節拍,跳起來……忘掉所有煩惱……
幾個熱情的女子,我跟她們一起在食堂吃過面湯,她們熱心招呼我加入,“來吧,一起跳舞,來吧,一起跳舞……”
我逃似地離開大院,來到清冷的屋子。棉被柔軟,粉色的被套、粉色的床單,配上王依粉色的蚊帳,在電燈光線的映襯下,顯得溫馨,甚至有浪漫的色彩。我坐在床上,記錄當天的走訪,從學校的點滴,到去郭莊的見聞,我甚至拿出手機刷微信,“養生從早餐說起”,“一生一世一雙人,半醉半醒半浮生”,“心靈雞湯:你為他付出了所有”,“想要在直銷行業里成功,必看”。翻過一條,很快跳出另一條——這些完全跟我無關的信息,在這個遠離家鄉的夜,瞬間安慰了我,成為我的心靈雞湯。
可我知道,無論做什么事,我都只是在排斥一件事,在忘記一個人——我承認,在這之前,我已經完成了二十萬字的留守婦女非虛構作品,往功利一面說,我其實不用再面對任何一個留守婦女,我現在只是在完成我的另外一部作品的素材積累,留守兒童跟老人——可是,我的面前、我的本子上、我的思緒里,卻全都是這個女人。
一頭濃密的黑發,腦后一根馬尾辮,長及腰際,額前黑密的劉海,一雙眼睛——怎么說呢?她的眼里滿含著什么說不清說不盡的內容。即便我跟她已經坐下來說了一些什么,但是,那都是她面對一個陌生女人的客套,一個當地住民對于偶爾路過的另外一個女人的鄉村最樸素的情愫——她封閉著自己,可是眼睛卻時不時泄露著巨大的秘密,無論她是否愿意告訴世人,那些欲說還休的情緒已經突奔往前,呼啦啦地來到她的面前,爭先恐后要向一個陌生女子訴說什么。
方格子,在《收獲》《人民文學》《花城》《天涯》《上海文學》《青年文學》《江南》《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 等發表、轉載中短篇小說近百萬字,作品兩次入選中國小說學會短篇小說排行榜,入選多種年度選本。出版短篇集《錦衣玉食的生活》《誰在暗夜里說,冷》,中篇集《冥冥花正開》,長篇非虛構《留守女人》《他鄉是故鄉》,長篇童話《月亮上的媽媽》。魯迅文學院第14屆、第28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現居浙江富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