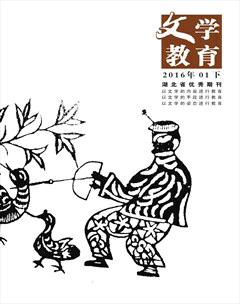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旨歸
李文亮
以“現代性”為通論的意識形態正以“工業社會”為載體在全球蔓延。受技術革新的影響,美好的永遠是在未來,“進步觀”取代了“是非善惡觀”,它以是否新潮的意識,將舊有的思想觀念無情地拋棄。它使得人不再追求“好壞”、“善惡”、“正義”的永恒價值,而心甘情愿地將思想流向于現代性的歷史觀念,即徹底的歷史虛無主義。“這種‘歷史觀念因此無情地沖刷著人心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濃度,導致人類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釋化和空洞化。”它使得每一個個體均可以在拉平了的社會中獲得一種活動的自由狀態。現代性以這么一種歷史虛無主義推動了人的自由的實現,但它卻是走向了一種人性墮落的自由。因此,列奧·斯特勞斯痛心疾首地指出:“這種墮落的自由主義宣揚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開心而不受管教,卻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質高貴、出類拔萃、德性完美。”也因為此,人類自我消解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完整人性,喪失了審美的能力,再也無法參與到人類文明不斷進行的對話之中,人的精神生命進入了一種自我封閉。
改革開放的日趨深化,使得當代大學生群體在現代性思維的影響下也不可避免地日益呈現出這一種狀態。也基于此,舊有的建立于威權主義基礎上的道德說教式的、空洞化的、教條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被現代性無情地解構,甚至成為了被奚落、被調侃的茶余飯后的調味劑。如何在現代性思潮的影響下重塑大學生的精神世界,塑造大學生的整全性人格,這是時代給當代針對大學生所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所提出的重大課題。列奧·斯特勞斯針對美國社會的“日漸沉淪”,提出了“回歸古典,重建自由”的思想理路,這是對當代中國思想政治教育界學人的重要啟示。以儒家“君子”理念提煉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價值目標,可以為思想政治教育創獲一條延承傳統、緊貼時代的思想路徑。
一、“仁”——“君子”人格的價值核心
《論語》一書共11076字,提及“仁”的理念有65處,“仁”字共出現有120多次。因此,自古及今,均有學人認為,一部《論語》,即為“仁書”。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將“仁”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由此可見,在儒家看來,一個人只有具備了“仁”的品格,才能被稱之為君子。李澤厚甚至認為,孔子以仁學結構(包括四個要素:血緣基礎、心理原則、人道主義、個體人格)消化掉或排斥掉外來的侵犯、干擾,而長期自我保持、延續下來,建構形成了漢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影響并指導著漢民族每一個社會個體的社會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解釋何為“仁”時,從來不會界定“什么是仁”,而往往代之以“如何做才稱得上仁”式的回答: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論語·學而》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后獲,可謂仁矣。”《論語·雍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論語·雍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論語·顏淵》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論語·顏淵》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論語·憲問》
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論語陽貨》
由此可見,儒家所倡導的“仁”并不是讓人從概念上把握,而是要求在現實生活中去體悟,去習得“仁”之精髓。
二、“為學”——通過對“仁”的理念修習而明君子之道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語》開篇即明確指出,“學”乃“君子”人格形成的必由路徑。只有通過“學”,才能真正獲得以“仁”為 核心的諸如“仁、智、信、直、勇、剛”的君子人格,如果缺乏了“學”的路徑,君子人格則會出現歪曲:“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那么,究竟應該要學些什么呢?孔子以“六經”為范本而展開的教學可以給予啟示。“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對于《詩》的學習,使人獲得一種溫柔敦厚的人生品格。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儒家看來,個體只有始終保持溫順和藹、寬懷待人、誠實厚道的人生品格,才能在人與人的交流溝通中更容易獲得他人的認可。因此,孔子才有了“不學詩,無以言”的人生感悟。學于《書》,則可收獲疏通知遠的人生坦途。中國社會的文化意識中有著深厚的歷史感,更在乎于在歷史中找尋生命的存在感。因此,對于歷史的學習,是中國人在學習過程中重要的價值向度。中國人從來都認為,歷史是對于人生經驗的總結,一個人如能善于學歷史,便能曉人事,知人倫,進而在習得的基礎上讓自己的人生道路走得更為通達、更為遠闊,甚至能進一步的以自己的人生經驗,啟迪后人。因此,才有了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歷史情懷。
自周公“制禮作樂”,而使中華文化有“禮樂文化”之名。因此,儒家特別看重“禮樂”的修習。從“禮”的視角而言,孔子曾言及“不學禮,無以立”,也就是說,一個社會人,只有學禮進而知禮,才能屹立于天地間。而從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來看,荀子甚至認為禮分別是天地、先祖、君師的根本(筆者按:三者分別指向了天道、人道、治道的思想層面)——“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孔子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一個人通過學禮而尋天命以敬畏之,尊崇之;通過知禮而畏父母大人之言以孝順之;通過守禮而畏圣人之言以心安之。只有這樣,當個體在接人待物、行為處事之時便可做到“恭儉莊敬”,那么整個社會也便自然而然實現了秩序的有序性。
如果說,通過“學禮—知禮—守禮”讓個體在社會活動中能清楚地定位自己,從而做到恭儉莊敬狀態下的安分守己。通過對于“樂”的學習,則可達到內心的安和。《禮記·樂記》指出,“德者,情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荀子也曾指出,“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這正是音樂藝術帶給個體的一種心性的陶冶,從而獲得了個人修養的提升,推動了個體生命的圓融。此即學于樂所帶來的“廣博易良”。當個體擁有了“廣博易良”的心性修為,與其說他會因為現實生活中的暫時困惑、迷茫、無助而陷入到一種極端狀態,毋寧認為他能在一種平和的心態中通過自我的反思尋得人生逆境中奮起的精神良方,走而走向生命之路的通達。
當然,儒家如此之重視對“禮樂”的學習,其最終的價值旨歸在于政治目標的實現,具體表現為在推動個體對于“禮樂”的學習中,實現天下大治——“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最后,君子必學于《易》。自古以來《易》便被賦予了“群經之首”的歷史地位,因為“易為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通過對《易》的學習,才能真正懂得人生,建構起完全意義上的精神生命。“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兇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要實現人生的價值,首先應該要站對位置,同時在對待人事之時也應懂得世間沒有絕對平等,因此,就應當要轉變自身的觀念,堂堂正正地做好自己。此即孟子所言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人生總有順境與逆境,在逆境之時,不要哀怨、過多牢騷,以淡泊之心求奮進之道;在順境之時,也應懂得謙卑和善,善待他人。如此,人生則無過無悔矣。這也就是《易》之所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三、踐履——“君子”人格在社會實踐中的體悟
儒家從來不會將君子人格的修成僅僅局限于“理論的學習”,毋寧說儒家更重視個體在社會實踐中體現其人生的價值。“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在孔子看來,理論式的學習,即使再多、再精妙,如果無法在社會實踐中體現出個體的價值,那也是無用的。因此,必須要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能明于人倫之道,才能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體悟到“仁”的真正內涵,成為現實中為他人、為社會、為歷史所認可的翩翩君子,并進而以其君子之德行對社會民眾有一種循循善誘之態,推動整個社會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諧。
總之,儒家所倡導的“君子”理念,是十分注重個體的整體人格的培育的,同時,儒家建構了一條培育君子人格的清晰路徑。大學生群體作為承載著中國社會不斷發展的精英主體,在其日漸沉淪為“碎片化、平庸化甚至是虛無化”社會群體的今天,真正賦予其以整全性的人格教育日益成為時代的艱巨任務,而儒家君子人格的培育,恰恰可以提供重要的經典啟示。
[本文系廣西財經學院2014年度黨建與思想政治教育課題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廣西財經學院防城港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