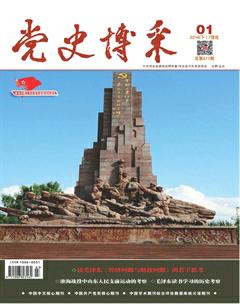論黨員干部在學雷鋒常態化轉型中的重要作用
馬薏雯
[摘要]本文通過文獻資料法、專家調查和邏輯分析等方法,探討了黨員干部在學習雷鋒常態化進程中的動力機制和重要作用。研究認為,學雷鋒常態化轉型是我國政治——文化運動的必然結果。黨員干部是社會政治運動與文化發展規律協動的關鍵,是學雷鋒常態化轉型形成歷史合力的保證;黨員干部是政府精神文明建設高度的代表,是衡量信仰體系先進性的尺度,是加快當下公民道德體系建設的重要環境和感召。
[關鍵詞]雷鋒精神;常態化;轉型;
1、雷鋒精神與學習雷鋒常態化
1.1、雷鋒與雷鋒精神
當我們穿行在中國近現代苦難與希望交織的歷史中,那些已經逝去了的,跋涉在民族求真、求善和求美歷程的先行者總會浮現在我們眼前。他們以鮮活的生命承載著民族史詩般的求索,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符號和精神標桿,照亮和重塑著我們這個民族的心靈史。在當代的民族記憶中,雷鋒就是這樣的一個典范;雷鋒在平凡的崗位上,在日常的生活中,他成長并抽象為中華民族歷史進程中一個不可磨滅的文化符號。雷鋒現象是歷史的偶然嗎?基于哲學與邏輯的范疇,這一問題也可以轉化為:具體、生活和有限的雷鋒是如何進入抽象、精神和無限的符號系統的?學者吳若增認為,正是由于“雷鋒已經成為了道德美的典范和人性美的化身”,才使其經久不衰[1]。陶東風更清晰的指出了這一路徑,“一種道德品質只有普世化、抽象化之后,才能獲得超越時代和民族的有效性”,但其隨后也指出這種升華與抽象所形成的單向性局限:這種提升后的品質與道德,“已經不再是當初構建的那種具有具體內涵的品質與道德,雷鋒也不再是當初塑造的那個雷鋒了”[2]。由此看來,學習雷鋒首先必須厘析兩個層面的問題:學習雷鋒同志和學習雷鋒精神。焦正安指出,雷鋒是新中國進入建設時期的優秀人物,但“雷鋒不是神,而是中華傳統文化精髓在一個英雄身上的集中反映”,而雷鋒精神卻是源遠流長的,是其先白求恩、張思德、時傳祥等及其后焦裕祿、孔繁森、郭秀明等好人群像共同構建的精神文明體系[3]。周楊的觀點殊途同歸,認為二者的關系是“雷鋒精神是以雷鋒同志命名的、以其體現的精神為基礎的、在廣大人民群眾創造的偉大實踐中不斷豐富發展的、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敬仰和追求的崇高精神文化”[4]。因此,活在當下的人的學雷鋒活動,必須實現“學習具體、生活和有限的雷鋒同志”和“學習抽象、精神和無限的雷鋒精神”的統一,認識到雷鋒同志是雷鋒精神的具體體現。只有抓住了不斷自我完善與發展層面的雷鋒精神,我們才能看清楚所謂“雷鋒過時說”的膚淺與蒼白,才能痛擊所謂后現代“解構雷鋒”的虛無與浮躁。
1.2、社會文化轉型與學習雷鋒精神常態化
通過上述的辨析,我們看到有限的雷鋒進入到無限的文化符號系統具有路徑的可能性,但這仍不足以回答更深刻的問題:雷鋒現象出現的必然性是什么?這一問題不僅指涉新中國人民群眾進入文字書寫的歷史符號系統的進程,也直接關聯到當下學習雷鋒常態化的實踐。誠然,歷史總是由偶然事件組成的,但這并不能成為否認歷史自有其內在邏輯的理由。以學理和邏輯見長的劉澤華對此進行了深刻的揭示,他認為,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是由王權主義統攝的超穩定結構。在君尊臣卑的的權力下行架構中,臣民是不可能具有所謂“獨立人格”的,故很難以大寫的人而成為歷史的符號,但這種剛柔并濟的架構依然不能扼殺思想文化的火花。他指明,政治與思想文化各有其運動規律,政治因社會需要建立秩序而產生,其遵循的是政治運動同一化規律;而思想文化運動卻有著內在的多元化動力,無論是認識論主體的主觀多樣性亦或知識的邏輯性,都決定了思想文化最終將沖破一切障礙沿多元化的方向逶迤而行[5]。根據這兩個范疇運動規律的矛盾來分析,我們也能夠意識到,新中國的建立客觀上確立了人民群眾的主體性,為國民“獨立人格”的普遍形成奠定了基礎,為新文化知識邏輯的展開開辟了道路,故雷鋒等國民群體的歷史涌現既是王權主義架構崩潰、新政治架構轉型的要求,也是新文化知識邏輯、國民意識、獨立人格普遍生成的文化多元化運動規律使然。同時,分析這一矛盾,我們也能夠認識到,政治民主的進程推動歷史符號系統的民眾化,反之,文化思想的自由又保障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最大實現,而其中也隱含了這樣一種文化運動的歷史邏輯。在這種轉型時期,雷鋒精神本身也必然更多的從泛政治化層面轉向文化運動對真、善、美等普世價值和人類共有崇高道德的追求。我們認為,當前的學習雷鋒“常態化”的歷史轉型正是我國政治運動與思想文化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對此,何懷宏寫道“從動員式道德走向非動員式道德,也意味著從一種非常時期的道德走向一種正常時期的道德,從一種要求高蹈的道德走向一種堅守底線的道德,從一種價值和規范統一的道德走向一種區分價值和規范的道德”[6]。在此種意義上,我們對學習雷鋒常態化轉型有了一種有根基的認識,而這種轉型也為個體的、平凡的生命在倫理道德上的升華預留了個性化、可創造的和可超越的可能性。按照學者王強的解讀,這種轉型恰恰吻合了馬克思的政治革命歷史邏輯,“在沒有倫理在場的政治認同,以及政治如同對倫理認同的優位,才是造成認同危機的根本原因所在”[7]。
2、黨員干部在學雷鋒常態化轉型中的重要作用
2.1、傳統政治文化架構下黨員干部在學雷鋒常態化轉型中的基礎作用
傳統是現代的源頭,現代是傳統的當下。該如何考慮學習雷鋒的常態化轉型,傳統與當下是其重要的思考維度。有當代學者認為,在王權主義的統攝下,官僚、縉紳士大夫形成的剛柔結構組成了我國傳統政治文化運行的基本架構,這種傳統根深蒂固,雖然當代經濟改革跨越了層層樊籬,但政治改革卻稍顯步履蹣跚。我們認為,在這種不對稱的發展態勢下,對學習雷鋒常態化轉型這一具體政治文化運動而言,黨員干部都被推上歷史的潮頭。一方面,支持行政系統的干部的垂范與重視成為轉型時期傳統體制由上至下推動政治運動的核心力量。這一傳統體制的重要作用也被眾多研究所佐證:如鄭昌盛、王珊關于“雷鋒車”的研究[8];彭蕾、孫波關于“高校學雷鋒常態化”的研究[9];蔣曉俠關于“新形勢下雷鋒精神的弘揚之道”[10]的研究都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在當前體制下領導干部的態度在學雷鋒活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是首要作用。另一方面,支持新中國信仰系統的黨員又成為體現文化先進性的代表、須以其身體力行展現和注解這種由下至上的、作為當前經濟、文化多元化發展產物的文化運動,將行政系統中抽象的“常態化”雷鋒轉化為日常的、自發的、普世的、底線倫理的、具體的常態化雷鋒群像和場景。前者的失位,將直接導致對學雷鋒常態化轉型合法性的質疑,而后者的缺失則會引發轉型的路徑萎縮與合理性淪喪,遲滯我國當下倫理道德現代化的進程。就以上意義而言,干部與黨員就成為轉型時期傳統與當下相統一、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相嚙合的社會樞紐,從這一體制路徑加以思考,我們就能夠更加理解身處時代之中的毛澤東同志關于“學習雷鋒的關鍵是黨員干部帶頭”的論說所體現的深邃睿智和憂患意識。
2.2、公民社會發展背景中黨員干部在學雷鋒常態化轉型中的基礎作用
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改革的基礎,當前的社會也產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中之一即公民社會的初步形成。中國社會開始逐步轉入社會與公民關系的話語體系,個體的權利得到了解放。隨著社會倫理從規范倫理回歸美德倫理,作為“真正自我利益缺席”的道德行動者雷鋒也獲得了個體性的動機發展空間,即通過奉獻集體才能獲得個體存在價值的雷鋒,在公民社會中被轉化為通過服務社會、實現道德圓滿、達到個人幸福感的雷鋒。對于這一轉型過程,學者們有不同的見解,張亞月將之與志愿精神生成相關聯[11],解瑞卿則將之與公民精神轉化加以邏輯關聯[12],張家俊的研究也注意到這一問題,認為公民社會轉型中道德倫理發展存在從政府確立榜樣向社會選擇榜樣的趨勢[13]。這些研究都深刻地揭示出這種學雷鋒常態化轉型的自在之因。這樣,原有的動員式的、單向的、典范式的以規范統一的學雷鋒就自然的轉化為自覺地、雙向的、普遍式的追求個體道德幸福感的學雷鋒。這也產生了一個新的命題:如果傳統的動員式倫理已失去了其原有的推動力,那么,公民社會中道德的感召力量來自何處?或者說,在公民的道德成長中應該向誰學習?這個問題對我們黨有著不能承受之重,始終拷問著黨員干部的黨性和良知。由此得到另外一個命題,雷鋒當初學的誰?肖新給出了答案,雷鋒當初學習的榜樣是其身邊的領導[14]。陳思炳考證說,縣委書記張光玉、團政委韓萬金等黨員干部的善心、善行、善言曾深深地震撼雷鋒的內心[15]。可以說,黨員干部的春風化雨、潤物無聲造就了無數如雷鋒一般的向善之心。這也使我們意識到,民間道德倫理的生發過程有其民族心理和文化傳統的背景,個體在民族整體的道德信仰中獲得的精神滿足有著更為充沛的生命力,在此種意義上,黨員干部等先進份子所堅持的美德及立場往往會成為一個民族道德文明的環境與普遍追求的高度標示。關于這一問題的逆向思維也會推導出這樣一個問題:人民崇尚雷鋒,而雷鋒的背后是一大批屹立著的黨員干部,黨員干部的高度就是雷鋒的高度,那么人們質疑雷鋒,就蘊含著黨員干部沒有很好的支撐起社會倫理道德應有的高度。劉亦功的分析頗有新意,他認為當代“雷鋒質疑論”顯示著格雷欣法則某些特點,如果我們不能夠迎頭痛擊精神領域的腐朽現象,就容易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16]。此觀點極有見地,因為干部背后是國家的高度,黨員背后是信仰的高度,它們共同構成了當前公民社會精神文明的高度,它們就是公民美德成長的當下環境。好的環境將強化公民的道德歸屬感和道德實現的幸福感,不良的環境將導致公民對道德行為后果的擔憂,甚至是對道德倫理的懷疑。基于以上的原因,可以認為當前學雷鋒常態化轉型亦即我國當下道德倫理的公民化轉型。雖然說黨員干部不能夠決定歷史自在的方向,但他們所代表的道德高度及環境將決定公民社會道德建設的速度和難度,也會決定當下由此形成的外在具像學雷鋒常態化問題的過程。
3、結束語
學雷鋒常態化轉型是中國精神文明建設的必然結果,黨員干部是轉型時期的推動學雷鋒活動深入發展的重要環節和核心力量。從歷史縱向的政治體系和文化體系的運動規律看,黨員干部是兩個規律發生協動的紐帶,從當下橫向的公民社會道德倫理的發展看,他們即是政府的精神文明建設的高度,也是信仰體系的標尺。學習雷鋒常態化轉型要重視黨員干部的重要作用。
[注釋]
[1]雷鋒的意義.人民日報(第8版),2004-6-19.
[2]陶東風,呂鶴穎.雷鋒:社會主義理論符號的塑造及其變遷[J].學術月刊.2010(12).
[3]焦正安.雷鋒精神之淵源、嬗變和提升及其他[J].學理論,2012(24).
[4]周楊.雷鋒精神永不過時—關于雷鋒精神的三點思考[J].蘭州學刊,2012(03).
[5]劉澤華.中國的王權主義[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82-184.
[6]何懷宏.底線倫理[M].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89.
[7]王強.雷鋒精神如何進入生活:一種哲學追問[J].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12(02).
[8]鄭昌盛,王珊.新時期擴大雷鋒車精神社會效應的策略研究[J].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2(02).
[9]彭蕾,孫波.對推動高校學雷鋒活動常態化的思考[J].當代青年研究,2012(04).
[10]蔣曉俠.新形勢下雷鋒精神的弘揚之道[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02).
[11]張亞月.志愿精神與雷鋒精神的關系辨析及整合前景[J].思想理論教育,2012(15).
[12]解瑞卿.論雷鋒精神與公民精神的邏輯關聯[J].廣西青年干部學院學報,2012(05).
[13]張佳俊.從向雷鋒同志學習到全國道德模范評選——建國后中國共產黨榜樣教育模式變化之初探[J].經濟研究導刊,2009(22).
[14]肖新.雷鋒當初學的誰[J].冶金政工研究,2003(01).
[15]陳思炳.雷鋒當初學的誰[J].江淮,2007(03).
[16]劉亦功.主流與沖擊—雷鋒精神傳播中的雜音透析[J].青年記者,20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