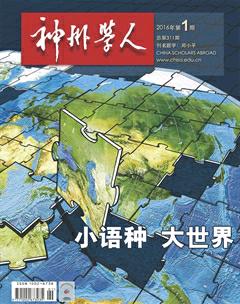當芬蘭語遇上法律
陸斐

2015年芬蘭的雪來得似乎有點遲。11月,我身處的北極圈小城還徘徊在零上三四度。不過這反常的“高溫”并沒有影響極光漫天飛舞的“心情”,我已經接連3天在公寓陽臺上欣賞極光在空中肆意舞動的身姿了。這些年來綠色的極光倒是多見,今天有些特別,天空隱約泛著些粉紫,都說極光下許愿比較靈驗,于是趕緊許個愿。
取舍
今年是我在芬蘭的第6個年頭,而我與芬蘭、與芬蘭語的緣分則快滿10年了。記得大三那年第一次走出國門,我對芬蘭的一切都感覺那么新鮮,激動與興奮溢于言表。畢竟,對學習語言的學生來說,能夠在對象國學習、生活一段時間是一件幸事。大三出國留學對于本科4年的非通用語專業的學生來說,是最恰到好處的選擇:大一、大二是系統學習、夯實基礎的關鍵,在形成對語言本身和對象國的基本認識之后,進入最佳的語言環境,語言能力才會有一個質的飛躍。更重要的是,大三之后就要面臨人生轉折點——職業選擇。
記得一次與時任諾基亞公司中國區總經理交談,他說,會芬蘭語當然能成為將來求職的一個亮點,但語言只是溝通的工具,還需要有專業能力,畢竟工作中大家都會說點英語。他的話道出了很多學習非通用語的學生所面臨的窘境——是要為了工作舍棄語言,還是執著于語言卻面臨畢業就失業的風險?
現實中大部分人選擇了前者。面對這個問題,我想我是幸運的。在本科學習芬蘭語時,我接待了芬蘭瑞典法學訪問團,遇上了我現在的博士生導師,導師建議我嘗試把良好的語言基礎與新的專業知識做一個有機的結合。
大三留學期間,我在學習語言的同時堅持去旁聽其他專業的公開課:新聞、教育、商科……沒想到還是法律最吸引我。留學回來之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學院的老師,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幫助我獲得了保送本校法學院攻讀法學碩士的機會。當時從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畢業后選擇跨專業工作的同學,大多從事了海外漢語教師或外交工作,吃“法學”這只螃蟹的,我算是第一個。
法院院長讓我做翻譯
從一個語言學習的佼佼者淪為法學的“后進生”——“老學姐”擠在大一新生堆里上法學基礎課的滋味不好受。但既然選擇了,就要勇往直前,要對自己負責。這種決絕在我選擇到芬蘭攻讀法學博士學位時也是一樣。
有的跨專業學生會把以前學習的語言給丟了,但我熱愛語言,熱愛芬蘭語,我要用芬蘭語來研究法律問題!2011年,我獲得了國家留學基金委的獎學金,第二次踏上了留學芬蘭的征程。
與芬蘭的第二次親密接觸,我有了更加明確的目標。但要實現這個目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開始我就遇到了不小的挑戰。
想要真正了解芬蘭、了解歐盟的法律體系,離不開全面系統的學習。在芬蘭拉普蘭大學法學院,在博士生課程之余,我又開始了法學基礎課之旅。不同的是,這次是全芬蘭語教學。一堂課少則3個小時多則6個小時的高能專業知識,芬蘭本國學生聽著都有些吃力,何況我一個外國人。不過我沒有因此而退縮,不懂就多看多聽多問,久而久之,我不僅能夠消化整堂課的內容,還能夠參與課堂討論。后來整個拉普蘭大學法學院都知道了有一個會說芬蘭語的中國學生。
在芬蘭攻讀博士學位給予了我一個良好的平臺來研究芬蘭法律,而我本身的語言能力也著實為我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礎。但是博士階段的研究意味著我要閱讀大量芬蘭語文獻。芬蘭語本身就很復雜,而閱讀芬蘭語的法學專業文獻,是個讓芬蘭學生都頭疼的事情,有的時候一個句子往往要來回閱讀好幾遍才能弄明白意思,本科4年學習的芬蘭語知識突然變得不夠用了,我著急了。
事有湊巧,2012年9月,第四屆中芬比較法國際研討會在芬蘭羅瓦涅米上訴法院召開,研討會上該上訴法院院長要介紹芬蘭的司法制度,法院院長聽說我這個中國學生會芬蘭語,硬是要我給他做翻譯,雖然有點措手不及,但我也只能硬著頭皮完成任務。沒想到任務順利完成,效果竟然出奇的好。后來法院院長問我要不要來法院工作,這是一劑強心針,讓我深信自己有能力攻克語言與專業這兩個難關。這也讓我再次慶幸本科4年的語言學習,那些努力都沒有白費,如果當時沒有打下堅實的基礎,就根本無法用芬蘭語來學法律;而從芬蘭語專業畢業也并不意味著芬蘭語學習的終結,隨著研究的深入,對芬蘭語的應用要求也越來越高,只有不斷地學習、提高,才能幫助我真正做到用芬蘭語來研究法律問題——或許這也是語言的一種獨特魅力吧。
使命
很多人會問,你用芬蘭語研究芬蘭法律,將來回國有什么用呢?
芬蘭作為歐盟成員國,是一個很好的窗口,讓我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歐盟法律制度,而歐盟研究在中歐關系往縱深發展的時刻是非常有必要的。我選擇從事中芬法律的比較研究,一來并不脫離中國的實際,二來也可以彌補學界這一研究方向的欠缺。更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成為了我向世界展示中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文化的窗口。
2012年,我受邀參與了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重大項目——《世界各國憲法》中《芬蘭憲法》的翻譯與校訂工作。翻譯,對于每一個語言學生來說都不陌生,但這一次的翻譯工作有所不同,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把語言與法學這兩個學科進行了有機結合,也為我國現行憲法公布實施30周年獻上了自己一份小小的賀禮。
2013年,我獲得了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總部實習的機會,短短4個月,譜出了我求學階段精彩的小插曲。當時我擔任教科文組織“國際工作人員協會”的法律助理,主要任務是幫助該組織的雇員及時獲得法律救濟,這給予了我一個獨特的視角來了解國際組織。我實習期間正值教科文組織第37屆大會召開,也是該組織第一次選舉中國代表擔任大會主席,這位主席就是中國教育部副部長郝平。會議間歇我遇到郝平,聊起他為非通用語學生出國留學做出的積極努力,他感嘆北外的學生果然沒有讓他失望。而那一刻,盡管我不是一名外交官,但也深深體會到了“世界上凡有五星紅旗飄揚的地方,就有北外人的身影”的驕傲與自豪。
我們非通用語人身上都有一種使命感——語言是我們打開世界大門的鑰匙,而通過這把鑰匙,我們不僅要把世界介紹給中國,也要把中國介紹給世界。我想,正是因為有了這一使命,我才擁有了如今立足語言、跨界法律、放眼世界的機會。而我也衷心希望“做一個多語種、復合型的國際化人才”不再只是一個口號——這也是我在極光下許下的美好愿望。(作者系芬蘭拉普蘭大學比較法學研究學者、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