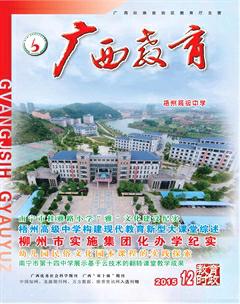優質共享 力促均衡
蒙秀溪+歐金昌
“新學校太漂亮!太好了!”柳州市景行小學柳東校區學生覃慧伶連用兩個感嘆來表達內心的感受。一年前,覃慧伶就讀于當地一所村小。“那是一所又小又舊的學校,連活動場地都沒有”。2014年,當地原有的3所村小撤銷了,所有學生進入景行小學柳東校區就讀。“以前我只會踢毽子、跳皮筋,圍棋、毛筆這些都沒碰過,什么是多媒體也不知道。現在,這些我都懂了。我特別喜歡現在的學校”。對于新學校,覃慧伶滿是“新奇和興奮”,而覃慧伶的爸爸秦茂飛則更多的是“放心”,自從女兒進入新學校就讀后,他的擔心就沒有了:“孩子在這么好的學校里讀書,我完全放心。”
景行小學柳東校區成立雖然只有一年時間,卻已是當地群眾口中的“好學校”。這是柳州市實施集團化辦學取得的又一碩果!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群眾對優質教育的需求越來越大。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的優質教育資源相對集中在城市,形成了教育‘貧富分化的局勢。”柳州市教育局局長姚尹意說。為沖破教育不均的“藩籬”,2012年,柳州市探索實施集團化辦學,以縮小城鄉教育差距,破解“擇校熱”“大班額”等教育難題,最終實現教育均衡發展。
收放有度:自主開發“自耕田”
來到位于柳州市河東開發新區的景行小學總部,一幢幢以淺黃色為基調的建筑赫然映入記者眼簾,陣陣清新悠長的桂花香縈繞鼻尖,耳畔響起的是學生們洪亮悠揚的歌聲……景行小學,這所經歷百年積淀的名校,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在柳州市占有絕對優勢。正因如此,它成了柳州市第一批“涉水”集團化辦學的學校。
“開展集團化辦學之后,我們根據各校實際進行自主研究、設計,市里沒有太多約束。”景行小學教育集團總校長韋莉說,“這就像是給了我們一塊‘自耕田,怎么種、種什么都是我們自己做主。這樣更有利于各校發揮自身優勢,促進學校間的深度結合。”
自主規劃,是柳州市實施集團化辦學的一大原則。這里的“自主”有兩層含義:一是城區(縣)的自主,各城區(縣)根據本地實際,規劃集團學校的成員組成;二是學校的自主,各集團學校根據自身情況,設計結合方式、內容和時間表等。正如柳州市第四十五中學教育集團總校長黃杰說的那樣:“每所學校都有自己的實際,不能‘一刀切。這需要給予學校充分的自主權,讓各集團走個性化、特色化發展道路。”
柳州市第四十五中學教育集團是一個“新生兒”,成立只有3個多月,是柳州市為數不多的設有附屬小學的初中教育集團。這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如何協調初中與小學的步伐?如何做好初中與小學的銜接?如何實施具體的管理工作?如何開展教師培養工作?如何實施校園文化建設?……“像我們集團這種情況,如果照搬其他初中教育集團的經驗,不僅達不到預期效果,反而會產生學生無所適從的消極影響。”黃杰總校長說。
但是,放權不等于“放牛”。在鼓勵自主規劃的同時,柳州市在頂層設計上進行了總把關:制定“名校+弱校”“名校+村校”“名校+新校”3種集團化辦學模式,促使名校優勢資源向薄弱地區、農村地區延伸;在全市范圍內實施教師交流輪崗制度,促使全市教師職業水平整體提升;加大對集團學校的資金、人才和政策的支持力度,保障集團化工作順利推進。
收放有度的管理機制,使得柳州市集團化辦學呈現出良好態勢。如今,該市已成立了初中、小學、幼兒園教育集團20余個,而且未來幾年還將以每年2-3個的速度遞增。教育集團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柳州市教育格局由此重組,教育資源也由此而重新分配。
柳南區實驗小學和美分校學生家長王浩敏告訴記者,當地過去的幾所小學的辦學質量都不高,孩子上學問題一度困擾他們夫妻。2014年5月,柳南區實驗小學和美分校掛牌成立,聽聞消息后他立即為孩子報了名。“看到孩子在學校里那么快樂地學習,想到在家門口就能上這么好的學校,我們覺得很滿意。”王浩敏高興地說。
多法并存:名校優勢的外延和發散
景行小學教育集團潭中校區原為柳州市城中區潭中路小學,是一所資深學校,辦學質量一直不錯。然而,由于家長對優質教育需求的增強,幾年前,該校出現了學生外流的現象。為了更好地吸引本學區的學生,柳州市城中區教育局將該校劃為景行小學教育集團的一個校區。加入集團后,該校開始復制景行小學的辦學理念、課堂文化、學生活動等,全面盤活了學校的各項辦學機制。
“我最喜歡現在的‘課前精彩兩分鐘,同學們可以盡情展示自己的學習成果。”說起這個“兩分鐘”,潭中校區學生戴弘斌仿佛有說不完的話,“為了做好展示,我們要做很多準備,和爸爸媽媽一起找資料,學做PPT,還要鍛煉自己的口才。在‘課前精彩兩分鐘中,我學到了許許多多的知識。”
“課前精彩兩分鐘”是景行小學課堂文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即每節課前安排兩分鐘,由學生上臺展示,展示的內容因學段的不同呈現出層級性、梯度性的特點,如:一年級以講百家姓為主,可以講姓氏起源、發展,也可以講歷史名人姓名的由來;三年級以推薦課外書為主,可以是PPT演示,也可以上臺表演書中某個精彩片段。潭中校區移植了總校的這一做法,并在全校鋪開。
“做這些會不會影響孩子的課堂學習?會不會占用孩子太多的課外學習時間?對孩子的成長有用嗎?”身為教師的學生家長惠靜對此有自己的思考。她的孩子成績一直拔尖,因此對于學校復制“課堂精彩兩分鐘”不免有些擔心。可當看到女兒為做好展示而專心準備時,看到女兒在講臺上滔滔不絕時,她“那顆懸著的心放下了”。“終究是名校的好經驗,相比過去的教學方法,現在這個方法實在是有效多了!”她由衷感嘆道。
集團化辦學第一年,潭中校區便有30多名學生回流,當年一年級招生預計為4個班,后來不得不擴至5個班,第二年又擴至6個班。該校一年級學生家長沈艷玲回憶當初給孩子報名的情形時笑著說:“當時報名真是擠破了頭,還差一點報不上呢!”
與景行小學教育集團“完全復制”的方法有所不同,柳南區實驗小學教育集團則更強調“求同存異”。在大方向上,如辦學理念、發展路線,該集團要求各分校與總校保持一致;在細節方面,如校園文化、學生活動等方面,該集團則鼓勵各分校在學習、借鑒總校經驗的基礎上,可以進行個性化設計。
柳南區實驗小學和美分校吸納了總校“美的教育”的理念,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更注重自身的實際情況。例如:總校設置的語言類社團為“小主持人社團”,到了和美分校就成了“誦讀社團”;總校的啦啦操隊,和美分校也沒有復制,而是成立了武術社團。“我們設計每一個活動都會充分考慮學生的基礎、家庭情況等因素,不能完全用‘拿來主義。”該校執行校長龍菲說。
在“自主規劃”原則的指導下,柳州市每個教育集團之間都存在著差異,或是集團理念不同,或是結合方式有別,亦或是管理方法互異,但其目標都是一致的:實現名校優勢的外延和發散,逐步縮小弱校、村校、新校與名校之間的差距。正如在原河東小學任教了15年的莫翠群老師所說的那樣:“如果不是靠上了景行小學這棵‘大樹,我想我們這所村小還不知要花多少時間和精力,才能達到現在的水平呢。”
交流輪崗:從“稀釋”到優化重組
雖說差異是存在的,但在師資調配方面,柳州市所有教育集團都采取了教師交流輪崗制度。這是柳州市集團化辦學頂層設計的一項核心工作。“師資是學校深化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造成當下教育不均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學校區位、硬件配備等,但最重要的還是師資力量的不均衡。所以,我市把教師交流輪崗工作當作關鍵項目來抓。”姚尹意局長說。
對周偉榮老師來說,從潭中校區交流到景行小學總部,既是壓力更是動力。有近30年教齡的她,在原潭中小學擔任教導主任,因為任職時間太長和身體問題,她“感到了厭倦和迷茫”,曾想辭去教導主任一職。集團化辦學之后,她交流到總部。“在總部,我學到了很多新的管理理念和教學方法。沒想到在我這個年紀還能有這樣的提升。如今我走出了倦怠和迷茫,重新找回了當年的活力,感受到了另一番風景。”說到此處,她已微微有些哽咽,“交流期結束后,我一定要把我的收獲帶回去,跟同事們分享。”
從景行小學總部交流到潭中校區的王燕春也有類似感受。過去在景行小學任教的16年里,對她來說都是“風平浪靜的,沒有太多新鮮感”。后來一聽說有交流輪崗的機會,她便主動請纓。“在潭中校區接觸到不同層面的家長、學生,每天都會遇到不同的狀況,這是新的挑戰。為了解決好這些問題,我要看更多的書,和同事進行更廣泛的交流。來譚中校區的兩年里,我收獲的不僅是專業提升,更是個人價值的體現和對教師意義的領悟。我很珍惜這兩年的時光。”王燕春說。
自2014年秋季學期實施教師交流輪崗制度以來,柳州市要求縣城學校與鄉鎮、農村學校之間,城區優質學校與弱校、新校之間,均要進行教師雙向交流輪崗,并根據區域實際給予每人每年1萬至2萬元的補助,極大地調動了教師的積極性。截至目前,柳州市全市教師交流人數達到4641人次,實現了全市中小學教師交流全覆蓋。
對于大范圍的教師交流輪崗,也有人提出疑問:這會不會使大量優秀師資迅速稀釋?就像一杯濃牛奶被分別注入到多杯白開水中一樣。“我認為,稀釋是必然的,但這與‘牛奶稀釋不同。交流輪崗是把優秀師資分配到各個學校,以榜樣、專業的力量帶動當地教師的提升;把較弱的教師集中到名校,用名校的理念和方法幫助他們進步。這是一個從‘稀釋到優化重組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時間的保證。”韋莉總校長很有信心地說道。
為了確保“釋”而不“稀”,柳州市除了進一步加大市級培訓力度,還鼓勵各集團開展形式多樣的校本培訓,一方面幫助一線教師提升技能,一方面從中挖掘、培養新的名師,最終實現教師隊伍的優化重組。
并肩齊進:弱校搭上名校的“順風車”
“課堂真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呀!”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縣民族中學南校區學生歐治伶感嘆說,“以前上課都是老師在上面講,一些同學就在下面睡覺。現在我們也和北校區一樣,開展生本教育,課堂上大家可以你一言我一語地發表意見,還可以上臺展示,再也沒有睡覺的現象了。”
融水民族中學南校區原來是融水實驗學校,2013年,融水實施集團化辦學后,該校與融水民族中學合并,成為融水民族中學的分校區。兩校合并之后,在教育理念、學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術、教育評價上實行統一管理,以實現優質教育資源共享。
生本課堂帶來的沖擊,是合并后原融水實驗學校師生們最先感受到的“巨變”。在原實驗學校任教多年的教師韋國忠告訴記者,融水在2013年啟動生本教育改革試點工作時,該校便有意申請成為第一批“基地學校”。“但由于師資等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我們也是有心無力。”韋國忠無奈地說,“而自從與民中聯合之后,情況變了,總校從教師培訓、學生小組建設甚至是學生的課堂行為,都給了我們全方位的幫助和指導,讓我們享受到了課改的紅利。”
“集團化”改變的不只是課堂,還有學生的課余生活。“現在,北校區的活動我們也有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課外活動不再只有打籃球、跑步了,還可以練舞蹈、書法,到校外搞社會調研,有時還會和北校區的同學一起搞活動。這讓我學到了很多知識,還交到了很多新朋友。”融水民族中學南校區學生韋江洪說。
“集團化辦學給我們帶來了發展的春天!”韋國忠一句由衷的感嘆,表達了柳州市參與集團化辦學的弱校、村校、新校的心聲。
在集團化辦學中獲得紅利的又豈止是原融水實驗中學?迄今為止,僅柳州市城中區就成立了4個教育集團,以景行小學、彎塘小學、公園小學、文惠小學為龍頭學校,帶動了包括景行小學河東校區、彎塘小學文華校區、文惠小學靜蘭校區在內的7所弱校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柳北區也成立了4個初中教育集團,在龍頭學校的帶領下,柳北區第二十六中學及附小、柳北區第二十九中學及附小等9所弱校,將自身辦學資源與龍頭學校的辦學資源進行有效對接,促進了辦學水平的全面提升……一個又一個教育集團的成立,讓一所又一所薄弱學校搭上了名校的“順風車”。正像景行小學教育集團柳東校區執行校長唐瑜璟所說:“要將一所薄弱學校辦好辦強,單靠自身力量,周期會很長,也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但如果通過引進、內化名校的優勢,就能縮短這個周期,還能通過名校的社會影響力造聲勢。我們學校就是集團化辦學的受益者。”
“如今,學生學習講求合作。這道理是一樣的,集團化辦學就是‘合作,通過‘合作,弱校可以依靠名校的力量實現整體提升,名校也可在與弱校的聯合中發現新的辦學路徑。這是實現教育均衡的一條好路。”采訪最后,姚尹意局長如此總結道。
(責編 歐金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