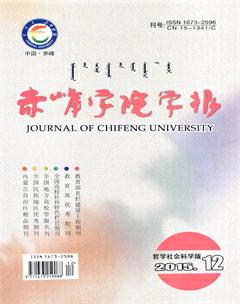“他校”與“對校”“理校”關系之淺析
童坦
摘 要:“他校”與“對校”“理校”都是陳垣校勘體系中的科學方法。“他校”與“對校”“理校”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厘清他們之間的關系可以加深我們對陳垣校勘學思想的理解,進而更好地利用這一科學理論指導我們的校勘工作。
關鍵詞:陳垣;他校;對校;理校;區別;聯系
中圖分類號:G25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12-0138-03
校勘學,在我國是一門古老的學問。從宋代開始,就有純粹的校勘學著作問世,校勘學已然成為一門自覺的學問。到清代,隨著文字訓詁學、考據學的興盛,校勘學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至近現代,校勘學者更是自覺地對校勘方法的理論體系進行研究與總結。
清代學者吳承志的《遜齋文集·校管子書后》總結了“大略盡之”的改字5例:“據善本校改”“據古書校勘”“據注文校改”“據本書校改”“據文義校改”。清末民初藏書家葉德輝的《藏書十約·校勘七》也歸納出兩種校勘方法:“活校”與“死校”。上世紀20年代初梁任公在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中也提出了影響后人的4種校勘法。但真正做出科學總結并被公認為校勘正規方法的則是近人陳垣在《校勘學釋例》(《元典章校補釋例》)中總結的“校法四例”,即“對校”“本校”“他校”和“理校”4法[1]。這4種方法在本質上構成了一個各要素具有相互關聯性的整體,成為指導古籍校勘者的科學理論體系,推動了我國古籍整理事業的發展。
自陳垣“四校法”問世以來,學者們對其闡釋和探究之論也是層出不窮,對4法之間的關系也各有看法。本文也試圖通過對陳垣“他校”“對校”“理校”三法的分析,在揭示其理論內涵的同時,就“他校”與“對校”“理校”的關系發表一些自己的見解。
一、“他校”與“對校”“理校”的區別
(一)“他校”與“對校”的不同
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于其旁。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陳垣指出了對校法的主旨和優缺點: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
此外,陳垣還專門指出,必須先用對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而且他還從兩個方面強調了使用對校法之必然性,其一“有非對校決不知其誤者,以其義表面上無誤可疑也”,如:沈刻本“元關本錢二十定”看似無錯,因為從語義上來看是通順的。但用元刻本對校之后便知是非,元刻本作“二千定”,才知是形近而誤。其二“有知其誤,非對校無以知為何誤者”,如:沈刻本“每月五十五日”,讀來便知有誤,誤在何處卻無從而知。通過與元校本對校后便找到了原因,元刻本作“每五月十五日”,才知是上下字關聯而倒。
對校法也稱“版本校”,即對校“對”的是“版本”,“版本”是對校的對象。這就決定了在運用對校法校勘古籍時一定要先厘清底本外各個本子(同書之祖本或別本)之間的淵源遞嬗關系。對校的目的和任務是著力消除同一部典籍在歷經不同版本的變遷時所衍生的訛誤,保護文獻本身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向讀者提供保持著文獻原貌的讀本。
陳垣先生所謂校勘的主旨在于“校異同,不校是非”,并不能單純地理解為“死校”。他的主要目的是存真,是保存祖本和對校本的本來面目。而且他的這一主旨的提出是有其前提性的,即“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一部古籍的成功校勘需要各種校勘方法的完美配合。
他校法,即以他書為參照來校本書。關于這個“他書”,陳垣認為有3種:一是“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二是“有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書校之”,三是“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并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同時他也指出了此法的優缺點:此等校法,范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
古書之間常相互“征引”(轉引),如類書、詩文選本、前人舊注等,雖然這些書籍有些在性質上與本書有很大差異,但是其中的相關文字記載、事件、史實等都可以作為校勘古籍的資料。他校法,就是用與本書有轉引關系的他書來對古籍進行比對校勘,即面對需要整理的古籍,其轉引的有前人之書時,則以前人之書校之;其有為后世之書所轉引時,則以后世之書校之;其與同時之書轉引的有相同的文獻資源或史料時,則以同時之書校之。他校法的任務也是要盡可能地消除一部典籍在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訛誤,保護文獻的完整和真實,保持文獻的原貌。
陳垣將“他書”分為前人之書、后人之書、同時之書,條理是極為嚴密的。但一言以蔽之,在他校法中,用來與原書進行對比校勘的是別一部書。而在對校法中所使用的則是與原本同書不同版的書,這正是兩者的本質不同之處。
陳垣認為對校的主旨是“校異同,不校是非”,不能參己見。對此,一些學者是持反對態度的,認為如此便無異于“死校”。的確,校勘的最終目的是要校出一部在文字上比較正確無訛的新善本。但是就對校本身來說,其首要功能和目的只是校出異文,其本身是不能明確審定是非的。時永樂先生根據陳垣所說的“故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直接指出“陳垣的本意也正是把對校法作為校勘一部古書的一個步驟的”[2],一些學者所持的對校時也要加入判定是非、決定取舍的內容的看法,已經超出了單純對校法的范圍,更應該是對校與理校法的結合。這樣,他校法與對校法又有了不同之處,下文將會論及。
(二)“他校”與“理校”的不同
關于理校法,段玉裁在《經韻樓集》卷六《與諸同志論書校之難》中認為:“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3]陳垣在繼承前輩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最后強調“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因為“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
理校法需要古籍點校者充分發揮邏輯推證能力,運用分析、綜合、模擬等手段,在無古本可據時據理推斷典籍中的正誤,或校出數本中的異文時據理判定是非。陳垣認為在使用理校法這一科學校勘方法時不能魯莽行事,而要謹慎為之。他的原則是:“只敢用之于最顯而易見之錯誤而已,非有確證,不敢藉口理校而憑臆見也。”即理校也要有確鑿的證據。因此,一般只有具備豐富的文獻學、文史常識、文字、詞匯、語法、音韻等方面的知識并且能夠綜合加以運用的通識大家才能熟練操之。
如《戰國策·趙策》載:“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詟愿見,太后盛氣而揖之。”王念孫認為前文有太后所說“復言”之辭,從文氣而言其后當有與其呼應者,“左師觸詟愿見太后”顯然不符合文章邏輯,應該改為“左師觸龍言愿見太后”。“觸詟”的“詟”字應是“龍”、“言”合字致誤,“左師”應名“觸龍”[4]。1973年湖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戰國縱橫家》證明了王念孫的推理是正確的。如果沒有深厚的古文修養和淵博的文史知識,王先生是不會做出如此正確的推斷的。
而關于理校具體所使用的方法,分析得最詳細的當屬管錫華先生在《漢語古籍校勘學》中總結歸納的諸多方法,比如:從音韻校;從文字校;從詞匯校;從語法校;從修辭校;從行文特點校;再如:從常用語校;從典制禮俗校;據史實校;考典故校;據古今習俗校;考地理校;考歷法校;還有:從義理校;推算數字校;據成書年代校;據文學形象的統一性原則校等等。
如陳垣先生在《校勘學釋例》中的校例:(《元典章校補釋例》卷六)
吏五四:合無烕(滅之繁體)半支奉;校:“烕半”當作“減(減之異體)半”。校勘的依據是“烕半”語言不倫。吏八一七:也可扎忽赤;校:當作“扎魯忽赤”,元本亦漏。這是據蒙古族人名號的常例校正的。刑一四:江西省行準中書省咨;校:“省行”當作“行省”。這便是根據元朝行政制度的歷史而改的。戶五三一:亡宋淳佑元年;校:“淳佑”當作“淳祐”。很顯然,宋朝的年號只有“淳祐”而無“淳佑”。
他校法借助的是更多的是實證,是他書中的可以用來同文對比的資料。而理校借重的則是邏輯推理的力量,它“超出了對具體校勘資料的尋求,進展到作為文獻產生、存在背景的歷史文化領域中,去尋求判斷是非的依據”[6]。他校法使用的更多的是文本依據,是屬于感性和經驗層面的,理校法使用的更多的則是義理依據,是屬于理性層面的。
二、“他校”與“對校”“理校”的聯系
(一)“他校”與“對校”的聯系
杜澤遜在論及他校法時認為他校任然屬于對校,“不過不是全書對校,而是片段對校。無論他書引本書,或本書引他書,這些語句都仍是出于這一部書[7]。程千帆、徐有富也持此種觀點,認為他校“也是一種對校”[8]。本文對其中的一些看法是持肯定態度的。
對校是要校出底本與祖本或別本的異同,是一個獲得同書異本之間的異文、發現訛誤的過程。他校是要校出底本與他書(與底本有征引關系的前人之書、后世之書和同時之書)的異同,也是一個獲得他書異文資料、發現訛誤的過程。二者都是經驗層面的據本校正,所據之本即可以發現同文對比資料的所有文本,不同的是一個是同書異本之同語,一個是本書與他書之同語。因此,他校和對校之間有一個共同的依據,即同語異文。
(二)“他校”與“理校”的聯系
他校法主要是校出底本與對校本的同語異文(他書異文)。可是,在進行校勘時決不能把他校看成只是對同文對比文獻資料的簡單使用。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可以從他書中發掘大量的“義理、事實、數據等方面的依據用于論證”[9]。從文獻材料的來源來看,這種論證屬于他校,從使用方法來看,這種論證也屬于理校。從此可以看出,他校與理校在某種程度上是有著密切聯系的。
如武秀成先生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的點校本《唐會要》中所存有的訛誤的舉證(現舉兩例):
景龍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宗)崩于神龍殿。(《唐會要》第4頁)
按:中宗之死在六月二日,“二十”乃衍文。《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條載中宗忌日為“六月二日”。又《舊唐書·中宗本紀》景龍四年云:“六月壬午,帝遇毒,崩于神龍殿。”《新唐書·中宗本紀》《通鑒·唐睿宗景云元年》亦并作“六月壬午”。六月辛巳朔,壬午正初二。并其確證。
開元八年十月敕:“諸督刺史上佐,每年分蕃朝集,限一月二十五日到京,十一月一日見。”(《唐會要》第536頁)
按:“諸督”不詞,“督”上當脫“都”字。《唐六典》卷三“戶部郎中”條亦載此制,云:“凡天下朝集使皆令都督、刺史及上佐更為之。……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于京都,十一月一日戶部引見訖,于尚書省與群官禮見。”此正作“都督”,可證。或疑“諸”為“都”之誤,非是。《唐會要》載此類詔救,其首多有“諸”字。如此條前后之顯慶二年十二月敕、先天二年十月敕、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敕、建中二年七月敕,詔文前并有“諸”字。又據《唐六典》,知“一月”亦有誤。以理揆之,諸朝集使若十一月始許朝見,又何須限其正月到京?且諸朝集使或為都督,或為刺史,若正月到京,至十一月方可離京,其奈州府政事何?是“一月”當從《六典》作“十月”[10]。
而“他校法”與“理校法”的這一聯系也正是其與“對校法”的一種區別所在。
陳垣的“校勘四法”已被公認為正規的校勘方法,是一個具有指導性的科學理論。他的理論的完整性是前人難以企及的,也是后人難以望其項背的,因為它是一套對校勘行之有效的科學的方法理論體系,4種方法之間形成了自身內在的理論邏輯性,4法之間是相互拱衛的整體。其中的“他校”“對校”和“理校”是構成陳垣校勘方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他校”與“對校”“理校”之間既同處于一個相互具有關聯性的科學理論體系中,又分別具有各自不同的理論特色和實踐原則,“他校”與“對校”“理校”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因此我們要分清“他校”與“對校”“理校”之間的不同,不能混淆他們的理論內涵,更不能混淆他們在校勘中的功能和用法,在整理古籍時要根據現實條件選擇合適的校勘方法,從而取得預期的校勘效果。同時我們也不能無視“他校”與“對校”“理校”之間的內在聯系,在整理古籍時要靈活地綜合運用各種校勘方法,以實現古籍校勘的目的和宗旨。總之,正確認識和厘清陳垣校勘法中“他校”與“對校”“理校”之間的關系,不僅有利于我們對陳垣校勘學思想的深刻理解,也有利于我們的古籍整理和校勘工作的更好進行。
——————————
參考文獻:
〔1〕陳垣.校勘學釋例(卷六,第四十三,校法四例)[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118-122.
〔2〕時永樂.古籍整理教程[M].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93.
〔3〕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六·與諸同志論書校之難[M].上海:上海書局石印《皇清經解》本,光緒十三年.27.
〔4〕王念孫.讀書雜志·戰國策[M].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2,99.
〔5〕管錫華.漢語古籍校勘學[M].成都:巴蜀書社,2003.160.
〔6〕李山.陳垣“四校法”疏解[J].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4):79-86.
〔7〕杜澤遜.文獻學概要[M].北京:中華書局,2001.180.
〔8〕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M].濟南:齊魯書社,1998.403.
〔9〕沈澍農.校勘法方法的新認識[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149-156.
〔10〕武秀成.古籍校點中他校法的運用及其意義[J].北京圖書館館刊,1994,(1/2):101-110.
(責任編輯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