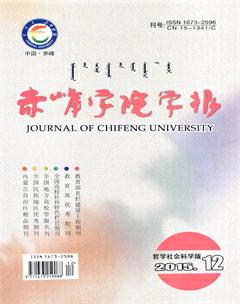失去·尋找·失去
劉亞鈺
摘 要:村上春樹的《國境以南 太陽以西》如何圍繞作者作品中固有的自我主題,向讀者展開追問自我、尋找自我意識的過程,并通過自我他者化的手法,向讀者展開一個虛無的、不可能到達的自我的世界。
關鍵詞:村上春樹;《國境以南太陽以西》;自我意識
中圖分類號:I3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12-0166-02
《國境以南 太陽以西》是村上春樹發表于1992年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的男主人公初是一位在東京經營兩家酒吧、和妻女一起過著幸福生活的成功人士。但是,他的內心里,始終有事業和家庭都填補不了的空洞,而重新遇見小學時的同伴島本,似乎讓他的內心充盈了起來。然而,島本卻不愿吐露自己的過去的一切,總是行蹤不定,在小說的最后,兩人在箱根別墅度過了一夜后,島本終于一去杳然、再無蹤跡可尋了。
在這部作品在發表之后,對這部作品的評論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分化,2000年在德國出版時,評論家馬塞爾·賴希-拉尼茨基盛贊這本書,而另外一位奧地利女批評家西格麗·勒夫則認為這是一本色情的、大男子主義的文學快餐。在日本,也存在關于這是一部有深度的宏大作品還是僅僅是一部迎合大眾口味的平庸的言情小說的爭論。較之村上春樹的其他作品,這部作品中的確很難發掘出非現實性元素和深刻的社會意義,主人公的感情經歷和性經歷占去了作品的大半篇幅,故事的構架也較平鋪直敘,但這仍然是一部透視生活、思考分析現代人生存困境、延續一貫的自我主題、喪失主題的作品。作品沿著失去·尋找·失去的線索,向讀者展開了一個虛無的、不可能到達的自我的世界。
一、失去——不完整的封閉的自我
生于50年代的初,適逢日本戰后第一次人口出生潮。特殊的“獨生子”身份讓初覺得自己是孤獨和“不完整”的,而天生腳有缺陷同為獨生子的島本,和初成為了親密的好友,兩人一起度過了難忘的少年時光,外界對于“獨生子”的強大氣壓,讓島本和初筑起高墻與世界隔絕,封閉在自己世界里,一起品嘗著孤獨與缺失,保護著“驚人的相似的東西”。
作為孩子的初已經意識到了不完整的自我并試圖和島本一起去填補:“想必我們都已感覺到我們雙方都是不完整的存在,并且即將有新的后天性的什么為了彌補這種不完整性而降臨到我們面前。”兩人一起聽著“國境之南”,憧憬著國境之南所象征的沒有缺失的神秘的另一個世界,但是失望的發現國境之南只是指墨西哥。小學畢業后,兩人的交往戛然而止。在此后的歲月里,無論是求學還是工作,初都一個人孤獨而茫然的體驗著青春、離別、背叛。
關于小說中的島本是否真實存在過,是村上留給讀者的謎。村上運用將自我意識投射到他者身上的手法,刻畫了島本這一投射了初的不能實現的自我的形象。和《挪威的森林》一樣,這部作品也是通過將自我他者化這一方式去追問自我的。島本身上有初的內心投影,相比較初的孤僻不合群,島本是一個成績優秀、堅強自律、在班級里很受歡迎、能和人融洽相處的人,在難過的時候也可以假裝快樂的人,島本的身上投射出了初內心中的應該成為的合理自我。但是通過“握手”這一通道,初透過島本的合理自我的外衣,透視出了島本純真脆弱如孩童般的真實自我,認識到她和自己本質上的驚人相似,開始了對純真自我的不懈尋找。少年時代的島本,其實是初的守護者:因為“她照料的并非唱片,而大約是某個裝在玻璃瓶里的人的孱弱魂靈”,而那一張張唱片,正是島本留給初的尋找真實自我的鑰匙。
二、尋找——自我回歸之路
成家立業后的初,看似擺脫了一個人的孤寂生涯,在資本構建的看似繁華的世界里,擁有近似完美的平靜的生活。初代表了戰后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的中產階級的合理而富足的人生,而某天當初在寶馬車里聽著舒伯特時,他突然覺得“我正活在別人的生活中,不是我自己的生活”,音樂這把鑰匙重新開啟了已是中年人的初繼續去尋找某種失去的、理想的東西的路程。
進入70年代之后的日本,與日漸豐盈的物質生活相對的,是人們日漸空虛的精神生活,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正在解體,另一方面,一片繁榮的經濟背后,隨之而來的是泡沫經濟的轟然奔潰,故事發生的1988年,初已經敏感的感受到一步步逼近的殘酷現實,向西伯利亞的農夫一樣,踏上了面向“太陽以西”一直走去,直至死亡的不歸路。
出現在一個雨夜的、重新進入他生活的島本,她的腳已經完全治好,她的外表已經出落的無比美麗,島本又一次投射出初現在看似完美的合理自我,而島本對于過去的只字不提,不定時的消失又不定時的出現,以及幾年前關于島本的一次離奇相遇,都預示著這條尋找之路的虛無與迷茫,時而出現時而消失的島本,正如時明時暗的大海上的燈塔,讓初置身于無法自拔的幻覺中。重逢后他們對于彼此的稱呼,還和少年時代一樣,但是一切卻如水泥在鐵桶里凝固一樣,無法再回到過去。
在村上的其他小說中,處于70、80年代的主人公們,都在不安與迷茫中以各種方式一心一意的“尋找自我”,并且相信只要努力遲早會實現。在這部作品之后,村上就發表了頗受好評的《發條鳥年代記》,很多評論家把這部小說作為《發條鳥年代記》的序章。在《發條鳥年代記》中,主人公不僅在尋找自我,尋找精神出路,還在尋找歷史、尋找人類的真理。在尋找的路上。村上本人也慢慢走進了小說藝術的深處。
三、失去——最終未能抵達的太陽以西
在作品的最后,初和島本有了一次完美的結合,島本答應初“明天”將一切向初坦白。但是在“明天”到來之時,島本、還有象征著鑰匙的唱片都徹底的消失了,“我心目中原有的什么消失了,斷絕了——無聲無息地,然而決定性地”。如同《象的失蹤》中神秘消失的大象一樣,將初一個人留在了“月球那沒有空氣的表層”。
島本真的存在過嗎?“她只存在于我的記憶中”,初這樣想。島本的離去讓初意識到自己的致命缺憾將會一成不變的永遠存在,初回到妻子身邊,體會著寶貴的東西的失去,封閉的安度余生。村上暗示著在這樣一個外部世界里,沒有人能夠逃離,沒有人能夠回避,以平庸、合理的方式活下去可能是個體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唯一選擇。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依然可以無限接近真實自我甚至在那么一瞬間與其完美的結合,我們也可以在內心深處繼續渴求著“太陽以西”。
“太陽以西到底有什么呢?也許那里什么也沒有,或者有什么也不一定,總之和國境以南多少有些不一樣。”島本與初的對話,揭示了國境以南的和太陽以西正是現實性與非現實性的象征,如“世界盡頭”和“冷酷仙境”一樣,是自我意識世界的兩極。太陽以西正是投射在島本身上的過去的、幻影般的世界,是脫離于社會之上的,如島本一樣或許不存在的完美世界,太陽以西和現實世界不僅隔著空間上的巨大空白,還隔著時間上的無法逾越的鴻溝。
這世界本不存在完美的東西,是村上在作品中一直力圖求證的事實。我們想當然的認為我們認識了這個世界,知道自己的缺憾,并且以為可以有填補這種缺憾的出口,正如初認為島本身上有使他完整的東西,為此他愿意不惜一切代價,而事實上這樣完整的自我,這樣完美的世界,只能是深藏于我們內心,無法抵達。
最終的失去與最初的失去,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少年帶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堅信自己失去的東西“它就在那里,我總有一天會到達那里”;中年人在失敗的找尋之后逃回表面上一成不變的生活,而失去后他的內心早已改變,他已不再如年少時充滿幻想,他清楚的知道幻想不會再助他一臂之力了,世界也不會再為他編織什么夢想,他要做的就是將自己浸入無邊的空白,并將這片空白作為最終的歸宿,畢竟比起“沙漠”,空白要好的多。
在自己的酒吧,初要求鋼琴師不要再彈他喜歡的艾靈頓給他聽了。很長以來寄托在喜歡的一首音樂上的某種心情已然消失,通往不存在的世界的鑰匙也已然消失。它依然是優美的音樂,但僅此而已。國境以南是什么沒人知曉,太陽以西永遠走不到。如果抵達不了太陽以西,就只能在現實世界里繼續生活,因為“不存在中間性的東西的地方,也不存在中間”,“其實我們只能在有限的可能性中生存”,抱著這樣的念頭,我們也許就從虛幻的自我意識里抬起頭來,也許就可以遠離沙漠吧。
四、重生于現實生活的初和重新出發的村上春樹
一場看似失敗的逃離中,初卻由此獲得重生,勇敢正視注定不完整的自我,經歷了失去、尋找、失去,盡管未能到達那虛幻的太陽以西,但一切努力并非徒勞,初清楚的向這個世界表達了尋找自我的訴求,將腳步延伸到最隱秘的內心深處,完成了對生命意義的求索。而從今往后,初將為別人繼續編織夢幻,雖然不知這夢幻的作用力有多大,但是也會盡全力去做。雖不知即將到來的明天對自己有多大意義,但是初已經在努力重生。
在一片對《國境以南 太陽以西》的質疑聲中,村上本人并不認為這部作品屬于“文學性退步”之作。村上是在向《發條鳥年代記》這部巨作攀登的途中作為間奏曲而寫下這部作品的,在此基礎上村上才得以繼續向《發條鳥年代記》的頂峰攀登。村上認為這部作品是“確認自己的心之居所”之作,在他的文學人生當中“自有其價值,有其固有的意味”。在此之后,村上改變了習慣性的講述方式,最終導致了村上小說藝術手法和寫作風格的變化。這部在探尋自我意識的道路上的成功作品,對于讀者來說,其中一定潛藏著什么“對自己至關重要的東西”。
——————————
參考文獻:
〔1〕黑古一夫.村上春樹——轉換中的迷失.日本:勉誠出版社,2007.
〔2〕楊炳菁.后現代語境中的村上春樹.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3〕村上春樹.國境の南、太陽の西.日本:講談社,1995.
〔4〕吉田春生.村上春樹、転換する.日本:彩流社,1997.
〔5〕杰·魯賓.傾聽村上春樹: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6〕國境以南、太陽以西.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責任編輯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