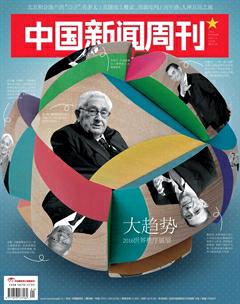中國的絲路愿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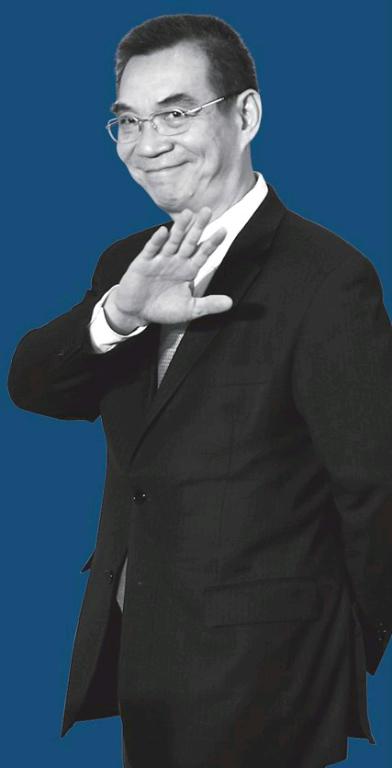
林毅夫。攝影/本刊記者 張浩
林毅夫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jīng)濟(jì)學(xué)家、高級(jí)副總裁,北京大學(xué)國家發(fā)展研究教授兼名譽(yù)院長。
2015年,全球新聞?lì)^條都集中在中國經(jīng)濟(jì)放緩,并充斥著對(duì)中國能否保持改革勢頭、實(shí)現(xiàn)向基于增加國內(nèi)消費(fèi)和擴(kuò)大服務(wù)業(yè)規(guī)模的新增長模式轉(zhuǎn)換的擔(dān)憂。而在中國國內(nèi),對(duì)經(jīng)濟(jì)長期向上發(fā)展軌跡的信心依然強(qiáng)大。事實(shí)上,雖然中國領(lǐng)導(dǎo)人無疑意識(shí)到了增長的放緩,但他們依然致力于確保實(shí)現(xiàn)國家主席習(xí)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戰(zhàn)略,在2016年也將如是。
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戰(zhàn)略開啟后的近40年間,中國已經(jīng)實(shí)現(xiàn)了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成為當(dāng)今全球最大貿(mào)易國和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以購買力平價(jià)計(jì)算則為第一大)。但正如中國領(lǐng)導(dǎo)人所意識(shí)到的那樣,未來還要付出許多努力,以確保實(shí)現(xiàn)習(xí)近平主席提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為了進(jìn)入世界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國必須在國內(nèi)外更高效地利用市場和資源。與此同時(shí),它必須在國際舞臺(tái)上承擔(dān)更多的責(zé)任——并奪取更大的影響力。?
無可否認(rèn),現(xiàn)有的國際秩序有利于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這在該體系于二戰(zhàn)后建立之時(shí)是合理的,但是,如今全球力量平衡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如果中國希望在世界事務(wù)上成為“負(fù)責(zé)任的利益相關(guān)者”——它事實(shí)上也是——就需要在國際決策中發(fā)揮更加突出的作用。
在這一點(diǎn)上將國際共識(shí)付諸行動(dòng)已被證明是極為艱難的。在2009年的G20峰會(huì)上,中國前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達(dá)成了一項(xiàng)協(xié)議,以增加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quán)。但美國國會(huì)在次年否決了這一協(xié)議,因此,它也從未付諸實(shí)施。
事實(shí)上,盡管不斷宣稱中國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一定的國際責(zé)任,但美國似乎一直致力于限制中國的影響力——即便在中國自己所在的區(qū)域也是如此。這也是奧巴馬將戰(zhàn)略“支點(diǎn)”轉(zhuǎn)向亞洲背后的主要?jiǎng)訖C(jī)。同樣,跨太平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TPP)這個(gè)由美國發(fā)起的、包含十多個(gè)環(huán)太平洋國家而排除了中國的動(dòng)議,似乎是要維護(hù)美國的戰(zhàn)略主導(dǎo)地位,保衛(wèi)其在亞太地區(qū)的地緣政治和經(jīng)濟(jì)利益。
總之,要靠中國自己去爭取應(yīng)有和需要的影響力,也是習(xí)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緣由。
這一思路相對(duì)來說簡單而直接。通過從古代絲綢之路的經(jīng)商和文化交流網(wǎng)絡(luò)得到啟發(fā),習(xí)近平的“絲綢之路經(jīng)濟(jì)帶”和“21世紀(jì)海上絲綢之路”將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以及非洲連接起來,最終到達(dá)歐洲。通過在整個(gè)絲綢之路沿線建設(shè)急需的基礎(chǔ)設(shè)施——從連接港口的公路、鐵路,到資源輸送管道,中國希望建立起一個(gè)“擁有共同利益、命運(yùn)和責(zé)任的國際社區(qū)”。
沒有哪個(gè)國家比中國更適合在基礎(chǔ)設(shè)施上起帶頭作用,由于自身的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由國內(nèi)基建項(xiàng)目的大規(guī)模投資所推動(dòng),因此中國在該領(lǐng)域擁有豐富的、新近的操作經(jīng)驗(yàn),更何況中國已經(jīng)擁有龐大的建材行業(yè)。此外,其龐大的外匯儲(chǔ)備——目前為3.5萬億美元并可能繼續(xù)增長——將能為項(xiàng)目提供足夠的資金。
中國已經(jīng)投入部分儲(chǔ)備來充實(shí)最近成立的亞洲基礎(chǔ)設(shè)施投資銀行(AIIB)——這正是中國牽頭來實(shí)現(xiàn)其絲綢之路雄心的戰(zhàn)略機(jī)構(gòu)。隨著全球五大洲57個(gè)國家的加入(包括英、法、德這些不顧美國抗議而加入的美國的親密盟友),亞投行成為第一個(gè)專門設(shè)計(jì)用以滿足發(fā)展中國家,尤其是亞太地區(qū)基礎(chǔ)設(shè)施需求的動(dòng)議。
這些投資的回報(bào)將是巨大的。二戰(zhàn)以來的經(jīng)驗(yàn)表明,那些能夠抓住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國際轉(zhuǎn)移戰(zhàn)略機(jī)遇的發(fā)展中國家可以實(shí)現(xiàn)20~30年的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這將促成更發(fā)達(dá)國家——包括中國所渴求的新市場的崛起,從而為中國高附加值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fàn)幦】臻g。?
由于工資上漲消除了中國在勞動(dòng)密集型制造業(yè)方面的比較優(yōu)勢,低收入國家——比如那些由絲綢之路相連的、其中大部分人均GDP不足中國一半的國家,正在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通過改善基礎(chǔ)設(shè)施,這些國家就能更好地吸納從中國轉(zhuǎn)移過來的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
同時(shí)這個(gè)吸納的規(guī)模也極為龐大。在上世紀(jì)60年代,當(dāng)日本開始向海外轉(zhuǎn)移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時(shí),其制造業(yè)就業(yè)人數(shù)為970萬人。在上世紀(jì)80年代,當(dāng)“亞洲四小虎”經(jīng)濟(jì)體(香港、新加坡、韓國和臺(tái)灣)經(jīng)歷同樣歷程的時(shí)候,它們累計(jì)雇傭勞動(dòng)力達(dá)530萬人。相比之下,中國內(nèi)地的制造業(yè)雇傭了1.25億工人,其中8500萬個(gè)職位是低級(jí)技術(shù)崗位。這足以讓幾乎所有沿著新絲綢之路的發(fā)展中經(jīng)濟(jì)體同時(shí)實(shí)現(xiàn)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
雖然世界對(duì)中國的增長放緩、股票價(jià)格和匯率的回調(diào)感到憂慮,但中國正加緊推動(dòng)一項(xiàng)將為全球經(jīng)濟(jì)帶來不言而喻好處的戰(zhàn)略。除了為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創(chuàng)造出前所未有的機(jī)會(huì)外,“一帶一路”戰(zhàn)略將使中國能夠更好地利用國內(nèi)外兩個(gè)市場和資源,從而強(qiáng)化其作為全球經(jīng)濟(jì)增長引擎的持續(xù)驅(qū)動(dòng)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