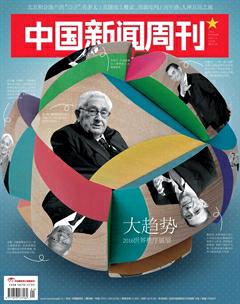從系統角度破解城市問題
賀斌

10月19日,上海西郊。目前中國在城市生活的有7億多人口,其中5億是城市居民,2億是農民工,占城市人口的1/3,因此,能否真正從心理上接受農民工成為市民,將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時隔37年,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再次召開。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最高規格的“全國城市工作會議”。中央層面再次將城市工作列為重大政務主題來研究,因此格外受到關注。
在受訪的專家看來,此次中央城市會議的召開,預示著中國的城市發展思路將由碎片化發展轉向系統化發展模式,從著重建設城市轉向城市治理模式,從而破解目前城市發展中存在的諸多問題。
發展的新時期
此次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對當前中國城市的發展情況進行了分析判斷:在經過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后,中國城市發展已經進入新時期。
同時,會議明確提出未來城市工作的六大原則:尊重城市發展規律;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統籌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和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
此外,會議還提出,將在中西部地區培育發展一批城市群、區域性中心城市,促進邊疆中心城市、口岸城市聯動發展。同時會議還為城市發展劃定了“水體保護線、綠地系統線、基礎設施建設控制線、歷史文化保護線、永久基本農田和生態保護紅線”等六條紅線。而城市的交通、能源、供排水、供熱、污水、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也要按照綠色循環低碳的理念進行規劃建設。
在《中國新聞周刊》采訪的一些專家和業內人士看來,從中央層面召開此次會議是一項戰略性、總體性、全局性的安排,是基于現在城市發展階段面臨的問題和挑戰,遵循了頂層設計的完整思路,會上提出的一些觀點,也非常具有現實性、緊迫性和創新性。
在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石楠看來,此次會議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強調了城市工作是一項系統性工作,提出了城市本身的系統性和城市工作需要遵循的系統原則,這是一個巨大的突破,“現在強調不僅僅是制度要創新、理念要創新,理論也要創新,我覺得這就是理論創新的標志。”
他表示,城市是個復雜的系統,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要有更高的管理技能和管理思路,而系統性也正是城市社會和農業社會最本質的差異。“這次是從中央層面,而且是從最高決策層,從方針政策層面來提出城市工作的系統性,我感到非常欣慰。”石楠說。
近年來業界對于召開全國性城市工作會議的呼聲一直高漲,2010年9月底,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了《中國發展報告2010:促進人的發展的中國新型城市化戰略》研究報告,包括農民工市民化、城市化空間布局、城市化的主體形態、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住房制度和房地產發展、城市建設資金來源以及農民工市民化后承包地和宅基地處置等在內的一些重大問題均有提及。
同時,《中國發展報告》課題組建議,每年以中共中央名義召開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統籌研究城市化發展中的新問題,制定城市化發展的大政方針和政策,部署農民工市民化、城市群發展、城市產業、城市住房、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等方面的工作。
實際上,早在上一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召開之后,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加強城市建設工作的意見》,基本清定了此后約30年時間中城市建設和發展工作的基本思路。
在一些業內專家看來,時隔37年的兩次會議處于不同的時代背景,都適應了當時經濟發展階段和水平的需要。
“1978年,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世界差距很大,當時面臨的城市化問題沒有現在復雜和緊迫,那時候討論大中小城市問題,更多的是看到西方存在這些問題;那時候討論大城市好還是小城市好,主要是受蘇聯經驗影響,希望按照生產資源和生產力配置來組織安排城市布局。”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城市規劃系主任吳唯佳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道。
當時,中國剛開始搞市場經濟,城市化水平很低,經濟發展水平也很低。而現在經濟形勢則完全不同。
“大的環境變了,才導致我們可能需要一系列新的政策、新的舉措、新的理念。”石楠分析說。
在他看來,這兩次會議,中國面臨的挑戰也不同。1978年的時候,經濟發展是中心任務,“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把經濟搞上去,是壓倒一切的大局,所以那時候的重點是趕上發達國家,盡快實現經濟的增長和騰飛,能夠把總量做大,采取了改革開放政策,采取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種差異化的政策。
“從經濟關系角度來講,現在一方面要繼續增長,繼續做大蛋糕,另一方面是怎么切蛋糕,怎么實現經濟分配更公平。”石楠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現在已經實現了第一步,即“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正開始進入第二步,就是讓剩下的一部分人跟著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共同富裕,實現全面小康,這是很大挑戰。
“現在是很重要的時間點。隨著國家城市人口數量越來越大,工業經濟、服務業經濟比重越來越高,經濟發展對城市發展的依存度也越來越密切,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城市發展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中國正處在一個交匯點上,在這個時候,停下來仔細思考研究我國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的相互關系,十分有必要。” 吳唯佳表示,這次會議能將城市工作提到中央的高度,可以說對新時期乃至未來一段時間,城市發展和城市工作在國家發展戰略布局的重要地位發出的了一個明確信號。
城市化和“城市病”
1979年,美國地理學家諾瑟姆在總結歐美城市化發展歷程的基礎上,把城市化的軌跡概括為拉長的S型曲線。
他把城市化進程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城市化起步階段,城市化水平較低,發展速度也較慢,農業占據主導地位;二是城市化加速階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城市化推進很快。隨著人口和產業向城市集中,市區出現了勞動力過剩、交通擁擠、住房緊張、環境惡化等問題,小汽車普及后,許多人和企業開始遷往郊區,出現了郊區城市化現象;三是城市化成熟階段,城市化水平比較高,城市人口比重的增長趨緩甚至停滯。在有些地區,城市化地域不斷向農村推進,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和工商業遷往離城市更遠的農村和小城鎮,使得大城市人口減少,出現逆城市化現象。
對三個階段的劃分,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標準。一般認為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為起步期;30%~70%為快速發展期;70%以上為穩定期。其中,快速發展期以50%為界,分為兩個階段:50%之前是增速發展階段,50%~70%是降速發展階段。
根據中國社科院2015年9月發布的《城市藍皮書》,截至2014年底,中國城鎮化率已達到54.8%,預計到2020年將超過60%,到2030年將達到70%左右。
“目前中國城市化發展已經到了快速發展的降速階段,城市化發展速度會逐步下降,不能再人為推動加速城市化。”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石楠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在積極推動城市化的同時,要把質量提升作為這一階段的核心任務,實現速度和質量并重,而且更加注重質量。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人涌向北上廣等特大城市,造成這些地方的公共服務資源越來越緊張,本地居民和外來移民之間的矛盾也愈加激烈;樓房越來越高,也越來越貴;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嚴重不足,又造成城市擁堵和效率低下;空間越來越小,環境越來越差,空氣越來糟糕。當人們一窩蜂涌向大城市和城市時,卻發現“城市”這個曾經承載著夢想的詞匯,逐漸變成了一場噩夢。
“這是‘城市病。”有人發明了這個詞,殘酷卻又精準。
對此,吳唯佳卻沒有這么悲觀,在他看來,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問題,經濟規模越來越大,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高,城市總是處在基礎設施供給和需求不平衡之中。城市本身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和動力,經濟增長的同時總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問題,需要通過發展和轉型來解決。
“城市化不完全是個數字和百分比,也不光是戶籍制度。在未來,也許有一部分人在農村生活,卻從事城市的工作和勞動,不能以城市邊界劃定農村和城市的生活。”吳唯佳說。
在石楠看來,城市發展到現階段,一些社會矛盾和現實問題都會暴露出來。現在已不僅僅是供需總量矛盾的問題,而是結構不平衡,效益不高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居民有了新的訴求,不僅要擁有自己一部分財產,更重要的是參與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參與到社會治理的過程,由此也出現了很多社會矛盾,而“城市病”只是一個表征現象。矛盾的解決不能只靠城市里的每個個體,不能只靠某一個政策、某一個文件、某一個部門解決,必須是靠系統的思路,靠規劃,綜合地解決。
市民化的關鍵在縣域和小城鎮
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石楠認為,應該從制度層面提出來加以解決。“我們在過去3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初期,將城門打開讓農民進城,卻并沒有真正給他們一個平等的安家樂業的機會,很少關注這2億多農民工是否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樣的權利和機會。”
但他同時指出,除了制度,還需要原有的城市市民轉變觀念,真正從心理上接納他們。
目前中國在城市生活的有7億多人口,其中5億是城市居民,2億是農民工,占城市人口的1/3,因此,能否真正從心理上接受農民工成為市民,將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對此,吳唯佳表示,城市化率主要是看常住人口,但實際上常住人口中的常住外來人口,也即農民工的比例還很高。我國以城市戶籍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也只有40%左右。從城市人口的流動狀態來講,由于人口流動是城市的主要特點,市民化就不能追求百分百,因為這不符合城市人口流動的規律。
“不可能所有人都成為城市市民,農業是國家發展的根本,我們國家還需要一定比例的農業人口。對于城市而言,一年大概有多少常住外來務工人口轉為市民,需要遵循城市經濟發展狀況、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安置能力等基本條件,根據各地發展狀況來決定。”吳唯佳表示。
那么,應該在哪兒實現市民化?是北上廣這樣的特大城市嗎?對此,石楠給出了否定答案,在他看來,全國有600多個城市2萬多個鎮,從導向來講,不能把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群作為農民工市民化的主體,而是要把縣域城鎮化,縣城以下的建制鎮城鎮化,作為農民工就地就近城鎮化的最主要流向。
“但問題是這些縣域和鎮本身承載力是否足夠,有沒有一定的吸引力?如果吸引力不夠,承載力不夠,就業也不夠,怎么能吸引農民往那兒去?大家還是會往特大城市擁堵,所以需要相關制度和政策的配合,甚至還需要一些具體措施。”
石楠解釋說,比如有關政策資源、資金和人才、項目等,要給予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更多傾斜,還要加大培訓力度,幫助農民工提高素質、提高技術、提高能力,這需要政府、教育機構和社會組織一起來做。“市民化是關注社會長治久安的非常重要的戰略問題,一定要從制度層面加大力度。”石楠說。
讓市民參與規劃治理
此次會議對城市工作提出了五個統籌的要求,基本囊括了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受到了業內和學者的普遍贊同。
其中,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最為核心,旨在提高各方推動城市發展的積極性。這也將城市工作的落腳點最終放到了“人”的上面。
“這就是一種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思路的落實。”石楠認為,整個城市工作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很多領域,而大量的行為主體是企業,中國處于市場經濟逐步完善階段,市場主體在很多時候起關鍵作用,政府只是搭臺,制定規則和彌補市場失靈,民眾才是社會最關鍵的參與者和管理者,不能簡單看作人民城市人民建。
“這也是下一步城市工作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石楠認為,必須提高全社會的城市意識,使大家意識到自己生活在城市社會,需要一套新的城市治理理念,不能按照管農業社會農耕文明的思路管理城市,這無論是對決策者和相關部門,還是對于企業和社會公眾,都是需要特別強調并關注的。
在受訪者們看來,此次會議最重要的突破是強調要統籌“政府、社會、市民”等三大主體,“鼓勵企業和市民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城市建設、管理,其中核心要義是關注生活在城市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