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積極心理學的視角提升本科生的主觀幸福感
謝建軍



【摘要】本研究旨在通過實驗干預提升本科生的主觀幸福感。本文的兩個實驗都以牛津幸福感量表為測量主觀幸福感的工具。實驗一采用實驗組對照組重復測量設計的方法。實驗一的結果顯示:運用寫“幸福日志”的方法,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本科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實驗二采用多組實驗組控制組重復測量的設計方法。實驗二的結果表明:上積極心理學課程和寫感謝信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被試的主觀幸福感。從實驗一和實驗二的結果得出結論:從積極心理學的視角,運用寫“幸福日志”和寫“感謝信“的方法,的確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本科生的主觀幸福感。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本科生縱向干預重復測量
1.文獻綜述
國內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是從理論建構和人口統計學上的比較以及影響因素三個方面來進行的。而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研究主觀幸福感主要是對國外研究的一些綜述,很少有對提高人們的主觀幸福感進行實證研究。截止到本文開題時,只檢索到了一篇關于對初中生的主觀幸福感進行實驗干預的研究。
國外近10多年來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逐漸從社會學,倫理學和經濟學轉向心理學。而心理學主要是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對提高人們的主觀幸福感的實驗研究。并且其研究范圍越來越廣,時間跨度越來越長,研究方法層出不窮。尤其是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由前美國心理協會(APA)主席和心理學家塞里格曼(Seligman)所倡導的,并且由他領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積極心理學研究中心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進行了大量的關于提高人們幸福感的實證研究(例如:心理學家塞里格曼等人(Seligman,2005)招募了一批志愿者去訪問積極心理學網站。他們分別用網站上積極的練習(練習一周內每天用新的方式運用自己的優勢特征)和一般的中性練習對志愿者進行實驗干預。研究結果表明:那些被提供積極練習的志愿者的主觀幸福感在接下來的6個月都有所提高。另外,研究(Emmons,&McCullough,2003)發現:主動地鼓勵人們去增強情感狀態中積極的方面可以使他們變得更加健康和擁有更加愉快的心情。那些被指派思考并寫下他們最深刻積極體驗的大學生比那些只要求寫中性話題的大學生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更少去學校的心理健康中心求助。那些參與感激實驗干預的被試,在多次寫下他們感激的事件之后,報告說感到生活更加美好并且體驗更多的積極情緒[1]。
2.問題提出和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意義
2.1問題的提出
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對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和相關研究固然重要。但是,著力研究得到幸福的各種途徑及其具體操作方法,從而真正地提高人們的主觀幸福感迫在眉睫并且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然而,縱觀國內關于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對國外研究的綜述,或者只是對不同人群的主觀幸福感及其關系進行描述,或者是對主觀幸福感進行一些理論方面的建構。很少有對提高人們的主觀幸福感進行縱向的干預實驗研究。而國外,尤其是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由前美國心理協會(APA)主席和心理學家塞里格曼(Seligman)所倡導的,并且由他領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積極心理學研究中心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進行了大量的關于提高人們幸福感的實證研究。基于以上現狀,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了以下三個關于如何提高人們主觀幸福感的實驗研究。
2.2本研究的目的
1)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通過對大學生進行實驗干預,以求達到提高實驗參與者的主觀幸福感;
2)驗證深圳大學開設積極心理學課程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3)為提高國民幸福指數(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證支持。
2.3研究意義
1)理論意義——在繼承和發展傳統心理學的基礎上,對傳統心理學加以補充,豐富從心理學的角度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
2)現實意義——通過提高人們的主觀幸福感,從而預防和減少心理障礙的發生,進而促進社會的和諧健康發展。
3.研究方法
3.1實驗一:通過寫幸福日志提升本科生的主觀幸福感
3.1.1實驗一設計:采用實驗組對照組重復測量設計方法
3.1.2實驗一被試
以深圳大學選修“積極心理學”課程的兩個班所有學生為被試。他們是不同年級(大一至大四)和不同專業的本科生,且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其中一個班的人數為25人,上課時間為每周二晚上,將該班作為實驗班;另一個班的人數也為25人,上課時間為每周三晚上,作為對照班。
3.1.3實驗一材料
1)牛津幸福感量表(TheOxfordHappinessInventory,OHI)
2)幸福日志本(TheHappinessJournalorHAOJournal)。
給每位學生準備一個50頁左右的本子。要求實驗組的學生每天(每周至少五次)在一頁上記錄下當天發生的三件快樂的事情(H-happiness)和三件值得感激別人的事情(A-appreciation)以及三件樂觀的事情(O-optimism).而讓控制組的被試寫一般的日志。
3.1.4實驗一步驟
在開學后第二周的上課期間,用修訂過的牛津幸福感量表分別對兩個班的同學進行實測,作為前測成績。實驗班和對照班分別收回有效問卷25份和23份。在周二晚的課堂上示范實驗班的學生寫幸福日志,每周至少寫五天。在周三晚的課堂上讓對照組的學生寫普通日記,同樣每周至少寫五天。三個星期后,即第五周,分別對兩個班用牛津幸福感量表進行實測,作為后測成績。實驗班和對照班分別收回有效問卷23份和22份。五個星期后,即第七周,再次分別對兩個班進行施測,作為后測成績。分別收回有效問卷22份和21份。
3.1.5實驗一結果


3.1.6實驗一討論
從以上實驗結果表一和圖一得知:盡管在實驗干預前實驗班在牛津幸福量表上的得分比控制班的得分低一些,但是經過實驗干預后,實驗班在牛津幸福量表上的得分不斷上升,三個星期和五個星期后的得分都高于控制班相對應的得分。而控制班的得分是先有所下降,然后再上升。盡管控制班所測分數上升的幅度不小,但還是小于實驗班所測分數上升的幅度。這表明實驗干預的確起到了提高被試主觀幸福感的作用。實驗二的結果證明了從積極心理學的視角,運用寫“幸福日志”的方法,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本科學生的主觀幸福感。但是,實驗一存在的一個很大問題是所有被試都是選修積極心理學課程的學生。針對這一不足之處,作者們設計了實驗二,以求有所改進。
3.2實驗二通過寫感謝信提升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
3.2.1實驗二目的
通過開設“積極心理學課程”和“寫感謝信”活動,采用不同的干預方式對本科生進行干預研究,考察不同干預方式對本科生主觀幸福感提高的效果。
3.2.2實驗二被試
以深圳大學2個“積極心理學”課程班級的本科生和1個“英語口語交際”的本科生。分別作為實驗組1,實驗組2和控制組。
3.2.3實驗二材料
1)用因素分析法修訂后的牛津幸福感量表(TheOxfordHappinessInventory,OHI)。(在實驗一中已經介紹過了)。2)感謝信樣例。
3.2.4 實驗二設計

3.2.5實驗二步驟
1)前測:在開學后的第二周分別對實驗組1,實驗組2和控制組三個組進行施測,采用統一的指導語。
2)在開學后的第三周要求實驗組2的被試寫感謝信。并告知被試完感謝信后,最好是能夠親自當面讀給被感謝的人聽。若這個難以做到,至少要確保被感謝人接收到所寫感謝信。
3)寫感謝信一周后測量,即開學后的第四周,采用統一的指導語分別對實驗組1,實驗組2和控制組三個組進行施測。
4)寫感謝信一個月后再次測量,即第八周,采用統一的指導語分別對三個組的被試進行集體施測。
5)后測:寫感謝信三個月后最后測量,即第16周分別對實驗組1,實驗組2和控制組三個組進行施測,采用統一的指導語。
3.2.6實驗二數據分析
采用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重復測量分析的方差分析和事后檢驗。
3.2.7實驗二結果

3.2.7實驗二討論
以上結果表3和圖2顯示:上積極心理學課程和“寫感謝信”活動相結合的干預方式與僅采用上積極心理學課程的干預方式都可以提高學生感戴和主觀幸福感,但是前者比后者更加有效。理由是,在對被試進行實驗干預前,對照組在牛津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高于兩個實驗組,并且既上積極心理學課程的實驗組2的測量分數最低。而在實驗干預過程中,僅上積極心理學課程的實驗組1在牛津幸
福感量表上的得分穩步上升并最終超過對照組。實驗組2的所得分數在每次測量時都增加地十分明顯并且在最后測量時的分數大大地超過其他兩組被試。而控制組所得的分數基本不變,甚至在第三次測量時有不小幅度的下降。所得分數下降的最可能的原因是那次測量的時間正好為“十一”長假過后的一周。學生在假期后回到學校,需恢復相對忙碌的課程學習,并且很有可能須完成和提交不少作業,甚至還有可能須參加階段性的測驗。這就在某種程度上給學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負擔,從而使得他們的主觀幸福感在短期內受到影響。那么,怎樣解釋相同的生活事件卻對兩個實驗組的被試影響不大呢?原因可能是,上“積極心理學”課程和寫“感謝信”這些實驗干預活動在應對學業壓力時,不僅起了緩解作用,而且還具有積極的學習動力效果。
4.總討論
4.1關于本文對主觀幸福感水平測量工具的評價
本研究兩個實驗中的測量工具均為牛津幸福感量表(TheOxfordHappinessInventory,OHI)。盡管有學者證實了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時間跨度較長和被試地理分布較廣的重測信度都很高,且本文作者也運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對其進行了效度檢驗,結果也顯示出了該量表的單維性。然而,運用到中國文化背景下,還是具有不適之處。因此,有待對其進行修訂。
4.2關于本研究中不同干預方式的研究結果的分析
本研究結果基本驗證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設,即通過寫“幸福日志”和“感謝信”以及上積極心理學課程對深圳大學的本科生進行實驗干預,能提高他們的主觀幸福感。因為經過實驗干預,設有對照組的實驗一和實驗二,實驗組的參與者在牛津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都在不小程度上提高了。
4.3本研究與之前同類研究的比較
實驗二的研究結果與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積極心理學研究中心的Seligman等人的讓被試寫三件好事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中的實驗組在牛津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提高了13.5%,高于其9%[2]。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存在文化方面的差異和實驗干預的內容也有所不同。因為在SeligmanE.Martin等人的研究中,被試的任務主要是寫三件愉快的事情。而本研究中的實驗二將中國文化背景下的“好”字的拼音“hao”與英文單詞Happy(幸福的),Appreciative(感激的)和Optimistic(樂觀的)的首字母相結合。從而設計了幸福日志表單(HAOJournal),要求被試不僅要寫三件愉快的事情,還須寫三件值得感激的事情和三件樂觀的事情。這使得實驗干預對提高被試的主觀幸福感具有更大的效果。這表明實驗干預的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提高實驗組被試主觀幸福感的作用。進一步分析各組前測與后測分數發現:控制組在牛津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有所下降,而實驗組的得分則大幅的提高。出現這種現象的可能原因是:讓控制組的被試寫一般日記,由于他們
不清楚寫日記的目的,而且,平時很有可能沒有寫日記的習慣,這樣寫日記對他們可能是一種負擔,而由此產生一些負性情感體驗。相反,實驗組的被試在寫幸福日志的過程中可能體驗到了一些積極的情感體驗,從而最終提高了他們的主觀幸福感。
實驗二的研究結果與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Lyubomirsky等人的研究結果相比,只接受上積極心理學處理的實驗組一的被試在牛津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只提高了5.2%,低于他們研究中的只被激勵組的對應提高分數,10%。類似的是,既接受上積極心理學處理又寫感謝信的實驗組二,與他們研究中的既被激勵組又寫感謝信的被試相比,所得分數盡管提高了13.8%,仍然低于其對應提高分數,15%[3]。同樣,實驗組二的參與者比控制組的參與者的分數提高多出約13.9%,這一數字也低于戴維斯市加利福尼亞大學的Emmons教授的同類研究的對應分數,25%[4]。以上實驗結果的比較都可部分歸因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含蓄與西方文化的開放性和情緒表達的直接性之間的差異。例如,絕大部分的西方人,將“Iloveyou!”常掛在嘴邊,而與之相反的是,很少有中國人在公眾場合說“我愛你。”甚至對自己的伴侶和親生父母也難以啟齒。
然而,實驗二中的實驗組2的結果與Seligman等人的來自其積極心里實驗室的“感恩拜訪”研究相比[5],參與者的分數提高百分比為13.8%,高于他們的對應分數,約10%。可能的解釋是,要求被試在寫完感謝信給被感謝人之后,還要求他們去拜訪被感謝人。這種讓人們制定一個正式的感恩計劃的做法,考慮到時間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則有些不太實際。
國內方面,本研究中實驗二的結果與河北師范大學的石國興,祝偉娜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他們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班級輔導和“列舉恩惠”活動相結合的干預方式與僅采用“列舉恩惠”活動的干預方式都可以提高學生感戴和主觀幸福感,但是前者比后者的效果好[6]。根據感恩的拓寬建構理論,感恩體驗及由其激發的行為,建構了心理的、社會的和精神的資源,并鼓勵人們去關注從他人那里得到的恩惠,從而使人們體驗到他人的愛和關心,最終提升自己的幸福感[7]。國外的研究表明,感恩和主觀幸福感緊密聯系,高感恩的人通常有較多的積極情感和較高的主觀幸福感[8]。
另外,本研究中兩個實驗的結果也可以從腦科學的生理基礎方面進行解釋。通過寫“幸福日志”和“感謝信”,使被試記住和回憶一些開心的事件以及感激的需要得到了實現,會刺激大腦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和類啡肽激素[9]。這些生理激素具有促進大腦的愉快中樞興奮的功能,從而增加個體對積極情緒的體驗,最終提高人們的主觀幸福感。
5.本研究的結論
從積極心理學的視角,運用寫“幸福日志”和“感謝信”的方法,的確在
不同程度上提高了本科生的主觀幸福感。
參考文獻
[1] Emmons R .A.,McCullough M. E. Counting blessings versus burdens: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in daily lif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4 (2): 377 - 389.
[2] Martin E. P. Seligman, Nansook Park, Christopher Peterson. Positive Psychology Progress: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Intervention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5, 60(5): 410-421.
[3] Lyubomirsky, Dickerhoof, Boehm. The influence of Motivation, optimism and gratitud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8.
[4] 羅伯特·艾蒙斯/著. 伍鐵/譯. 感恩:成功花朵的快樂種子[M].第1版.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8:36 - 45.
[5] 羅伯特·艾蒙斯/著. 伍鐵/譯. 感恩:成功花朵的快樂種子[M].第1版.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8:61- 63.
[6] 石國興,祝偉娜. 初中生感戴和主觀幸福感的干預研究[J]. 心理學探新,2008, 28(3)
[7]. 劉建嶺. 感戴: 心理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C].河南:河南大學論文, 2005.
[8] McCullough M. E,Emmons R. A. & Tsang J. A. The grateful disposition: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opography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2,82 (1) :112 – 127.
[9]Lyubomirsky S, Sheldon K. M. & Schkade D. Pursuing happiness: The architecture of sustainable change.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5, 9 (2): 111 -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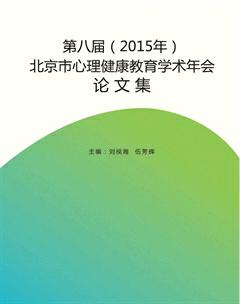 北京心理衛生協會學校心理衛生委員會學術年會論文集2015年1期
北京心理衛生協會學校心理衛生委員會學術年會論文集2015年1期
- 北京心理衛生協會學校心理衛生委員會學術年會論文集的其它文章
- 論教師話語與兒童情緒情感發展
- 小學心理活動課融入品德教育的研究
- 孤山獨秀絕非夢中風景
- 學生的學習情緒對課堂教學效果的影響
- 論隔代教育與兒童的心理發展
- 論心理咨詢理論與方法的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