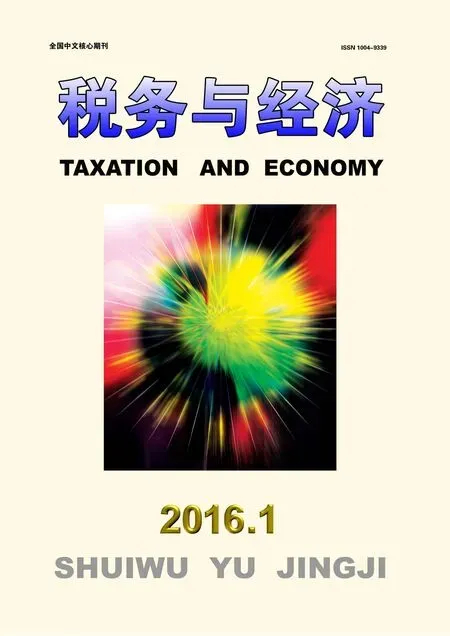產業結構調整與稅收增長:抑制還是促進
李普亮
(惠州學院 經濟管理系,廣東 惠州 516007)
一、引 言
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正在由過去的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據統計數據顯示,1979~2011年,我國GDP平均增速高達9.9%;但自2012年起,GDP增速告別了以往高增長態勢,開始步入“7時代”。值得關注的是,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同時,產業結構調整的進程卻在不斷加快。2013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46.1%,超出第二產業2.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4年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進一步上升至48.2%,超出第二產業5.6個百分點;而在2015年上半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49.5%,超出第二產業5.8個百分點。然而,與產業結構持續升級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稅收收入增速卻呈現不斷下降態勢。2012年稅收收入同比增長12.1%,較2011年下降10.5個百分點;2013年和2014年的稅收收入增速分別進一步降至9.8%和7.8%;而在2015年上半年,稅收收入增速僅為3.5%。
我國稅收收入增速與GDP增速表現出了較強的一致性,符合經濟決定稅收的邏輯。但經濟對稅收增長的影響不僅僅取決于經濟規模的大小,同時與經濟結構息息相關。產業結構作為經濟結構的核心內容,對稅收增長的影響不容忽視。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能否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與稅收持續增長的目標兼容值得深入探究。
從理論界的相關研究看,經濟增長對稅收增長的影響受到了廣泛而持久的關注,但產業結構調整與稅收增長的關系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在為數不多的實證文獻中,郭慶旺和呂冰洋(2004)以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產值比不斷上升作為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的度量指標,基于1997~2002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產業結構變化對稅收收入的影響,研究發現,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產值比提高明顯有利于稅收總收入的增長,但這種影響存在區域性差異。[1]然而,這一研究至今已10年有余,產業結構調整與稅收增長的關系有無發生新變化需要持續跟蹤。萬瑩和史忠良(2009)利用2007年統計數據,對中國各地區間稅收負擔率與產業結構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分析,證明在現行稅制下,第三產業的發展與稅收增長之間確實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2]馮瑜(2011)運用統計模型對1994~2010年稅收收入與產業結構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第二、三產業經濟增加值增長與稅收增長呈正相關關系,其中代表產業發展方向的第三產業影響最大,第二產業次之,第一產業經濟增加值對稅收呈負增長關系。[3]韓秀蘭和王久瑾(2013)采用對數平均D氏指數方法,對山西省地方稅收、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之間的定量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論顯示,山西省經濟增長對稅收增長的產出效應最大,產業結構效應次之,行業稅負效應最小。[4]
上述文獻為理解產業結構調整與稅收增長的關系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由于多數文獻通常采用截面數據或時間序列數據檢驗產業結構對稅收收入的影響,不僅樣本容量較小,而且無法考慮地區間異質因素的影響,估計結果的可靠性有待商榷。另外,已有文獻側重考察產業結構對稅收收入總量的效應,但沒有考慮其對稅收收入增速的影響。為此,本文基于我國31個省(市)2007~2013年的面板數據,不僅實證檢驗了近些年來產業結構調整對稅收收入總量的效應及其區域性差異,而且進一步考察了產業結構調整對稅收收入增速的影響及其區域性差異,進而可為協調產業結構調整與稅收增長的關系提供新的啟示。
二、產業結構與稅收收入的演進軌跡:1994~2014*由于1994年我國工商稅制進行了重大改革,為了保持數據可比性,本文以1994年以后的相關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一)產業結構的變化特征
圖1顯示了1994年以來我國GDP構成的變化趨勢。

圖1 1994年以來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
從圖1不難看出,自1994年以來,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由1994年的19.9%降至2014年的9.2%,累計下降10.7個百分點,降幅高達53.8%。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年際間雖有波動,但總體較為平穩,由1994年的46.6%降至2014年的42.6%,累計下降4個百分點,降幅為8.6%;特別是自2009年以來,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現持續下降態勢。相比之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總體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由1994年的33.6%升至2014年的48.2%,累計增加14.6個百分點,增幅高達43.5%;特別是自2013年以來,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續高于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上述數據表明,我國產業結構正在實現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戰略性轉變,符合國際上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但由表1可以看出,與部分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和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還明顯偏高,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明顯偏低;即便與“金磚國家”中的其他四個發展中國家相比,同樣如此。因此,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將是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
另外,中國的信息化進程正在加速,在信息化推動下的經濟結構的服務化是產業結構升級的一種重要特征,鑒于在“經濟服務化”過程中的一個典型事實是第三產業的增長率要快于第二產業的增長率(吳敬璉,2008)[5],一些學者還傾向于選取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度量指標;即便從這一角度看,我國產業結構也在波動中趨于優化(如圖2所示)。

表1 中國GDP構成的國際比較(2012年)

圖2 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走勢圖
(二)稅收收入的變化特征
自1994年工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稅收收入規模不斷擴大,由1994年的5126.88億元增至2014年的119 158億元,增長23.2倍,年均增長17.0%;而同期名義GDP則由48 197.9億元增至636 463億元,增長13.2倍,年均增長13.8%,低于稅收收入增速3.2個百分點。圖3顯示,1995年以來,除個別年份外,我國稅收收入增速均高于名義GDP增速,由此導致稅收收入占名義GDP的比重由1995年的9.9%攀升至2014年的18.7%。但需要注意的是,稅收收入增速在年際間呈現出較強的波動性。在過去的20年中,稅收收入增速最高可達31.2%(2007年),最低僅為7.8%(2014年),相差23.4個百分點;特別是自2012年以來,稅收增速持續走低。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隨著我國經濟逐步邁向新常態,稅收增長也將相應步入新常態。

圖3 稅收收入增速與GDP增速對照圖
(三)產業結構調整與稅收收入增長的相關性
根據產業結構的演進軌跡及稅收收入的增長趨勢,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產業結構調整究竟抑制還是促進了稅收增長?如果能夠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稅收持續增長的目標兼容,那么各級政府將有充分的激勵加快產業結構調整進程;否則,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協調產業結構調整與稅收增長的矛盾。圖4顯示了1994年工商稅制改革以來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與對數化稅收收入的散點圖,二者整體上呈現明顯的正相關。
圖5 顯示了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與對數化稅收收入的散點圖,兩個變量之間同樣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正相關。
為了更加全面地刻畫產業結構調整與稅收增長的關系,本文還進一步分別繪制了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與稅收收入增速的關系(見圖6和圖7)。與圖4和圖5顯示的結果有所不同,產業結構調整與稅收收入增速整體上呈現出一定程度的負相關。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初步推斷,產業結構調整很可能促進了稅收收入總量增長,但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

圖4 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與對數化稅收收入散點圖

圖5 第三產業增加值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與對數化稅收收入散點圖

圖6 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與稅收收入增速散點圖

圖7 第三產業增加值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與稅收收入增速散點圖
三、產業結構調整對稅收增長效應的實證檢驗
(一)模型設定及變量說明
為檢驗產業結構調整對稅收增長的效應,本文設定如下形式固定效應模型:
lntaxi,t=αi+β1structurei,t+β2lnpergdpi,t+εi,t
(1)
taxratei,t=αi+φ2lnpergdpi,t+εi,t
(2)
在上述兩個模型中,tax代表稅收收入總量;taxrate代表稅收收入增速;structure表示產業結構調整,分別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tratio)和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度量(stration);pergdp為各省人均GDP,用以控制經濟發展水平對稅收增長的影響;αi為個體效應,用于控制難以觀測的地區異質因素的影響;i和t分別代表省份和年份。
本文實證分析數據主要源于2008~2014年的《中國統計年鑒》。為剔除價格因素影響,本文利用以2007年為基期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對各省稅收收入進行了價格調整,用人均GDP指數對各省人均GDP進行了相應調整。同時,為了減小異方差影響,本文還對tax和pergdp進行了對數化處理。各個變量的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注:稅收收入(tax)、人均GDP(pergdp)兩個變量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二)實證結果
本文首先對模型(1)和(2)進行了冗余固定效應似然比檢驗,檢驗結果拒絕了不存在固定效應的原假設,繼而對上述模型進行了固定效應估計,實證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不難看出,當以lntax為被解釋變量時,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tratio)的系數在統計上顯著為正,表明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有利于稅收收入總量增長;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stration)的系數同樣為正,但在統計上不太顯著。總的來看,加快以第三產業發展為著力點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地方政府增加稅收收入的目標并行不悖。但當以taxrate為被解釋變量時,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stration)、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stration)的系數在統計上均顯著為負,這意味著加快以第三產業發展為著力點的產業結構調整雖然有利于增加稅收收入總量,卻降低了稅收收入的增速。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近年來我國較為嚴格地限制了高污染、高能耗行業的發展,加之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速出現較大幅度放緩的態勢,在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速也穩中趨緩的條件下(見圖8),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及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相對升高,但第二產業增加值和第三產業增加值的同時放緩卻導致了稅收增速的放緩。因此,出現產業結構升級與稅收收入增速反向變化的現象并不足為奇。二是我國第三產業中,傳統服務業所占比重較高。以2012年為例,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批發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等傳統服務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達37.1%。這些行業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較低,對稅收貢獻相對較小。而金融、現代物流、信息技術服務、租賃和商務服務、創意和設計服務、研發和技術服務等附加值較高的現代服務業規模相對較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服務業發展對稅收增長的貢獻。另外,人均生產總值(pergdp)與稅收收入總量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與預期吻合,但其對稅收收入增長速度卻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主要是因為人均GDP較高的地區通常稅收收入基數較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稅收收入增速的提升。

表3 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
注: *、**和***分別代表10%、5%和1%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標準誤經Cross-section weights (PCSE)校正。

圖8 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速與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速對照圖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異,各地的產業結構也不盡相同,為了檢驗產業結構調整對稅收增長的影響是否存在區域性差異,本文進一步將樣本劃分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兩個子樣本*其中,東部地區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其余省(市)劃入中西部地區。,對模型(1)和(2)再次進行估計,結果如表4和表5所示。
對比表4和表5不難發現,從稅收增速的角度看,無論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都對其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抑制效應,而且中西部地區的這種抑制效應要大于東部地區。而從稅收收入總量的角度看,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對稅收增長的效應存在較大差異;其中,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顯著促進了稅收增長,而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對稅收增長則沒有表現出積極影響。概而言之,與發達地區相比,欠發達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對稅收增長的效應更不樂觀。主要原因在于,相對于發達地區而言,欠發達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進程較為緩慢,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程度較低,服務業中傳統服務業占比較高,而且規模較小,層次不高,而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稅收的現代服務業比重明顯偏低,進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產業結構調整對稅收增長的促進效應。

表4 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東部地區)
注: *、**和***分別代表10%、5%和1%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標準誤經Cross-section weights (PCSE)校正。

表5 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中西部地區)
注: *、**和***分別代表10%、5%和1%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標準誤經Cross-section weights (PCSE)校正。
四、結論與政策含義
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將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逐步成為主體。按照經濟決定稅收的邏輯,經濟運行呈現出的新特征必將對稅收產生一定的影響。從相關統計數據來看,近年來,隨著產業結構調整的不斷推進,稅收增速反而呈現下降態勢,那么,這是否意味著產業結構調整抑制了稅收增長?本文分析表明,如果以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度量指標,則產業結構調整會促進稅收收入的總量增長,但卻抑制了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這主要緣于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主要是在第二產業增速明顯放緩的條件下實現的,同時第三產業的層次較低,傳統服務業占比較高,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稅收的現代服務業規模相對較小,第三產業的發展質量和效益整體上有待進一步提升。分區域看,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對稅收增長的積極效應弱于東部地區,表明欠發達地區服務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尤其不容樂觀。
產業結構調整有利于稅收收入總量的擴張。從這一角度看,對于各級政府來說,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與其追求稅收增長的目標是兼容的,應當不遺余力地摒棄傳統發展方式,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的要求,將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作為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來抓,并以此作為穩定稅收增長的重要舉措。盡管產業結構調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稅收收入增速,但這并不能否定產業結構調整對稅收增長的貢獻,關鍵是要在做強第二產業的基礎上更好地發展第三產業,大力優化第三產業的內部結構,逐步增加現代服務業比重,重點發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稅收、低污染的相關行業,確保第三產業有質量、有效益地增長。事實上,雖然我國稅收增速整體放緩,但不同行業的稅收增速存在很大差異,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稅收增速較為可觀。以2015年一季度為例,第三產業稅收收入增長3.9%;其中,金融業稅收增長33.4%,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稅收增長22.7%,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稅收增長14.1%,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稅收增長10.4%。為此,應堅持市場主導與政府引導相結合的原則,既要積極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落實投資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充分激發市場活力,又要綜合采用財政、稅收、金融、科技等優惠政策引導資金、技術、勞動等生產要素向現代產業部門轉移,大力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確保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與稅收增長的協同。
[1]郭慶旺,呂冰洋.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調整對稅收增長的影響[J].涉外稅務,2004,(9):11-16.
[2]萬瑩,史忠良.中國地區間稅收負擔率與產業結構關系的實證分析——以2007年數據為例[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09,(6):21-24.
[3]馮瑜.產業結構調整與稅收增長分析[J].稅務研究,2011,(7):84-86.
[4]韓秀蘭,王久瑾.地方稅收、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基于對數平均D氏指數方法的分解分析[J].稅務研究,2013,(12):61-64.
[5]吳敬璉.中國增長模式抉擇:增訂版[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8.
[6]曹海娟.流轉稅和所得稅對產業結構影響的經驗分析[J].現代財經,2012,(3):35-43.
[7]沈坤榮,余紅艷.稅制安排對產業結構的影響[J].經濟縱橫,2014,(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