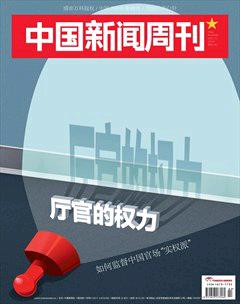公共討論是“民主的作坊”
徐賁
許多人私下或與朋友間談話(可以稱之為“社交談話”)時,能說會道、談笑風生,但在公共討論的場合發言或表達意見(“公共討論”)時,卻是笨拙拘謹,甚至不知所措,這是怎么一回事呢?人們也許會以為,這是“緊張”的緣故。那么,為什么會緊張呢?原因之一是,這兩種談話的群體環境是不同的。一個是在熟悉者或朋友之間,另一個是在比較陌生者或陌生者之間,而越是在陌生者之間的交談就越是需要知道和遵守談話的規則。
人類需要用交談來形成和維持相互間的群體感,但是,社交交談和公共討論所涉及的人群范圍是不同的。社交交談的范圍既不像家人間那么親密隨便,也不像陌生人(公眾)之間那么需要規范,通常發生在飯局、宴會、沙龍、俱樂部或學術或讀書討論會。
公眾交談或討論的人群范圍要大得多,參與者往往互相不認識,也從未謀面,因此主要是一種“陌生人”之間的交談。熟人交談與陌生人交談的目的會有重要的區別。熟人之間的社交交談主要是為了愉悅和快樂互動,而非熟人的公眾交談則為了公共目的。社交交談的目的是融洽互動,為談而談、以談為樂,有沒有結論并不重要,也不一定包含具體主張、明確觀點、充分理由、邏輯推導。但是,公眾交談的目的則不是為了獲得談話的交往樂趣,而是發表對公共問題的看法,尤其是新聞辯論或時事討論,被稱為“民主的作坊”,因此特別需要重視主張、說理、推導、邏輯等重要環節。
傳媒學家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 Schudson)稱社交交談為“審美模式”,稱公眾交談為“解決問題模式”。他概括道, “它們都強調對話伙伴的平等。在交談中,平等、禮貌和公平占支配地位。但是要進入這兩種模式的交談,門檻卻各不相同”。社交模式強調情緒教養,對話伙伴講究精妙技巧,談話才會新鮮活潑。相反,解決問題模式注重論辯方式,陳述對時務或公共問題的觀點,明了對方的觀點,并且作出合理應答。
公共說理是民主善治和公民社會所不可缺少的,正如美國政治理論家和憲法學家史蒂芬·霍爾姆斯(Stephen Holmes)在《熱情與自制》(Passions and Constraint)一書中所說,倘若民主是通過討論而實現的治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通過在法律上平等的公民之間進行自由的公共討論而實現的治理”,那么公共說理便一定是民主最核心的部分。
但熟與非熟的交談經常只是一些程度的差別。例如,學生們在課堂里討論問題,可能熟悉也可能并不相熟,可能不渴求結論,也不推導至上,但仍然會對公共問題發表看法,并有所爭論。這個時候,社交交談的個人教養與公眾交談的規范也就會融合到一起。又例如,網絡媒介也改變了傳統的社交交談與公眾交談的區分,不受“外人”打攪或質疑的個人獨語或少數人的快樂互動即使仍然可能,也由于處在公共交談的大環境里而變得更加困難了。網絡新聞組(Newsgroups,通常是一個討論組)和博客隨時都可能對一個人發表的意見提出不同的看法。電子郵件、微博、短信都可以給人面對面交談的感覺,各種鏈接也讓人有置身于多聲、多角度交談網中的感覺。這種不可預測、不可控制的異見或對立面的存在可能使得一些 “自媒體”參與者顧及公共說理的某些規范。
舒德森指出,在民主社會里,我們可以區分兩種不同的公共對話。第一種是“同質對話”,這時候,人們主要與價值觀一致的他人交流,可以放心地相互驗證觀點, “知道自己與對方的基本原則上一致的……會安然無恙”。
第二種是“真正的公眾對話”,這是與價值觀迥異的其他公民談話,這時候,對話者對不一定友善的意見沖突必須有思想準備,也必須具備較高的說理能力,更重要的是,“應該以公共論證的精神進行參與,不是簡單地堅持自己的立場,而是考慮關注他人的合理主張”。
真正的公眾對話確立了公共討論的說服標準,這種標準也會對社會里的私人交談,包括家人或朋友間談話方式有好的影響。例如,父母對孩子提出某種要求或表達某種看法,孩子問“為什么”。這時,父母要提出理由,而不能回答:“因為是我說的”。在這種交談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孩子,將來也就比較容易成為善于與他人交談和對話的合格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