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拉美關系:是處困難期,還是最佳期?
江時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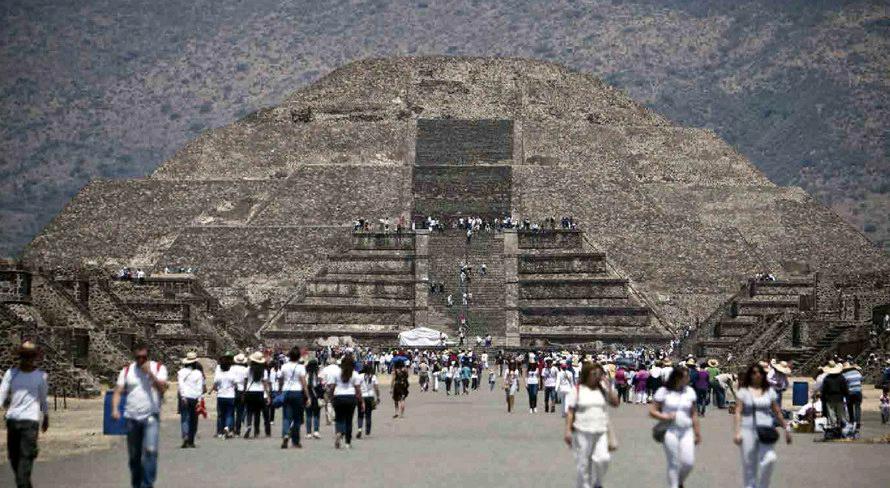
美國學者陳懋修認為,中國與拉美國家的關系正在從“比較輕松、比較容易的一段時期”進入“困難”時期。他之所以稱前一段時期為“輕松”、“容易”,是因為中拉貿易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而目前“中國和拉美的經濟及雙邊關系都面臨著不少嚴峻的挑戰”。因此,中拉關系已開始進入一個“困難”的時期。[1]無獨有偶,美國學者戴維·馬拉斯也認為,“在當前宏觀經濟背景下,中拉關系正在步入一個困難時期……過去一直說中拉合作是‘贏—贏模式,如今有可能變為‘贏—輸模式”。[2]
上述兩位美國學者的觀點是否正確?中拉關系的現狀如何?如何正確判斷當前及未來中拉關系的走向?如果中拉關系真的進入了“困難”時期,其原因何在?毫無疑問,探討這些問題的答案,對于我們正確把握中拉關系的發展前景以及如何進一步提升這一關系,是大有裨益的。
如何判斷雙邊關系的親疏遠近
如何衡量和判斷雙邊關系的“難”、“易”或好壞,絕非易事。有人曾試圖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來達到這一目的。例如,為了判斷歐盟成員國與中國雙邊關系的密切程度,復旦大學陳志敏教授等選取了七個指標,其中經濟關系指標三個(對華貿易、對華投資和金融關系),政治關系指標四個(雙邊關系定位、外交互動、軍事交流和歐盟國家的達賴政策)。他們給予每一個指標一定量的分值。例如,歐方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來訪,一次記3分,外交部部長來訪,一次記1分。中國領導人或外交部部長出訪,得同樣的分值。薩科齊總統曾會見達賴,須扣除5分。經貿關系可以采用同樣的方法。例如,2011年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的對華貿易僅占其國際貿易總額的1.2%;而德國的比重高達4.6%。因此,德國的分值高于立陶宛的分值,德國與中國的關系比立陶宛與中國的關系更好。
該論文認為,七個指標的分值大小與歐盟成員國與中國雙邊關系的好壞或密切程度成正比。中國與德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政治經濟水平都比較高,與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的政治關系水平高。
這一分析方法是否科學另當別論。然而,應該指出的是,在當代國際關系中,影響兩國關系的因素不勝枚舉。在一定的條件下,貌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能反映雙邊關系的親疏遠近。換言之,僅僅用七個經濟和政治因素來判斷雙邊關系的好壞,未必經得起推敲。例如,在多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愿意把大熊貓租借給他國,或許比接待一位總統、總理或部長來訪更能說明兩國關系的融洽程度,更能推動雙邊關系的發展。又如,加入亞投行(AIIB)或許比進口一定量的中國產品更能說明兩國關系的親密度。而一般的定量分析是很難把大熊貓或AIIB等可能會影響雙邊關系的因素都考慮進去的。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經貿關系是雙邊關系的基礎。但在現實中,雙邊關系有時還呈現出“政冷經熱”或“經冷政熱”等奇怪的特點。這些特點再次說明,判斷雙邊關系的親疏近遠是多么艱難。
中拉關系的現狀
雖然難以用定量分析方法來界定中拉關系或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關系,但是,以下幾點充分說明,中拉關系并未進入“困難”時期。相反,目前的中拉關系處于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以來的最佳時期。
第一,高層互訪為中拉關系注入了強大的政治動力。在過去的十多年,推動中拉關系快速發展的動力之一就是高層互訪頻繁。2004年11月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拉美后,時任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2005年初也訪問拉美。兩次訪問間隔時間僅為兩個月左右。2008年11月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拉美后,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2009年初也訪問拉美,兩次訪問間隔時間同樣只有兩個月左右。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5月31日至6月6日訪問拉美,之前半個月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2013年5月9—16日剛剛訪問過拉美,一個國家的主席和副主席在兩個月內、甚至不足一個月的時間內先后訪問拉美,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這一切充分說明,中國非常重視與拉美發展關系。
拉美國家的領導人也經常訪問中國。通過頻繁的互訪,雙方的最高領導人可探討如何進一步提升雙邊關系,也能就重大國際問題交流看法。近幾年,中拉高層互訪的勢頭并沒有減弱。在中共十八大以來短短的三年多時間內,習近平主席已兩次訪問拉美,李克強總理也在2015年5月訪問拉美。因此,中拉關系并未進入所謂“困難”時期。
第二,經貿關系日益多元化。古往今來,貿易是經貿關系的主體。隨著雙邊貿易的發展,國與國或與地區的經貿關系會進一步多元化。在這一過程中,貿易的重要性會下降,投資的重要性會不斷凸顯。這一變化不等于兩國關系進入了困難時期。中國與拉美、非洲和歐洲及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系都經歷了這一過程。
誠然,近幾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因產業結構變化和增長方式調整而有所下降。受此變化和調整的影響,中國對海外資源的需求在減少,中國從拉美進口的初級產品在數量上并未繼續保持十年前的那種“井噴式”的增長。但這并不意味著中拉經貿關系停滯不前了。相反,隨著中國對拉美投資的快速增加,中拉經貿關系日益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這一變化既符合國際經濟關系的性質,也表明中拉經貿關系在“更上一層樓”。
第三,合作領域不斷拓展。隨著經貿關系的發展,其他領域的交往也會不斷擴大。這是當代國際關系的一個規律。中拉關系亦非例外。今天,經貿關系依然是中拉關系的主體,但政治關系、人文交流以及多邊場合的合作也在不斷發展。尤其是2008年中國發表對拉美政策文件后,中拉關系越來越呈現出全方位、多領域、“全面開花”的特點。從政黨到民間,從議會到軍隊,從文化到體育,從科技到衛生,從媒體到智庫,都能感受到中拉關系的熱絡氣氛。
綜上所述,所謂中拉關系進入“困難時期”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如何進一步提升中拉關系
否認中拉關系進入“困難”時期,并不意味著這一關系已進入盡善盡美的境界。毋庸置疑,中拉關系確實面臨著一些問題。中拉關系面臨的突出問題是什么?有人認為,拉美國家經常對中國出口產品實施反傾銷。因此,中拉關系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貿易爭端。
拉美國家確實經常用反傾銷的方式來保護其國內市場和企業。但是,與龐大的雙邊貿易額相比,受拉美的反傾銷影響的中國出口產品在雙邊貿易額中的比重極小。而且,隨著經貿關系的發展,出現一些貿易爭端難以避免。因此,貿易爭端不是中拉關系的主要問題。
中拉關系的最大問題是雙方相互了解不深不透。這一問題的危害性之一就是“中國威脅論”以及恐懼中國的心態在拉美尚有“市場”,甚至在不斷蔓延。例如,一些拉美的媒體經常將中國視為發達國家,并稱昨天的美國與拉美的關系就是明天的中國與拉美的關系。又如,“中國帝國主義”、“中國新殖民主義”等污蔑性詞匯經常出現在拉美的某些媒體上。在一些反對中國企業的游行示威中,還出現了不雅的反華標語和口號。
中國與拉美不僅遠隔重洋,相距遙遠,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和語言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此外,美國媒體對中國的不實報道在拉美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改變一些拉美人對中國的不正確的認知,絕非一蹴而就的。
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中國威脅論”和恐懼中國的心態,除了加大對拉美等宣傳力度以外,還應該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要鼓勵中國企業在拉美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嚴格遵從東道國法律,妥善處理投資項目與其所在地政府和民眾的關系;二是要吸引更多的拉美游客來華旅游,使其對中國的國家形象獲得一個眼見為實的認知;三是要鼓勵更多的拉美青年來華留學,為中拉關系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四是中國駐拉美國家的使館要多多舉辦一些宣傳和介紹中國的活動。
對中拉關系中若干問題的認識
為了進一步提升中拉關系,除了加強相互了解以外,還應正確認識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中拉經貿關系是否應該“超越互補性”?巴西是最大的拉美國家,因此中國與巴西的關系對整個中拉關系的影響是巨大的。2014年,中巴貿易額占中拉貿易總額的比重超過30%。
眾所周知,中國在制造業擁有顯而易見的比較優勢,巴西的比較優勢是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這意味著,中巴兩國在經貿領域的互補性是不容低估的。但巴西總統羅塞芙卻在2011年4月訪華時說,中國與巴西應該“超越互補性”,以便“使雙邊關系向充滿活力的、多元化的和均衡的方向發展”。[3]
確實,中巴經貿關系或中拉經貿關系應該不斷實現多元化。但是,經貿關系的基礎是各國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揚長避短,互通有無。超越這一互補性,雙邊經貿關系的活力就會減弱。
巨大的中國市場為巴西和其他拉美國家擴大出口提供了機遇。但中國市場上的競爭是很激烈的。且不論中巴貿易和中拉貿易是否應該“超越互補性”,要想在中國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包括巴西在內的所有拉美國家都應該進一步強化其競爭力。否則,“超越互補性”僅僅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第二,“一帶一路”倡議是否冷落了拉美?根據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在2015年3月28日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一帶一路”倡議未包括拉美。無怪乎中國和拉美的一些學者頗為失望。
其實,這一失望是沒有必要的。首先,“一帶一路”堅持開放合作,因此,“一帶一路”涉及的國家并不限于古代絲綢之路的范圍,各國和國際、地區組織均可參與。其次,“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是“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雖然《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未提及拉美,但中拉關系的發展進程實際上早已囊括“五通”。
由于中國與拉美隔海相望,就設施聯通而言,如在太平洋上鋪設鐵軌或興建道路是難度較大的。就此而言,中國學者和拉美學者關心的應該是如何實現“五通”,而非“一帶一路”是否應該包括拉美這一偽命題。
第三,如何應對拉美的“國家風險”(country?risks)?“國家風險”是一國政治、經濟、外交、社會等領域的不安全因素。在一定意義上,“國家風險”實際上就是投資環境。投資環境又有所謂“硬環境”和“軟環境”之分。“硬環境”是人的主觀愿望不可改變的,如地理位置、氣候、自然條件和資源稟賦等等。“軟環境”則是人能通過其自身的意志設法加以改變的,?如經濟政策、發展水平、政治民主、社會治安、法律體系和基礎設施等等。因此,在預測和分析拉美的“國家風險”時,不妨從投資環境,尤其是“軟環境”入手。
拉美國家的“國家風險”有很多:既有政局不穩定,也有政府的低誠信度;既有經濟危機、金融危機、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風險,也有匯率不穩定和通貨膨脹壓力;既有司空見慣的小偷小摸,也有毛骨悚然的綁架和暗殺;既有無處不在的腐敗,也有政府的低效率;既有戰斗力極強的工會組織,也有繁瑣復雜的稅法、勞工法和其他法律。這意味著,中國企業在開拓拉美市場時,必須重視該地區的“國家風險”。
“國家風險”的最佳應對之道無疑是準確地預測風險能否發生或何時發生。有些風險是可預測的。例如,左翼政治家當政后,必然會高舉民族主義大旗,對外資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有時甚至會實施國有化;如果一個國家長期奉行“寅吃卯糧”的赤字財政政策,債務危機遲早會爆發;在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社會凝聚力極為弱化或中產階級微不足道的國家,日積月累的社會矛盾必然會損害社會治安,甚至可能會演化為政府難以遏制的大規模的社會動蕩。
但是,有些“國家風險”是難以預料的。中國企業必須強化規避風險的意識,千萬不要以為背靠強盛的祖國就能使企業在拉美高枕無憂。強盛的祖國能在“國家風險”演變為危機后通過外交手段或經濟實力將危機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但并不能遏制拉美“國家風險”的發生。因此,中國企業在進入拉美市場之前必須時刻提防各種各樣的風險,真正做到有備無患。有些“國家風險”是東道國不遵守商業規則或違反商業信用等不良行為導致的。對此,企業必須積極訴諸法律手段,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
第四,如何認識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拉共體)在推動中拉關系中的作用?拉共體成立于2011年12月。其宗旨是:在加強團結和兼顧多樣性基礎上,深化地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一體化建設,實現本地區可持續發展;繼續推動現有區域和次區域一體化組織在經貿、生產、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對話與合作,制定地區發展的統一議程;在涉拉共體重大問題上進行協調并表明成員國共同立場,對外發出“拉美聲音”。[4]
2015年1月8—9日,中國—拉共體首屆部長級會議(又名中拉論壇)在北京舉行。毫無疑問,這一論壇的建立為中拉雙方開展廣泛領域的合作搭建了重要平臺,也為雙方加強政策對話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雙方表示,今后將以這一論壇為對話與合作的新平臺、新起點、新機遇,進一步深化中拉全面合作伙伴關系。
但是,拉共體與歐盟的作用和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尤其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后,歐盟已成為世界上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集團,實現了商品、人員、資本和服務的自由流通。除統一市場、歐元和共同貿易政策以外,歐盟成員國還在外交、安全和司法等領域實現了較高程度的一體化。目前,歐盟正在向政治聯盟、銀行業聯盟、財政聯盟、能源聯盟和數字聯盟的大方向闊步前進。面對這樣一個國家集團,中國有必要與其保持密切的關系。換言之,中國既要與歐盟成員國發展關系,也要與歐盟發展關系,兩者缺一不可。
相比之下,拉共體正處于發展階段,還未能從其成員國中獲得從屬于國家主權的任何職能,一體化的深度有待加強。因此,中國在與拉美國家發展關系時,除了依托中拉論壇這一平臺,也應重視雙邊層面的關系。
第五,并非所有拉美國家都適合與中國進行國際產能合作。作為中拉經貿關系多元化的產物,國際產能合作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必須注意到,中拉產能合作面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掣肘:第一,在拉美的33個國家中,半數以上的國家市場規模小。因此,現代化工業的大規模批量生產極易造成市場飽和。第二,雖然一些拉美國家的制造業落后,但其推動工業化建設的愿望和決心不強,因為它們擔心制造業會破壞其生態環境。第三,地理優勢及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使拉美國家能很容易地從美國進口任何工業制成品,根本沒有必要興建自己的工廠,因此與中國進行產能合作的動力不強。否則,美國制造業企業早就在拉美各國“安營扎寨”了。
所以,在與拉美國家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到東道國的國情,考慮雙方的需求,這樣雙方才可以實現互利共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拉美學會副會長,中國新興經濟體研究會副會長)
(責任編輯:魏銀萍)
—————————
[1]?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50828/141323107286.shtml.
[2]?http://m.caijing.com.cn/api/show??contentid=3961727.
[3]?Ana?Fernandez,?“Brazils?Rousseff?wants?new?phase?in?China?ties”,?April?12,?2011.
https://au.finance.yahoo.com/news/Brazil-Rousseff-wants-new-afp-2838520022.html.
[4]?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mhjlbgjgtt_683624/jbqk_68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