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代報案(中篇小說)
扎西才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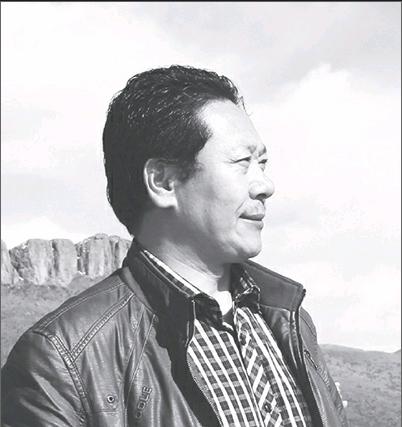
一
桑多鄉(xiāng)的后鄉(xiāng)長正在辦公室里發(fā)呆,聽到幾下膽怯的敲門聲。他猛地站起來,不小心撞翻了身后的背靠椅。這時,敲門聲停止了。那人似乎是在靜聽門內(nèi)的動靜。也許聽到了后鄉(xiāng)長在慌亂中發(fā)出的聲響,那人又敲起門,這次的聲音是堅定的,不慌不忙的。
后鄉(xiāng)長最近動不動就發(fā)呆。原因嘛,既和無窮無盡的工作有關(guān),又和媳婦的嘮嘮叨叨有關(guān)。如今鄉(xiāng)上的工作都圍著老百姓的生計轉(zhuǎn),亂如細麻,理不清,也不好搞,更搞不完。媳婦是個文盲,不懂也不關(guān)心國家政策,肚量又小,盡盯著蠅頭小利,又熟知自家男人的脾性,鄉(xiāng)長這頂官帽的光環(huán)在她眼里早就暗淡了許多,因此不是很支持男人的工作。這些破事,使年過四旬的后鄉(xiāng)長越來越難以招架,走神,發(fā)呆,就是常有的事了。
因此,當敲門聲打斷了那無奈的走神時光時,后鄉(xiāng)長很懊惱。他陰著臉,壓著嗓子說:“進來!”
進來的是二十多歲的矮個青年,猴子臉,一頭卷發(fā)臟兮兮的,一身寬大的迷彩服,也是臟兮兮的。
“干啥?”后鄉(xiāng)長掩飾不住對矮個青年的厭惡。矮個青年用小小的眼睛盯住后鄉(xiāng)長,含糊地說:“報案。”“甭挨?”后鄉(xiāng)長生氣了,“誰挨著你了?誰愿意挨著你?!”矮個青年的聲音大起來:“不是甭挨,是報案!”“報案”兩個字,把后鄉(xiāng)長驚得跳了起來:“哪里發(fā)生案子了?”矮個青年說:“還沒發(fā)生呢!”后鄉(xiāng)長又惱了:“沒發(fā)生你亂說個啥?”矮個青年說:“快要發(fā)生了!”“那你說說看。”后鄉(xiāng)長從辦公桌抽屜里取出黑皮筆記本,“你說,我記下來。”矮個青年猶豫了一下:“能不能叫我坐下了說?”
后鄉(xiāng)長這才發(fā)現(xiàn),自己的行為確實不是鄉(xiāng)長對待群眾才有的行為,忙指著斜對面的三人沙發(fā)說:“好,坐下說,坐下說。”
矮個青年落在沙發(fā)上,只擔(dān)了半片屁股,皺著眉頭對后鄉(xiāng)長說:“我想來想去,覺得這個案不報不成。”
后鄉(xiāng)長打斷了他的話:“你是哪個村的?叫啥名字?”矮個青年縮了縮脖子,撓了撓頭,這才說:“我是楊莊的,名叫喇嘛代。”
楊莊后鄉(xiāng)長知道,這是桑多鄉(xiāng)的一個自然村,大約有二三十戶人家,村民多半是漢族,少部分是藏族。因為民風(fēng)民俗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村民之間動不動就發(fā)生摩擦,年年都有民事糾紛。想到這一些,后鄉(xiāng)長就明白,說是案子,其實肯定不是案子,僅僅是村民之間的小沖突,不是什么要事,但在鄉(xiāng)政府的工作范疇內(nèi),管還是得管的。
后鄉(xiāng)長:“那好,喇嘛代,你說說,你要報啥案子。”
喇嘛代:“我想殺人!”
后鄉(xiāng)長吃了一驚,隨即就釋然了。在桑多鄉(xiāng),不知有多少群眾在鄉(xiāng)干部跟前說過類似的話了。這是句氣話,說這話的目的,僅僅是發(fā)泄心中的憤怒和痛苦,卻很少有真殺人的。
后鄉(xiāng)長饒有興趣地問:“你想殺誰?”
喇嘛代看了看后鄉(xiāng)長,又將眼光移到對面的墻上,盯著墻上的一個黑斑,咬著牙說:“我想殺了陰陽李根旺!”
一提李根旺,后鄉(xiāng)長就笑了。桑多鄉(xiāng)管著二十來個自然村,每個村里都有一些所謂的厲害角色,比如算命的能人,堪輿的陰陽,制作佛像的畫家,教書的先生,勸和的說客,還有打架的高手……正是這些厲害角色,成為鄉(xiāng)干部最頭疼卻又最離不開的人。李根旺是繼承了父親的衣缽,當上鄉(xiāng)村陰陽的。據(jù)說在看風(fēng)水方面,還真有兩刷子,這幾年生意比較多,慢慢地,竟成了一個人物。
后鄉(xiāng)長:“說說,你為啥想殺他?”
喇嘛代:“他家屋頂?shù)奶焖偸橇髟谖壹以鹤永铩N医o他說了好多次,他就是不聽。”
后鄉(xiāng)長一聽這理由,想笑,想起場合不對,就硬生生地正了神情。
干了多年鄉(xiāng)下的工作,后鄉(xiāng)長處理過太多這樣的事。他知道,像喇嘛代這樣因事煩心不講方法的人,在村子里,一抓就是一把。他們一旦有事,總喜歡找村長,村長解決不了,就找鄉(xiāng)長。找的過程,就是訴苦的過程。訴說完了,也就發(fā)泄完了,問題也就解決了。無論村長還是鄉(xiāng)長,能替他們解決問題最好,解決不了,最好長兩只善于傾聽的耳朵,也就行了。
所以,后鄉(xiāng)長立刻豎起耳朵:“說說,還有啥事?”
喇嘛代奇怪地問:“這事還不大嗎?你不知道,一下雨,滿院子都是水,走都走不成!”
后鄉(xiāng)長:“一下雨,誰家院子里沒有水?”他佯裝生氣,“我以為是啥事情逼你動手動刀子,原來就這破事啊!”
喇嘛代一看鄉(xiāng)長生氣了,忙解釋道:“你不知道他那個球樣子,給他說事情,他愛理不理的,叫人生氣得很!”停了停,又補充道:“這口氣咽不下,我真的想殺他呢!”
后鄉(xiāng)長看了看喇嘛代的臉色。那臉色有些黑,有些扭曲,似乎臉的主人確實處在憤怒中。于是安慰說:“你就甭生氣了。你說的事情我知道了,抽空我去去陰陽家,勸勸他。”
喇嘛代一聽這話,臉色頓時活泛了,站起身,過來要拉后鄉(xiāng)長的手。
后鄉(xiāng)長看到對方伸出的那雙手黑黝黝的,忙把自己的手背到身后:“那就這樣吧,我這還有事呢!”
喇嘛代尷尬地縮回了雙手:“這事,就拜托鄉(xiāng)長了,你一定要操心啊!”
后鄉(xiāng)長:“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見喇嘛代要離開,又叮囑道:“你可不能胡想,也不能胡做啊!”
喇嘛代諾諾連聲,退了出去。
二
三天后的上午,后鄉(xiāng)長苦著臉,坐在辦公室里等來自桑多村的消息。
這次他又發(fā)了很長時間的呆,因為桑多村的一個三格毛生了第三胎。
后鄉(xiāng)長聽了分管桑多村的干事劉二毛的匯報后,命劉二毛和另外兩個干事去辦因超生而罰款的事。
劉二毛把桑多鄉(xiāng)轄區(qū)內(nèi)的藏族,都叫三格毛。當然這也不是劉二毛自個發(fā)明的叫法。桑多村的藏族,據(jù)說祖先來自西藏,那已經(jīng)是元代的事情了。幾百年后,變化越來越大,穿著打扮隨了當?shù)販貪竦臍夂颍辉俅┖裰氐钠ひ\了。男人喜穿漢服,女人則把頭發(fā)辮成三根粗黑油亮的辮子,發(fā)辮上佩掛圓形的銀制品。身著藍色、紅色或綠色的大襟長衫,兩邊開叉,外穿色彩對比強烈的短夾,短夾鑲了錦邊,煞是好看。腰里,則系一條錦繡寬腰帶,勒出曼妙的腰身。下身大多穿紅色褲子,腳穿繡花鞋,那花艷麗,也開在了觀賞者的心頭。語言,也隨了漢族,一般場合,都說漢話。正是因為當?shù)夭刈迮擞兄洲p子,所以叫三格毛。叫著叫著,叫順了,沒有啥抬高或貶低的想法,只有一個意思:藏族婦女!
后鄉(xiāng)長也是藏族,他的母親和姊妹,都是三格毛。所以當劉二毛給他期期艾艾地匯報情況時,他一下子就懵了:若是漢族婦女超生,他就出面,拿政策辦事,但這藏族婦女超生,作為同一民族的人,自己確實不好親自出面,所以只好派三個干事去。
等了半小時,那電話終于來了:對方不配合,要殺人呢!
劉二毛說,要殺人的是那個三格毛的丈夫,名叫菩薩保。劉二毛他們?nèi)チ巳衩遥B上院就沒去,只站在下院里,對三格毛的公公——一個滿臉皺紋的黃臉老人,念了一段鄉(xiāng)上開的罰款通知。還沒念完,一個紅臉大漢就從堂屋里沖出來,手里攥著一把豁了牙的板斧,一個勁地嚷:“還讓不讓活了?我要劈了你們這些土匪!”大家認得是菩薩保,頓時嚇得呆住了,失了逃跑的本能。幸虧那黃臉老人攔住了那兇神惡煞的兒子,大家這才從下院里撤出來,站到巷道口,進也進不得,回也回不得。沒辦法,這才給后鄉(xiāng)長打了求救電話。
后鄉(xiāng)長愣住了,覺得這名字太熟,忽然想起三天前來報案的喇嘛代,禁不住自言自語:“這些名字與菩薩、喇嘛有關(guān)的,為啥這么難纏,動不動就想殺人!”他知道劉二毛他們一去,事情肯定不會那么順利,不成想竟這么不順利,對方的反抗也太強烈了吧!正手握話筒不知如何處理的時候,聽到了一陣敲門聲。他不想讓敲門聲打斷電話,就對著話筒喊:“那你們先回來,我給武書記匯報匯報再說。”
剛扣下話筒,門就被人推開,進來一個瘦高個男人,年紀在五十左右,戴一副橢圓形的茶色石頭鏡。那人用脊背關(guān)了門后,就畢恭畢敬地朝后鄉(xiāng)長鞠了一躬:“鄉(xiāng)長大人,您在啊!您不認識我了?”
后鄉(xiāng)長看了對方半天,猛然想起對方,忙過去握住對方的手:“啊呀,李老先生,我怎么能不認識呢?我正想到你家里,拜訪拜訪你呢!”
來人正是喇嘛代想殺的陰陽李根旺。
李根旺從口袋里摸出一盒煙,抖抖擻擻地抽出一根,敬給了后鄉(xiāng)長。后鄉(xiāng)長一看,是一盒八塊錢的紫蘭州,不好拒絕,就勉強接了。李根旺急忙拿出火柴,嗤地一聲劃著,將火苗湊近后鄉(xiāng)長。后鄉(xiāng)長偏過頭點了煙,長吸了一口,吐出一股濃煙,感覺像吐出了剛才接電話時的不快,這才對李根旺說:“坐,坐。”
李根旺小心翼翼地坐下來,往后靠實了脊背,有點正襟危坐的樣子。后鄉(xiāng)長覺得坐在沙發(fā)上的李根旺,就像一捆長而干硬的木頭。
李根旺:“鄉(xiāng)長大人,我找您來,是有件事的。”
后鄉(xiāng)長:“你直說無妨。”
李根旺:“我到這來,是想報個案。”
后鄉(xiāng)長心里又是一驚:“怎么又是報案的?”問道:“你想報什么案?”
李根旺:“我們村的喇嘛代你知道吧?”見后鄉(xiāng)長點了點頭,就接著說,“那尕年輕人這兩天在村里到處放話,說要殺了我呢!”
后鄉(xiāng)長:“這事我知道。他到我這也來過,一直嘟囔著要殺你呢!”
李根旺:“他來過了?那您怎么答復(fù)的?”
后鄉(xiāng)長:“他說的是氣話嘛,我只好好好勸慰他了。”
“那他什么態(tài)度?”
“還有什么態(tài)度?聽了我的勸,走了唄!”
李根旺長吁了一口氣:“那就好,那就好,有您出馬,就沒啥麻煩了!”
后鄉(xiāng)長:“話也不能這么肯定。我聽說問題都在你那呢,對吧?”
李根旺連連擺手:“我的鄉(xiāng)長大人,話不能這么說。惡人先告狀,就占了三分便宜。問題其
實還在他身上。”后鄉(xiāng)長:“你家的天水都淌在人家院子里,還說人家有問題,有啥問題呢?”李根旺:“不就是幾滴天水嘛,值得那二桿子這么大動干戈嗎?”
后鄉(xiāng)長笑了。二桿子是桑多鄉(xiāng)一帶的土話,專指不務(wù)正業(yè)的尕流氓。李根旺對喇嘛代這么評價,也就表明了自個的態(tài)度:他對喇嘛代很不感冒!
后鄉(xiāng)長:“我看這事不是幾滴天水的問題,是思想認識的問題,是如何處理鄰里關(guān)系的問題。”
李根旺忙:“對對對,您說得對。”
后鄉(xiāng)長:“你承認我說得對,就應(yīng)該把你屋頂天水的通道給改一改。改到別處,問題就解決了。”
李根旺為難地說:“改不成啊,我的鄉(xiāng)長大人。一改,就破了我家的風(fēng)水了!”后鄉(xiāng)長惱了,話也沖起來:“風(fēng)水個屁!你講風(fēng)水,人家就不講風(fēng)水?”李根旺忙站起來解釋:“我看了,那水到他家院子,聚財呢!”后鄉(xiāng)長揶揄李根旺:“你的水淌到他家,你
不就折財了?”李根旺:“風(fēng)水上沒這種說法。”后鄉(xiāng)長想繼續(xù)批駁對方,桌上的電話又響起來。一接,是劉二毛。劉二毛說:“后鄉(xiāng)長,我們按您的吩咐,離開了桑多村,那個菩薩保一直追到路口,罵罵咧咧的,還揚言要到鄉(xiāng)政府里來鬧呢。我們要不要給派出所說一說?”
后鄉(xiāng)長本來就被李根旺惹動了火氣,這時那火已在肚子里燒了起來:“這是你該管的事嗎?你們都回來!”說罷哐地扣了電話,驚得李根旺跌坐在沙發(fā)上。
李根旺討好地問:“又發(fā)生啥事呢?您可要保重身體啊!”后鄉(xiāng)長沒好氣地說:“你先回去。我給你剛才說的,你可要好好想想。”李根旺:“你不想整治整治那小子?”后鄉(xiāng)長:“整治誰?”
李根旺:“就喇嘛代那二桿子!”
后鄉(xiāng)長:“人家告你,是有理的,我怎么整治人家?我只能勸你,勸他,不要為屁大的事鬧得雞飛狗跳的。”
李根旺很疑惑:“那我這就走了?”
后鄉(xiāng)長:“走吧,走吧,等我哪天有空,把你們兩家叫到一起,好好調(diào)解調(diào)解。”
三
說是要好好調(diào)解調(diào)解,后鄉(xiāng)長卻沒有時間好好調(diào)解。
他的時間哪去了?用在調(diào)解菩薩保超生的事情上去了。
劉二毛去給菩薩保罰款,結(jié)果遭到激烈反抗。反抗的結(jié)果是:后鄉(xiāng)長只好自己出馬了!
后鄉(xiāng)長帶人去了桑多村,沒去找菩薩保,徑直去了村長家。村長四十來歲,精壯,沉穩(wěn),煮了一塊臘肉熬了一壺大茶招待后鄉(xiāng)長一行。
后鄉(xiāng)長卻沒心思吃,只問菩薩保家的情況。
村長說:“菩薩保是個好人,就是娶錯了婆娘。那婆娘也是好人,就是嫁錯了男人。”
后鄉(xiāng)長覺得奇怪:“你這話是啥意思?”
村長介紹說,兩個好人走在一起,本來就是對的事,錯的是兩人是親戚,是姑舅關(guān)系。這不,結(jié)婚之后,兩口子挺恩愛的,不到兩三年時間,就接連生下了兩個娃娃,一個兒子,一個女子。不過,兒子是癡呆,女子是啞巴。這下,一家人都急了,先是找大夫。大夫說,只有兩條路,一條,兩口子把婚離了,各自重建各自的家。另一條,再甭生了,膩著過日子算了,再生也會生個嘴斜眼歪的。菩薩保一聽,不高興了,把那個大夫揍了一頓,又去找活佛。活佛算了一下,說大夫說得對,你們的后人沒有清透的。菩薩保不信,找了個穿街走巷的郎中。那郎中說有辦法,拿出了個土方子,叫菩薩保的婆娘吃了幾次。后來就懷上了。這不,就生了。還沒出月,你們就罰款來了。
后鄉(xiāng)長:“菩薩保家里經(jīng)濟情況好不好?”
村長:“好個啥?人家都出門打工去了,就他們兩口子窩在家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你想想,兒子癡呆,丫頭啞巴,都離不開人的照顧。而今只有打工才能掙著錢,靠務(wù)弄那幾畝地,不頂事的。我給他家報了一個低保,菩薩保還鬧著再要一個指標呢!”
后鄉(xiāng)長:“那這事就不好辦了。”想了想,又問村長:“你看這事咋辦好?”
村長:“我想,罰款,還是要罰的。不罰的話,你們的工作無法做。我看不如這樣,罰款數(shù)額,按鄉(xiāng)上定的最低限度走,分三四次收,兩年收一次,三年收一次,都成。這樣,菩薩保也能接受,收款時也容易些。你看行不行?”
后鄉(xiāng)長:“辦法倒是好辦法,就是保不定那家伙還要生個五胎六胎呢,前面的地都沒犁完,后面的地可就荒了。”
村長:“我估計這第三個一生,他就再不生了。你們不是叫我們相信科學(xué)嗎?我還是相信的。”
后鄉(xiāng)長明白了村長的意思,告辭出來,去了菩薩保家。
菩薩保正在院子里磨那把板斧。見后鄉(xiāng)長幾人進來,眼皮也不抬,手上加了勁,磨得更給力了。還是那個黃臉老漢出來,迎接后鄉(xiāng)長一行到了上院。
后鄉(xiāng)長擺擺手:“你兒媳婦剛生了,我們就不進屋里了,進了,會沖的。我們就在院子里坐一會吧。”
黃臉老漢趕緊搬過來一張破舊的方桌,又配了兩條瘦長的板凳。等后鄉(xiāng)長他們坐定,又要去倒茶。
后鄉(xiāng)長:“不麻煩了,不麻煩了。我們來,是商量事情的。”
菩薩保一聽商量這個詞,就停了磨刀的動作,但還是不看后鄉(xiāng)長他們,只看那把板斧。
后鄉(xiāng)長:“你們家的情況,我們都了解了。我們知道,你家的情況,和別家不一樣,有很大的難處。”
一聽后鄉(xiāng)長這話,菩薩保才扭頭看來的幾個人。當目光落定到后鄉(xiāng)長身上時,后鄉(xiāng)長偏不看他。
黃臉老漢:“就是,就是,難處大著呢,都不敢給你們說。”
后鄉(xiāng)長:“有啥不好說的?你們有困難,就應(yīng)該對我們說的。我們這些干部,就是來給你們解決問題的。”
劉二毛掏出一個本子,拿出筆,要記后鄉(xiāng)長說的話。后鄉(xiāng)長低聲罵道:“記屁呢,收回去!”劉二毛紅著臉收回了本子。
后鄉(xiāng)長又說:“但話又說回來,國家規(guī)定,我們這里的農(nóng)民,只能生二胎。過了這個數(shù),就是超生,就是違反了國家法律,按規(guī)定,是要罰款的。”
黃臉老漢看了看后鄉(xiāng)長,又看了看他的兒子。菩薩保不看他老子,只看著后鄉(xiāng)長,卻不表態(tài)。
后鄉(xiāng)長對黃臉老漢說:“這樣吧,我先想辦法解決你們家的大問題,再給你們爭取兩個低保指標。你家先前那個低保,是你的。現(xiàn)在要爭取的這兩個,是你的孫子孫女的。阿婆的,以后再說。噯,阿婆在不在?”
黃臉老漢對著后鄉(xiāng)長他們連連鞠躬:“在呢,在呢,在伺候月婆子著呢。”
后鄉(xiāng)長忙起身扶住黃臉老漢:“老人家,你再甭鞠躬了,我們可受不起。”沉默了半會,又說:“不過,超生要罰的款,還得罰。你們家超生的原因比較特殊,這樣吧,我們就按國家規(guī)定的最低的限額來罰。”扭頭問劉二毛:“你是計劃生育專干,你最清楚,他們家這情況,最低限額是多少?”劉二毛說:“最低要一萬五。但前兩胎生了殘疾人的,再超生,最少也得罰八千。”
后鄉(xiāng)長問黃臉老漢:“那就罰八千元,你看行不行?”
黃臉老漢未搭腔,只是拿眼看菩薩保。
菩薩保擦拭著斧刃上的石泥,臉上的表情發(fā)生著輕微的變化。起先是懷疑,而后是驚喜,之后正了正神情說:“八千就八千。不過后鄉(xiāng)長,你可要說話算數(shù),兩個孩子享受低保的事,你不能給我放煙霧彈。”
后鄉(xiāng)長這才扭頭看著菩薩保:“我是鄉(xiāng)長,說過的話,就是吐出的痰,我不會又吃回去的。”
菩薩保把板斧丟在一邊:“那就好。”又給黃臉老漢說:“趕緊給鄉(xiāng)長們把茶倒上。”
黃臉老漢要進屋去拿茶杯,后鄉(xiāng)長制止道:“茶就算了。這罰款,你們是一次交清,還是分兩三次交?”
菩薩保:“我湊湊看。能湊齊的話,就一次交清算了。”
后鄉(xiāng)長:“那就這樣了。我們還有事,先走了。”又對菩薩保說:“你和我們的小劉保持聯(lián)系,錢湊齊了,就交給他。”菩薩保和劉二毛就答應(yīng)了。
告辭出來,一行人走到村口,回頭一看,菩薩保和黃臉老漢還站在門口張望著。
后鄉(xiāng)長:“狗日的事情,咋就這么多呢!”
劉二毛他們都不敢搭腔。一股旋風(fēng)過來,跟了他們老半天,又無聊地消失了。
四
后鄉(xiāng)長在桑多村處理超生事情的那會,喇嘛代又到鄉(xiāng)政府來找后鄉(xiāng)長。
后鄉(xiāng)長不在,喇嘛代只好去尋另外能管事的。恰好鄉(xiāng)黨委書記在。
這次,喇嘛代沒敲門,他忘了書記的姓,只好站在書記門口喊:“領(lǐng)導(dǎo)在嗎?領(lǐng)導(dǎo)在不在?”
書記姓武,漢族,是從軍隊上下來的,五大三粗的,不像個書記,倒像個屠夫。
武書記正開著辦公室的門,品他朋友帶來的鐵觀音,一聽有人喊,就拉開門吼道:“喊球呢喊,再甭球喊了,進來!”
人們都說,武書記面惡心善,千好萬好,就是一點不好。哪不好?說話不好。武書記有個口頭禪——球,說啥事都要帶個球。在正兒八經(jīng)的場合講話,倒沒事,因為念的是發(fā)言稿,不會念出球字。但只要在小場合做即興發(fā)言,就滿嘴帶球,聽著很不舒服。不過,時間長了,大家也就習(xí)慣了,書記講話不帶球字,倒覺得不舒服,武書記也就不是武書記了。
喇嘛代被武書記的粗聲大嗓給嚇住了,既不敢喊也不敢進。
武書記只好朝喇嘛代招手:“進來,進來,還愣啥?叫的就是你。”
喇嘛代這才進到書記辦公室里,卻豎在沙發(fā)旁,不敢坐。
因為家屬在縣上,武書記只能長住在鄉(xiāng)政府里。后鄉(xiāng)長的家離鄉(xiāng)上很近,安排辦公室時,就給了個單間。武書記的,卻是套間。里間住宿,外間辦公,會客。住著住著,辦公室就成私人的房間了。本來里間放的物什,被挪到外間,外間的東西,像長了腿,總是出現(xiàn)在里間。
喇嘛代之所以不敢坐,一來是見了大嗓門的書記,有些犯怵。二來,那沙發(fā)上正好堆著黃底紅花的被子,總不能坐在被子上吧。
武書記發(fā)現(xiàn)了喇嘛代的窘態(tài),就把被子搬到里間。出來時,已經(jīng)倒了一杯茶,擱在喇嘛代面前。
喇嘛代頓時感覺到武書記的好,鼻子有些發(fā)酸。幾天前他到后鄉(xiāng)長辦公室去報案,后鄉(xiāng)長似乎理都不想理他,就更不說倒茶的事了。這樣想著,就覺得對后鄉(xiāng)長十分的生氣了。
當然,生氣的原因,還有另一個:他已經(jīng)報案好幾天了,后鄉(xiāng)長說是要調(diào)解,就是沒有任何動靜。這不,實在等不及了,就又來了。
武書記見來人坐在沙發(fā)上走神,就問道:“你有啥事嗎?”
喇嘛代趕忙說:“就是,就是,我來報案!”
“報案?”武書記也像后鄉(xiāng)長那樣吃了一驚,但卻沒跳起來。他很納悶:報案,應(yīng)該到派出所去,跑到鄉(xiāng)上來干什么?但他沒說出自己的想法,只是感興趣地問:“哪里發(fā)生案子了?”喇嘛代:“還沒發(fā)生,快發(fā)生了!”武書記的聲音立馬高起來:“你這說球子啥話嗎?快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喇嘛代:“陰陽家的天水在我家滿院子淌著呢。給他說了,他不管。給后鄉(xiāng)長說了,后鄉(xiāng)長到現(xiàn)在還沒管。你們鄉(xiāng)上到底有管這事的人嗎?”
武書記被喇嘛代的這番話搞到了云里霧里,半天沒弄清楚。他要求喇嘛代從頭到尾說說。喇嘛代前言不搭后語地說了老半天,才使武書記明白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武書記:“球大的事情,至于你這樣三番五次往鄉(xiāng)政府跑嗎?這事你給村長一說,村長一解決不就行了?”
喇嘛代本來還指望武書記出面解決問題,一聽這話,又懵了,哭喪著臉:“村長能解決嗎?芝麻小的官,啥事也弄不來!”
武書記生氣了:“村長官再小,也是我們共產(chǎn)黨的官。是共產(chǎn)黨的官,就會替你們解決問題。有啥問題是不能解決的?你說!”說到激動處,雙手發(fā)抖,竟把茶杯里的水都抖了出來。
喇嘛代也激動起來:“你們不解決,我自己
解決。”武書記:“阿球啦,你想怎么解決呢?”喇嘛代:“我給他白刃子進紅刃子出,放倒不就成了?”“喲,你還想殺人?”武書記真的翻臉了,“癩蛤蟆扛個球,還想充當兒子娃娃呢!”喇嘛代忽地站起來,也說起粗話:“不球管了算了,我自己想辦法。”轉(zhuǎn)身,把門一甩,走了。
武書記氣得渾身發(fā)抖,趕忙追出來,朝著喇嘛代的背影喊:“尕球娃,不能胡做啊!過兩天我們就來調(diào)查你們的事。”
但那背影倔強得很,不回頭,徑自去了。武書記返回辦公室,給后鄉(xiāng)長打電話。電話通了。武書記:“后鄉(xiāng)長嗎?你在哪?”后鄉(xiāng)長:“哦,書記啊,我剛處理好桑多村的事,正在回來的路上。”武書記:“先別說桑多村的事,說說有人準備殺人的事。”后鄉(xiāng)長:“誰想殺人?”武書記:“球尕娃的名字沒顧上問,剛才還在我辦公室發(fā)火呢,說是到你那里報過案,有這回事嗎?”后鄉(xiāng)長:“哦,我記起來了,是楊莊的喇嘛代,說是要殺陰陽李根旺呢。”武書記:“這事你怎么不重視啊?要是真的出了人命可就不得了了!”后鄉(xiāng)長:“怎么不重視啊書記,我已經(jīng)把李根旺勸了一回,就準備調(diào)解呢。”武書記:“那就好,你今天下午就去了解情況,把問題處理掉。”后鄉(xiāng)長:“哪還等到下午啊,我現(xiàn)在就去。”
五
喇嘛代氣呼呼地回到家里,盤腿坐在土炕上,連抽了三根香煙。媳婦過來問:“那事,鄉(xiāng)上怎么說?”喇嘛代:“都是吃干飯的,啥事也不干。不干就罷了,還罵人呢!”媳婦:“誰罵人了?”喇嘛代:“還有誰?就那個滿嘴是球的書記!”媳婦:“那怎么辦呢?”喇嘛代:“他們實在不管,我就真要殺了那狗日的陰陽。”媳婦說:“你可不能這么做,這是犯法的事!”
喇嘛代哼了一聲,下了炕,翻箱倒柜找了好半天,竟找到一把長鞘藏刀。抽出來,那刃口上已經(jīng)發(fā)銹,染著幾團黑褐色的銹斑。掂了掂,感覺輕重很是稱手,心底就喜歡上了這把刀。想了想,記得這是祖父的遺物,霎時神情就有點黯然。
看到丈夫找出刀在把玩,媳婦有些驚慌:“你還真想殺人啊?”“狗急了跳墻呢,兔子急了咬人呢!”喇嘛代說,“欺負人不是這么個欺負法。”忽聽得門外有人喊:“喇嘛代在嗎?喇嘛代在嗎?”媳婦趕忙出去看:“在呢,在呢,在家呢。”喇嘛代趕緊將長鞘藏刀塞進箱子里。來人正是后鄉(xiāng)長,身后還跟著兩三個年輕人。后鄉(xiāng)長對喇嘛代的媳婦說:“你把喇嘛代叫出來,我們有事跟他說。”喇嘛代早就出來了:“我在這,有啥事你就說吧。”后鄉(xiāng)長:“我來看看天水在你家院子里是怎么個淌法。”喇嘛代:“沒下雨,你們看不到天水。”后鄉(xiāng)長:“不是那個意思。我想看看陰陽家的天水,是怎么到你家的院子里來的。”
喇嘛代帶著后鄉(xiāng)長走到東側(cè)房邊,指了指前院后墻頂上伸出的一個鐵皮水槽說:“那不是嗎?天水就是從那出來的。”
后鄉(xiāng)長看看那鐵皮水槽,又看看墻根下面,那里已經(jīng)被流下的天水深濺出一個小坑。坑內(nèi)塞著一個鋁制大碗,看樣子是擔(dān)心坑被濺得更深而采取的措施。拿出那個鋁碗就發(fā)現(xiàn),雖然天已經(jīng)晴了四五天了,但坑內(nèi)還有稀泥,顯然水分還未完全蒸發(fā)掉。
后鄉(xiāng)長:“前院這一家,就是李根旺家?”喇嘛代:“就是。不是他家,就沒這破煩事了。”后鄉(xiāng)長:“這水槽在這位置幾年了?”喇嘛代:“去年他們重新填了房頂,就成這樣子了。”后鄉(xiāng)長:“以前不是這樣?”喇嘛代:“以前李根旺是把這水槽開到東面的飼料地里。前年,他的堂弟買了他的飼料地,蓋了房子。今年,他就把這水槽對準我家院子了。”
后鄉(xiāng)長對身后的一個年輕人說:“你去看看李根旺在不在。”
那青年出去了,片刻,回來報告:“在呢。”
后鄉(xiāng)長對喇嘛代說:“走吧,我們到他家看看。”
喇嘛代:“要去你去,我不去。我去了就想殺他。”
后鄉(xiāng)長:“那好,我們?nèi)フ{(diào)解,你可不要亂做。有消息我們會及時通知你。”又對劉二毛說:“今天到喇嘛代家來的事,你記下,記清楚。”劉二毛答應(yīng)了。
這時,大家聽得喇嘛代家門口瑪尼桿上的經(jīng)幡,被南風(fēng)吹得啪啪作響。后鄉(xiāng)長抬頭看了看,那些經(jīng)幡都貼在藍天上,使藍天顯得更藍,經(jīng)幡上的經(jīng)文也顯得更清晰。再看時,便覺得有些眩暈,忙低頭帶著眾人出了門。
六
李根旺早就候在門口等后鄉(xiāng)長他們。一見眾人來了,忙不迭地迎進上房。后鄉(xiāng)長本不想進屋子,但想還得把話說透,不說一會,話就說不透,話說不透,就不能解決問題。于是就進去了,上了炕,劉二毛他們都側(cè)跨在炕沿上。
李根旺給每人泡了一杯八寶茶,又拿來了黑蘭州牌香煙和四星級的世紀金徽酒。后鄉(xiāng)長細看時,發(fā)現(xiàn)茶杯中有茶葉、紅棗、枸杞、核桃仁、桂圓、芝麻、葡萄干、冰糖等東西,知道這是茶里邊的稀罕貨。看到李根旺忙不迭地打開黑蘭州,又準備擰開世紀金徽的酒蓋,也就明白了李根旺的心思:這家伙想討好鄉(xiāng)上的干部,以便解決問題時對他有利。頓時覺得這調(diào)解之事,真是很麻煩。
他忙制止李根旺:“茶,你已泡上了,就喝幾口。煙,你打開了,就抽幾支。這酒,就不要開了。我們來跟你商量事情的,不是來喝酒的。再說,這工作期間,怎么能喝酒呢?”
李根旺:“鄉(xiāng)長大人說得對,說得對。”說著,把酒提離炕桌,放在一旁的八角柜上。
后鄉(xiāng)長喝了一口茶說:“今天來,主要是為了調(diào)解你和喇嘛代之間的關(guān)系。我們的想法是,你們要相互體諒,相互幫助,再不要為一件小事動什么干戈。”
李根旺:“我也是這么想的,但那喇嘛代硬要和我過不去,要我把房后的水路改了。那怎么能隨便改呢?”
后鄉(xiāng)長:“我們剛才去看了,你的確把水路留在人家院子里了,那地上都被水沖出了一個坑。這事落在我的身上,我也會生氣的。你不如真改個水路,別走人家院子,這也不是太復(fù)雜的事。你說對吧?”
李根旺:“我的鄉(xiāng)長大人啊,那水路是不能改的!”
后鄉(xiāng)長不明白:“為啥改不成?改了,會掉你身上的一塊肉嗎?”
李根旺:“那比身上掉一塊肉還麻煩,還可怕。”
后鄉(xiāng)長追問:“有啥麻煩可怕的?”
李根旺:“只要一改,就破了五行。破了五行,會遭報應(yīng),啥都不順的。”
后鄉(xiāng)長問:“五行是啥東西?難道比命還重要?”
李根旺:“鄉(xiāng)長大人啊,這您就在欺負我啦!您是從大學(xué)畢業(yè)的,肯定比我更熟悉五行。我怎能在您面前掄大刀呢!”
后鄉(xiāng)長:“對五行,我還真不太熟,你就給我補補課吧。”
李根旺:“您真不熟?”
后鄉(xiāng)長:“真不熟,熟的話,就不來找你了。”
李根旺只好解釋說,五行,是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的運行方式。按方位來說,五行中,火位于南方,水位于北方,木位于東方,金位于西方,土位于中央,這是萬萬不能亂的。我們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的平頂土木房,下雨后,房頂?shù)奶焖欢ㄒ泵媾拧H襞畔蚱渌轿唬瑫袨?zāi)難發(fā)生。
“我看沒那么嚴重吧!”后鄉(xiāng)長打斷了李根旺的介紹,“鄰里之間,還是要講究和為貴的,孔老夫子早就這么說了,也這么做了,我們應(yīng)該學(xué)學(xué)人家老先生的做法。”
誰知不提孔老夫子還好,一提,倒把李根旺的話匣子給打開了:“鄉(xiāng)長大人,您說到點子上了。若要對照儒家的文化,就說那‘五常吧,金代表安定,是仁;木代表生機,是義;水代表柔和,是禮;火代表爆發(fā),是智;土代表承載,是信。我把水的方位變了,就是不講禮儀。不講禮儀,就亂了。亂了,就不好,那災(zāi)難說來就來了。”
后鄉(xiāng)長被李根旺堵住了話頭,一時竟無話可說,只好取了一支煙,點著,吐出一口濃煙,然后黑著臉,一言不發(fā)。
李根旺:“所以說,這根本就不是水路的問題,是生老病死的大事。”
后鄉(xiāng)長用勁把那根煙抽完,又把煙蒂使勁摁滅,對李根旺發(fā)話:“你說,你到底改不改水路?”
李根旺看到了后鄉(xiāng)長眼睛深處的狠毒,忙說:“你給我給幾天時間,我再考慮考慮。”
后鄉(xiāng)長:“我只給你三天時間。三天后,我派人來檢查,若你還把那水槽撅在那,我就直接拔了。”
李根旺煞白了臉,不知說什么好。這時,院子里有一男孩喊道:“阿大,阿媽叫你有事說呢。”
后鄉(xiāng)長:“對,你們一家子趕緊商量商量,我們就先走了。”
后鄉(xiāng)長黑著臉背著手從李根旺家出來,對身后跟隨的年輕人說:“去,告訴喇嘛代剛才的決定,叫他也不要胡折騰。”一個青年慌忙去了。
七
喇嘛保聽了鄉(xiāng)干事的回復(fù),覺得水路的事沒啥問題了,心里有些歡喜。
可是,等了三四天,也沒見陰陽把那水槽挪動位置,十分納悶:“為啥還不動手呢?”越想越生氣,找了一根粗木棒,站在墻根下,使勁擊打那水槽。沒幾下,那水槽就歪斜下來,掉到地上,同時落下一塊壓水槽的條石,差點砸在他身上。
此時,喇嘛代又得意,又慶幸,覺得自己干了件男子漢應(yīng)該做的事。其實早該這樣做了,就是因為自個的隱忍,才一而再地往鄉(xiāng)上跑,結(jié)果事情還在等待解決中。現(xiàn)在,這事情不是輕而易舉地就解決了嗎?
正得意間,前院房頂上傳來罵聲:“哪個狗日的弄掉了我家的水槽?手閑得很嗎?”
喇嘛代抬頭一看,卻是李根旺的兒子,居高臨下,燥紅了臉,盯著他。顯然是專門罵他來的。
李根旺的兒子十七八歲,瘦高單薄,但罵人的聲音卻比較響亮。
喇嘛代惱了:“我弄的。你想怎樣?”
李根旺兒子:“對你們這些半番子,又能怎樣呢?”
半番子是桑多鄉(xiāng)一帶對不會說藏話只會說漢話的藏族男人的叫法,意思是藏族但又不是純藏族。正如把藏族女人稱為三格毛一樣,半番子的叫法,其實也沒有什么歧視的意思。
但正在斗氣的時候,喇嘛代覺得李根旺的兒子叫他半番子,顯然有著鄙視的意味,于是指著那瘦高的孩子說:“你等著,我一刀子豁了你!”
李根旺的兒子卻不害怕,冷笑一聲:“你能把我的球給割了?!”
喇嘛代:“你等著,我就要把你這尕崽娃給騸了!”
說罷折回屋里,打開箱子,取出刀子。媳婦趕緊拉住他:“你嚇唬嚇唬他就行了,可不能真的動手。你不是說這事鄉(xiāng)上正在解決嗎?我們再等幾天。”
喇嘛代:“等那些吃干飯的解決問題,那就等到驢年馬月了!”
話雖這樣說,但他還是希望由鄉(xiāng)政府出面盡快解決問題。不過,剛才一時沖動,拆了水槽,把這事弄得復(fù)雜了些。李根旺兒子一嚷嚷,實際上還是表明了一個態(tài)度:人家不愿意事情就這么被解決。
拿了刀出來,往房上一瞅,早沒了那小子的身影。猜測對方害怕了,逃了,不僅也冷笑了一聲。
轉(zhuǎn)眼一想,認為事情還沒完,可能后面還有麻煩事發(fā)生,又煩惱起來。他把那藏刀握在手中,端詳了一陣,覺得有必要磨一磨,于是端了一小盆清水,坐在磨刀石后,呼哧呼哧地磨起來。他的女人倚在上房門框旁,一臉擔(dān)心焦慮的神色。
磨了一會,拿清水洗了洗磨過的刀刃,看時,那刀刃在陽光下锃亮锃亮的。翻過來看另一面,也是锃亮锃亮的,用大拇指試了試,刃口刮著指紋,發(fā)出輕微的聲響,就知道確實鋒利了。
這時,從大門里進來兩個人,看時,前一人膚色白凈,精瘦似竹竿,正是李根旺。后一人瘦小精干,滿臉怒色,卻是李根旺的兒子。兩人看到喇嘛代在正在磨刀,都愣住了。李根旺先反應(yīng)過來,忙轉(zhuǎn)身拉住兒子的手。那年輕人罵罵咧咧,想掙脫父親的約束,跟喇嘛代論理。李根旺硬是拉走了自己的兒子。
喇嘛代知道對方是來尋事的,但顯然被自己給嚇走了,嘴角便露出一絲輕蔑的笑,一邊笑,一邊生出了憤怒。他把刀子插入刀鞘,別在腰里,走出大門。他要看看那些人到底想干什么。
八
巷子口,李根旺、李根旺兒子和另外兩三人站在自家門口,低聲商量什么事。見喇嘛代出來,就停止了交談,都拿眼看他。其時已是黃昏,斜陽照著房屋和巷子,房屋上一片金黃,巷子里一片陰影。
喇嘛代知道那些人是商量如何對付他,心里有些擔(dān)憂。他站在自家門口,出不出巷子,拿不定主意。
正猶豫之際,媳婦追了出來,緊緊抓住他的胳膊,驚慌失措地請求說:“你可不能這么干!”
媳婦的聲音高,立刻使李根旺他們警覺起來,都緊張地觀察著動靜。
喇嘛代甩開媳婦:“雜疙瘩們還想來鬧事,我一刀子捅了他們!”
李根旺的兒子漲紅了臉,作勢要撲過來,卻被李根旺拉住了。李根旺的兒子張口欲罵,又被李根旺拉回自家院里去了。
喇嘛代見到李根旺的兒子的反應(yīng),男子漢的熱血也被激發(fā)起來。他覺得該明確地表示一下自己的決心了:要么沖過去和李根旺他們打一架,要么好好罵一頓,只有這樣,才能讓別人知道他不是說說就會完事的人。
正猶豫之際,他家的那頭犏牛出現(xiàn)在巷子口。他曉得,已到牧歸時分,他家的牛自行回家了。
這幾年,男女老少都愿意出去打工,農(nóng)村里已沒人愿意種地,只為耕種而飼養(yǎng)的犏牛,已經(jīng)沒有了它的使用價值。年前,喇嘛代就想把牛賣掉。但因為喂養(yǎng)多年,早就有了難以割舍的感情,就暫時沒有脫手。
現(xiàn)在,喇嘛代看著巷子里越來越近的自家的犏牛,突然有了一種想法:他要當著那些人的面,宰了這頭牛,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
這想法是那么突然,但又是那么刺激,似乎這正是解決他走出走不出巷子的最好辦法。
于是,喇嘛代從腰里抽出藏刀,拔出刀子,等待牛靠近。那些人顯然看到了他的行為,有些驚慌,但都沒動彈,等待著他的下一步動作。
那牛看到喇嘛代立在門口,似乎有些興奮,抬頭朝主人哞了一聲,就溫順地停在主人的身旁。
喇嘛代離牛只有三四步距離。他用眼睛的余光瞥了瞥那幾個人,發(fā)現(xiàn)了那些人的驚慌。他知道只有殺牛駭人,才能徹底使他們害怕他,再也不敢生事。
他下了決心,手握長刀,向牛快速靠近。那牛信任主人,竟不躲避。喇嘛代用刀捅入牛脖頸下,由于用力過猛,連刀把都進去了一部分。霎時,刀口咕咚咚冒出一股熱腥氣,血就泛著粉紅色的氣泡汩汩地流到他握刀的手上,又流到地上。那牛狂跳起來,甩開了刀子,脖子上鮮血飛濺。但只跳了幾下,就轟然倒地,再也爬不起來。它圓睜著黑黑的眼睛,看著它的主人,似乎經(jīng)受了莫大的委屈,抽搐幾下,眼里的光芒就越來越淡,越來越淡,最后失去了生機。
喇嘛代這才知道自己確實殺了自家的犏牛,內(nèi)心一陣悲傷。他想扭頭看看那些人,卻無法做到這一點,他只好看著牛眼里越來越模糊的自己,慢慢地跪了下去。
身后,傳來一聲驚呼。扭頭一看,他的女人已經(jīng)昏厥在地,也像牛臨死時那樣抽搐著。
九
喇嘛代殺牛后的第二天,李根旺就去了鄉(xiāng)政府。
他驚慌失措地坐在武書記的辦公室里,抖抖索索地向后者講述喇嘛代殺牛的經(jīng)過。或許因為過度緊張,他的表達有些顛三倒四,但武書記還是聽明白了事情的經(jīng)過。
武書記:“人家殺了條牛,就把你緊張成這樣,你也太膽小了吧!”
李根旺:“不是我膽小,他那是殺給我看呢!”
武書記:“你的意思是,他是殺雞駭猴?哦不,是殺牛駭人?”
李根旺:“我估計就這意思。”
武書記:“那沒啥啊,他又沒給你動刀子。”
李根旺:“書記大人啊,他若是對我動刀,來給你說這事的,就是鬼魂了。”
武書記:“少給我說不科學(xué)的東西,我可不信這些玩意兒!”
李根旺:“我知道您不信。而今這事咋辦呢,您可要給我想個辦法。”武書記撥通了一個電話:“你到我這來一下。”過來的是后鄉(xiāng)長,苦著臉,好像有許多煩惱事。見到李根旺在,那臉就更苦了。
武書記問后鄉(xiāng)長:“那天叫你去處理他和鄰居家的事,你說你已處理好了,可現(xiàn)在又出了事,你說怎么辦?”
后鄉(xiāng)長吃了一驚:“出了啥事?”李根旺又把喇嘛代殺牛駭人的事說了一遍,這一次倒口齒清楚了許多。后鄉(xiāng)長批評李根旺:“那天我叫你把那水槽拆了,看樣子你遏著沒辦,是不是?”
李根旺:“我只拖了一天,他就自個給我搗毀了,還罵了我兒子一頓,威脅要殺了我兒子呢!”
后鄉(xiāng)長:“書記您聽,我都安排好了,可他們沒按我交代的辦。這兩天仁貝村又發(fā)生低保被人冒領(lǐng)的事,我正在查那事,所以這頭就沒跟緊。”
武書記:“低保的事,我聽說了,算是要緊事,你不要耽誤。這邊這事,你有空再去喇嘛代家,該勸說就勸說,該警告就警告,反正要把事情處理好。”
后鄉(xiāng)長連連點頭:“好的,好的。”又對李根旺說:“既然你的水槽已經(jīng)被人家毀了,你就重新改條水路,再不要整到人家院子里,行不?”
李根旺哭喪著臉:“這水路一改,我又要折財了!”后鄉(xiāng)長:“折個屁,你就是個迷信罐罐兒!”武書記:“你倆再甭球吵了,都回去,各干各的事吧。”后鄉(xiāng)長起身要走,武書記說:“哦,你先別走,我有個事要問問。”李根旺趕忙起身走了。武書記聽得李根旺走遠了,才對后鄉(xiāng)長說:“剛才別人在,你不應(yīng)該說低保的事。”
后鄉(xiāng)長:“給您匯報工作,一時給說漏嘴了。”武書記問:“仁貝村低保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鄉(xiāng)長:“有村民反映村長收了他們的一折通,說是公家有用,其實拿那些折子冒領(lǐng)了人家的低保。”
武書記:“這是真的嗎?”后鄉(xiāng)長:“還在查,估計八九不離十。”武書記:“球大的村長,膽子倒不小。這些胡日鬼,要好好治治。”后鄉(xiāng)長應(yīng)和說:“就是,我們這鄉(xiāng)上,就這些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破煩事!”
武書記:“這話不對,你作為鄉(xiāng)長,要明白:和老百姓有關(guān)的事,都是大事,沒有小事。”
后鄉(xiāng)長正要說話,武書記卻朝外罵道:“你這個球陰陽,還縮在門口干啥?”
被罵出來的,正是李根旺。他蹩進門來,猶豫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說:“這低保的事,兩位大人,你們能不能也考慮考慮我家,我家連一個都沒有享受呢!”
武書記:“享受個球,偷偷摸摸地,像個賊!賊能享受低保嗎?”武書記顯然對李根旺躲在門口偷聽的行徑很是生氣,罵人時已經(jīng)口不擇言了。李根旺渾身顫抖不止:“那那那喇嘛代,殺殺殺牛的事,你們還管管管不管?”武書記罵道:“管個球,把人殺了再說!”李根旺一聽,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在這屋子里待了,轉(zhuǎn)身就走,不小心被什么東西絆了一下,差點杵倒在地。
十武書記悔不該說出“把人殺了再說”的話來。第二天一大早,天氣不太好。
武書記對著陰沉的天空罵了一聲娘,話音沒落,喇嘛代就來了。
喇嘛代把一柄染著黑紅色血跡的藏刀撂在武書記的辦公桌上,說:“我來報案!”
武書記剛剛吃過早點,胃里的那兩顆蛋還未消化,猛地聞到一股血腥味,就有些反胃,干嘔了兩聲,端起茶杯說:“報球子啥案,不就殺了一頭牛嘛,還想到鄉(xiāng)政府來顯擺?”
喇嘛代:“這次殺的不是牛,是人!”
武書記手中的茶杯掉在桌上,茶水濺了一桌,流過桌面,又滴滴答答滴在地上。
“你你你,你說啥?”
“我殺了李根旺的兒子。”
武書記一陣眩暈,雙手撐在桌子上,胳膊一軟,沒撐住,跌倒在地上。
門突然被人搡開,一人闖進來:“書記,不好啦!那喇嘛代殺了人啦!”
來人正是后鄉(xiāng)長,他看到武書記倒在地上,正在努力往起爬,又瞥見喇嘛代坐在沙發(fā)上,以為武書記是喇嘛代打倒的,慌忙中拎過一把椅子,橫在自己身前。
武書記終于爬起來,他抖抖索索地坐回辦公桌后,問喇嘛代:“你真殺了人?”
喇嘛代:“不殺不行了,不殺我就沒臉活人了。”
后鄉(xiāng)長放下椅子,小心地坐在沙發(fā)那一頭,小心地問:“你這是啥意思?”
喇嘛代:“今早陰陽家的那小子來我家取他家的水槽,我以為他家準備改水路呢,就叫婆娘去拿給他。那小子見水槽壞得厲害,就罵罵咧咧的,說我殺牛就是為了裝樣子,還說有種的就把他的球咬掉。我在房子里聽著,心里不舒服,就出去問他是啥意思。他見了我,沖我喊:‘有種的就把我的球咬掉!我一氣之下,就抽出腰刀說:‘你再跳彈我就宰了你!誰知那小子把脖頸伸過來說:‘你敢!我愣住了,不知該怎么辦才好。他說:‘知道你就不是咬狼的狗,還冒充兒子娃呢!我生了氣,拔出半截刀,用刀背撞他脖子。誰知他伸手一抓,抓住了刀鞘。他不抓還好,一抓,我趕緊把刀子往懷里拉。他用力奪刀,我也用力奪刀,刀子就翻了個身。他的力氣大,搶得猛了,刀子就過去了,割到了他的脖子。誰知他的脖子不經(jīng)割,一下子就冒出血來,人也就倒下了。我嚇壞了,就趕緊到這里來報案。”
武書記這才明白過來:“那娃呢?”喇嘛代:“還在我家院子里吧,我來的時候,他還趴著呢!”后鄉(xiāng)長:“我聽他們村的人說,那娃已經(jīng)死了!”武書記:“你去他家看了沒看?”后鄉(xiāng)長:“我是上班路上聽說的,嚇壞了,趕緊來見你,還沒顧上去那呢。”武書記:“你趕緊去看看。我這就給派出所報案!”后鄉(xiāng)長慌慌張張地喊了一兩個干事走了。喇嘛代站起來納悶地問:“不是到這里報案嗎?”武書記罵道:“到這里報個球案,報案,要給派出所報呢!”喇嘛代一聽,站起來說:“我去報吧,人是我殺的。”武書記:“你等著,我打電話。”武書記轉(zhuǎn)身給派出所打電話,那邊卻無人接聽,連撥三次,都沒啥結(jié)果。只好擱下話筒說:“不行,沒人接,我倆一起去派出所報案吧!”
沒人搭話,扭頭一看,那喇嘛代卻不在身邊。忙追出來,問院門口進來的劉二毛:“見到喇嘛代了嗎?”
劉二毛煞白著臉說:“見了,提著一把刀,往北走了。”
往北的方向,正是去派出所的方向。武書記估摸喇嘛代是去報案了,但還是不放心,對劉二毛說:“我們也去,到派出所報個案。”
劉二毛奇怪地問:“報啥案?”
“沒聽說喇嘛代殺了人嗎?!”
“殺了誰?”
“殺了你娘!”武書記生氣了。
十一
但武書記錯了,喇嘛代是去了北邊,卻沒去報案。
誤殺了李根旺的兒子后,他懵懵浪浪的,腦子不大清醒,知道自己殺了人,要抵命的,又沒處可去,就提著刀來鄉(xiāng)政府報案。誰知竟報錯了案,報案應(yīng)到派出所去。在往派出所走的路上,腦子漸漸清醒起來,也害怕起來:本來不想殺人,才三番兩次去報案,誰知還是殺了人,這如何是好?
越想越怕,那要了人命的藏刀也抓不住了,倉啷一聲掉在地上。這聲音更嚇得他的魂都出了竅,心里亂成一團:“到底咋辦呢?咋辦呢?”
想反身回家,又覺得家里挺著一個死人,一大堆麻煩在等著自己。想去報案,又不知自己的后半輩子該怎么過,反正聽說殺人得償命,最起碼要判個幾十年,抓進班房子里,遭人欺負,吃屎喝尿,再也出不來。
胡思亂想了好一會,抬頭看看陰沉的天空,知道不一會就會下大雨,心里就更亂了。
忽然看到天幕下東邊的山脊上,隱隱透出亮光,頓時覺得那仿佛就是神靈在冥冥中的指引,腳步一拐,就拐上了一條山溝。這條山溝彎彎曲曲的,通向了東邊的山梁,通向了另一個縣的另一個鄉(xiāng)。他腿上一加勁,沒入了那條山溝。
西山頂上的烏云壓了下來,一道閃電之后,響起了可怕的雷聲。
十二
喇嘛代逃離后,武書記因為“把人殺了再說”這句話,不僅被縣上撤了職,還被通報批評。他自個也不好意思在桑多鄉(xiāng)待下去,就想法調(diào)到老家去了。而后鄉(xiāng)長,也因為在喇嘛代報案事情上的不作為,被組織給予警告處分,也在全縣被通報批評,弄了個灰頭土臉,做官也做得沒啥精氣神了。
幾年后,退休在家的后鄉(xiāng)長去外地轉(zhuǎn)親戚,順便去看望疾病纏身的武書記。兩個人坐在屋檐下,喝了一會茶后,武書記提議:“整幾杯吧?”
后鄉(xiāng)長:“您也退休了,身上又有病,為了您的身體健康,就不喝了吧!”武書記:“整一點,整一點。我還想給你說件事呢,你保證感興趣。”
于是拿出一壺青稞酒,倒在兩盞紫砂杯里。那青稞酒顏色渾濁,卻香氣撲鼻。兩人碰了幾杯后,后鄉(xiāng)長問:“老領(lǐng)導(dǎo),到底啥事啊?這么神神秘秘的。”
武書記:“知道那年殺人的喇嘛代嗎?”后鄉(xiāng)長:“那怎能忘記呢?正是因為他,我倆才走到了如今這個地步。”武書記:“其實沒有他,我倆也會走到這個地步的。”后鄉(xiāng)長想說什么,卻又閉了嘴,只端了一杯酒,灌進肚里。武書記:“我聽說,他在四川,被抓住了。”后鄉(xiāng)長“哦”了一聲,并不驚詫。武書記倒驚詫了:“你知道這個消息了?”后鄉(xiāng)長:“不知道。但我知道,他遲早會被抓住的。”“為啥呢?”“他的根在這里。只要根在這,他遲早會回來的。”
武書記:“你說得對。其實他的被抓,聽說還是他自己跑到當?shù)嘏沙鏊栋傅慕Y(jié)果。知道具體的過程嗎?”
后鄉(xiāng)長搖搖頭。武書記:“其實是喇嘛代又犯了一件事,走投無路,才走投案這條路的。”后鄉(xiāng)長很驚訝:“哦?”武書記解釋說:“他殺了人,在鄉(xiāng)上不敢待,也不敢待在縣上,更不敢在省里混。左思右想,就從親戚那里借了點錢,跑到四川去了。這一去,一邊到處打工,一邊東躲西藏,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后來覺得無法活下去了,正不知如何混的時候,不小心陷進一個泥坑了。”
后鄉(xiāng)長:“啥泥坑?”
武書記:“那個球不小心整上傳銷了!”
后鄉(xiāng)長著實吃了一驚!
武書記:“其實他也是稀里糊涂進去的。當時只想盡快發(fā)財,不成想竟被人家關(guān)進房子里,成了活死人。他又不敢聯(lián)系親戚朋友,只好干挨著。時間長了,就被人家斷了食糧。他親眼見到拉他入伙的那人,因為發(fā)展不了下線,被人家揍得死去活來,害怕之下,竟生出大勇氣,直接從三樓上跳下來,斷了一條腿。又怕人抓住,就一瘸一拐地進了當?shù)嘏沙鏊瑘罅藗麂N團伙犯罪的案子。”
后鄉(xiāng)長明白過來:“他要報案,人家肯定問他的來歷,這才被抓了?”
武書記:“就是。我估計他也不想再過東躲西藏的日子了。你想想,有家有室的,卻不敢看望。誤殺了人,心里可能也比較內(nèi)疚。再說事情過去好幾年了,我們政府的政策,若能自首,就能寬大處理。也許正是這些原因,才讓喇嘛代有了回頭的打算吧!”
后鄉(xiāng)長:“四川那邊的人怎么處理的?”
武書記:“那邊的人不信,以為他說謊。后來連窩端了那個傳銷組織,又打電話問我們這邊,得知確有這么多事,就把他抓了。”
后鄉(xiāng)長:“看樣子沒有那傳銷的事,不知道他要躲到什么時候呢!”
武書記:“是啊,走投無路的時候,投案,就是他喇嘛代不得不做的事了。”
兩人不再說話,只是碰杯喝酒,不知不覺,兩人都醉了。
武書記醉得尤其厲害,他問后鄉(xiāng)長:“喇嘛代,你到我這里來干啥?”
后鄉(xiāng)長醉意朦朧地回答:“書記啊,我不是喇嘛代,我是李根旺。我來想給您說,喇嘛代動了我家的水槽,災(zāi)難就從天而降了。我這是向你要兒子來了!”
誰知武書記早已沉睡過去,發(fā)出粗重的呼嚕聲。

